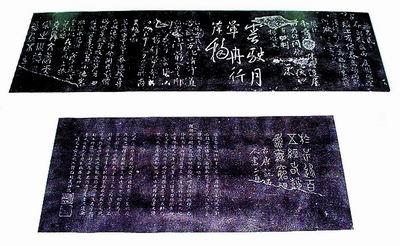-
沒有記錄!
百年滄桑臨灃寨
2013/12/9 10:07:21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位于郟縣堂街鎮的臨灃寨迄今已有140多年的歷史,被譽為“中原第一紅石古寨”、“古村寨博物館”。日前,她又喜獲一項殊榮——被建設部、國家文物局命名為“中國歷史文化名村”。11月14日,懷著仰慕之情,記者走進這座古村寨,去感受她的建筑與人文魅力。
滄桑臨灃寨
從郟縣縣城驅車往東南行12公里,遠遠便望見一個被高大的紅色寨墻圍著的村子,帶著幾分神秘,又有些許孤寂。同行的郟縣縣委宣傳部的人說,這就是臨灃寨。
村前有河水潺潺流過,繞著寨墻還有一條護寨河。據說寨子周圍原先還有千畝蘆葦蕩,想來一定很美。高高的寨墻清一色由大塊的紅石砌成,寨頂上隔一段一個垛口,看起來古樸而厚重。來到寨子的東南門,只見厚厚的木制寨門開啟在兩邊,外面包著的鐵皮已斑駁銹蝕,向人們訴說著年代的久遠。
走過寨門進入村中,剛下過雨的村中道路有些泥濘,一些古老的民居、在門前忙活的村民依次映入眼簾。聽說記者來采訪,郟縣堂街鎮臨灃寨開發辦主任尹亮亮急忙從外面趕了回來,熱情地做我們的導游。
臨灃寨始建于明末,占地7萬平方米,寨長1100米,呈橢圓形狀。村子里起初住著張姓人家,明朝萬歷年間,有朱姓人家從山西洪洞縣遷來,數百年來在此繁衍生息。現在村子里有600口人,約百分之九十是朱姓后代。
朱姓為何要遷居于此?尹亮亮說,臨灃寨一度曾叫“朱洼寨”,當地有一種迷信的說法是,因為“朱”與“豬”諧音,而豬性喜水,此處兩面臨河,又處洼地,能聚水聚財,朱姓便看中了這塊風水寶地。300多年后,朱姓后代做鹽商發了家,于同治元年重修了這座古寨,周圍修了護寨河,整個寨子就如一條小船漂在水上。
臨灃寨共有三個寨門,是按八卦的三個方向設置的。寨子的西北門保存得最為完好,我們在現場看到,寨門上方題有“臨灃(灃為老寫字)”二字,兩扇大木門上包著鐵皮,鐵皮上“同治元年”的字樣仍然清晰可見,寨門前設有兩道防水閘,當年的閘板還立在閘中。
尹亮亮告訴我們,“臨灃”二字,因面臨灃溪而得名。據《水經注》一書記載:“柏水經城北復南、灃溪自香山東北流入郟境,至水田村,一由村南而北,一由村北而東,環村一周,復東北至石橋入汝”。此處的“水田村”即為今天的臨灃寨。
寨子的西南門曾遭破壞,寨門沒有了,但高大的城樓還在,如碉堡一樣,上面留有許多打槍用的射孔。據《郟縣志》記載,日軍入侵中原時,郟縣的100多座村寨發揮了作用。1945年6月3日,日軍攻打“臨灃”,村民曾據寨英勇抵抗。1947年12月24日,我劉鄧九縱二十七旅八十團攻入寨內,活捉寨首朱清寬,解放了臨灃寨。
新中國建立后,各地開始拆除寨墻,郟縣的100多座村寨都拆了,唯有臨灃寨幸存了下來。尹亮亮說,這是由于1957年郟縣發生水災,臨灃寨因處洼地,洪水淹至寨墻數米高,為了防汛的需要,縣里決定不再拆除臨灃寨。
百年朱鎮府
雖然被高大的寨墻圍著,寨內居民的生活看來和別的村莊并無二致。想想也是,如今是信息社會,任何村莊都不可能成為“世外桃源”,遠離塵世的喧囂。
隨意走進村部旁邊的一戶村民院中,一位老太太坐在堂屋的房檐下,頭上包著毛巾,手上不停地摘辣椒棵上的小紅辣椒,面前的籮筐里已經快滿了。
老太太名叫王愛,90歲了,眼不花耳不聾。她家的堂屋是清代建的大瓦房,房頂上“五脊六獸”,雕刻精美的木門、木窗及室內的八仙桌,可以想象她曾經的繁華。老太太張開沒牙的嘴笑著說:“我從一二十歲嫁到朱家,就住在這房里,有六七十年了。”她的兒媳周勸說:“這房子是祖輩留下來的,現在破得很,很多地方都漏雨了。”周勸的兒子、兒媳遷到村外去了,家里只有她、丈夫和婆婆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