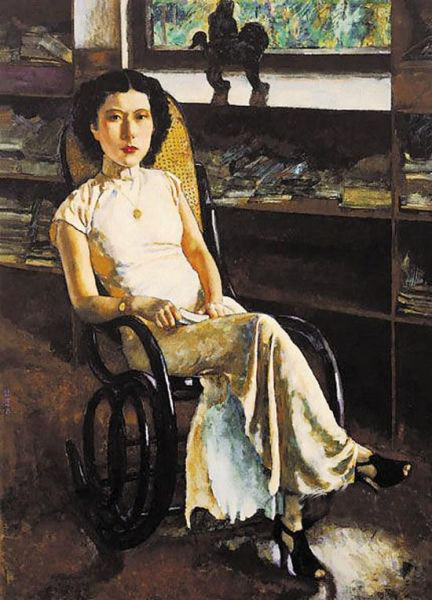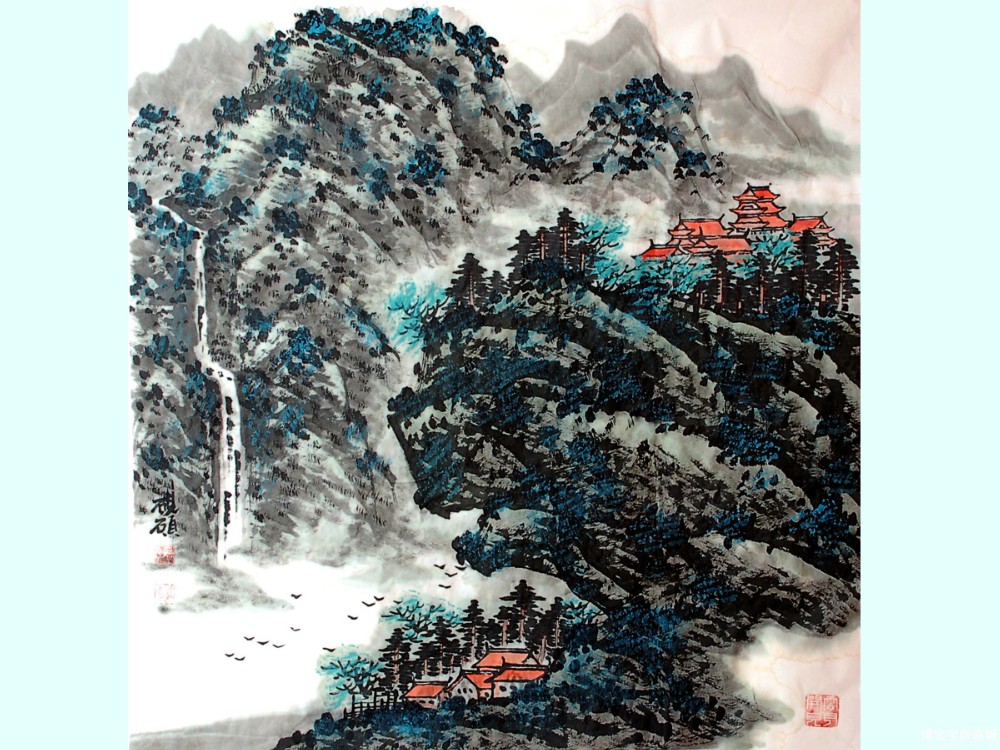-
沒有記錄!
《墨子》“說”體與先秦小說
2014/12/25 14:36:32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內容提要】《墨子》把用來論辯的故事稱為“說”,促成“小說”概念的產生。《墨子》“說”體故事是其書最具情節性、可讀性的文字,通過其中的志怪,可以窺見先秦志怪小說的內容與特點;關于名人軼事的編排,促成戰國軼事小說的繁榮。墨家拉開了“飾小說以干縣令”的百家爭鳴的序幕,也開啟了戰國雜家小說創作的精彩紛呈。
【關 鍵 詞】《墨子》/“說”體/先秦小說
【作者簡介】 董芬芬(1968—),女,甘肅莊浪人,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主要從事先秦兩漢文學研究。
一、《墨子》之“說”與“小說”概念
在論及論辯方法和技巧時,《墨子》提出了“說”的概念。《經上》篇說:“說,所以明也。”《小取》篇又說:“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說”,是用來解釋事物原委、說明意義的故事。如《貴義》篇說:“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則“湯之說”,就是湯往見伊尹的故事。又《明鬼下》在講述杜伯殺周宣王的故事后說:“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其中的“若書之說”,指書中那些鬼神賞賢罰暴的故事。《墨子》的“說”,是指用來證成自己學說、宣揚墨家主張的故事,有人物,有情節,故事性強,有一定的思想傾向,既是立論的材料,也是論辯的方式。
《墨子》把論辯用的故事稱為“說”,在戰國其他諸子那里得到認可沿用。《莊子·天道》篇桓公說:“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就講了自己斫輪的故事。宋玉《登徒子好色賦》:“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宋玉就講述了自己與那個“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的東家女的故事。《韓非子·內儲說上》云:“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臣壅塞,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灶……”“其說在……”式的表述在韓非《儲說》各篇中較多,“說”是指文中用以解釋經文的故事。其中的《說林》、《儲說》,是“說”的匯集,“所謂‘儲說’,即將許許多多的‘說’儲聚在一起,藉以表達作者的思想……所謂‘先經后說’,一般上都是‘經是事理,說是故事’”[1]285-286。所以,“說”是諸子論辯文中最具故事性、戲劇性、可讀性的文字。
“說”,還成就了中國古代一個重要的文體概念,“小說”一詞就是由“說”而來。《莊子·外物》篇說:“飾小說以干縣令,其與大達亦遠矣。”這里的“小說”本指那些“輇才諷說之徒”的“說”[2]。在莊子眼里,其他諸子都是見識淺陋的“輇才諷說之徒”,他們的“說”,與任公子釣大魚的境界有天壤之別,故稱“小說”。“小說”表面上是莊子對“輇才諷說之徒”們“說”的貶稱,引申意義指那些不同于道家思想、不能達于至道的其他諸子的學說。漢人把這一概念作為虛構性敘事文體的專稱,也是深得莊子“小說”之三昧。《漢書·藝文志》謂小說家為“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所造”、“閭里小知者之所及”、“芻蕘狂夫之議”,與莊子“后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表述的意思基本一致,所以,莊子“小說”一詞,是后世虛構性敘事文體“小說”概念的創始。《漢書·藝文志》所錄古代的小說家中就有五部以“說”為名,充分顯示出“說”與“小說”的淵源關系。漢代劉向所編的《說苑》、《新序》也是這種“說”的匯編,一則一則的故事,波瀾起伏,引人入勝,是“帶有一定古代小說集性質的書”[3]2-4。再到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沈約的《俗說》、殷蕓的《小說》,“實在是一以貫之的一條線,這種叫做‘說’或‘小說’的文體,顯然是產生于先秦,且一直影響并延續到后代的”[4]。所以,《莊子》是“小說”文體概念的創始,而“小說”一詞又源自《墨子》的“說”,也毋庸置疑。
諸子講道理、明觀點的“說”,包括歷史故事、逸聞瑣語、神話傳說、小說寓言等。后世沒有一個能涵蓋這些內容的概念,既然戰國諸子名其曰“說”,我們也就索性稱其為“說”體(有學者已經在使用這個概念①),“說”體可以概括諸子用來論辯的所有敘事性材料。《墨子》“說”體是指墨家用來宣揚思想、學說的所有敘事性材料。直接論證自己的觀點,未必能達到目的,而援引其他故事,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墨子》“說”體故事與先秦小說關系密切,本文主要從先秦志怪、名人軼事等題材小說為例,嘗試論之。
二、《墨子》“說”體與先秦志怪小說
《墨子·非命中》的“三表法”,其中“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墨子》論辯故事中有許多來自“天鬼之志”,這是《墨子》“說”體中最能體現墨家本色,“異端”色彩最為濃厚的地方。
《墨子·明鬼下》集中敘述杜伯射周宣王、燕簡公殺莊子儀、襪子杖斃觀辜、中里徼之死及句芒賜鄭穆公十九年這五則鬼神的故事,前四則《墨子》說分別來自周、燕、宋、齊之《春秋》。據說墨子見過百國《春秋》[5]1197,但這百國《春秋》亡佚,后人無從知曉其面目,但就這幾則故事來看,《墨子》所說周、燕、宋、齊之《春秋》,與正統史書大相徑庭,倒很像志怪野史之類。如杜伯之事:
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于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杜伯射周宣王事,《國語·周語上》內史過也有一句提及:“周之興也,J2Y308.JPG鳴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部。是皆明神之志者也。”這里的“明神之志”,就是關于鬼神的記載,應同墨子的“天鬼之志”一樣,皆是張皇鬼神、稱道靈異的書籍。內史過說杜伯之事在“明神之志”,《墨子》說“著在周之《春秋》”,則這“周之《春秋》”即“明神之志”、“天鬼之志”類專門宣揚鬼神賞善罰暴的志怪野史。
杜伯射周宣王的故事,情節曲折,語言生動,細節描寫引人入勝,散發著神秘、恐怖的氣氛。周宣王之死乃歷史大事,《尚書》卻未有一字提及。《左傳》也記載了內史過論神這件事,卻無“杜伯射王于鄗”這句話。司馬遷《周本紀》寫周宣王之死,也只有非常簡單的交代:“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宮湦立。”[6]145這些正史對《墨子》所說的杜伯射周宣王的故事未予采信,大概皆因其過于荒誕不經。
《墨子》句芒賜鄭穆公十九年陽壽的故事,孫詒讓以為其中的鄭穆公“實當‘秦穆公’之訛”[7]227,此說正確。王充《論衡·無形》篇云:“傳言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秦穆公是《左傳》著重記載的人物,句芒賜年十九的故事不見于《左傳》,大概也是出于“明神之志”、“天鬼之志”類書籍。燕簡公于周敬王十六年即位,是春秋晚期人,其被莊子儀杖斃之事《左傳》、《國語》皆未載。王充《論衡·書虛》篇說:“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儀,其后杜伯射宣王,莊子儀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為虛言。”正史的作者,皆以其為不雅馴之“虛言”而不予采信。墨子說出于齊《春秋》的王里國、中里徼訴訟之事,更是帶著濃厚的巫術、神判色彩,顯得原始而詭異。讓二人面對社神讀自己的起誓辭,認為在神的示意下,羊會攻擊那個有罪的人,中里徼的誓詞未讀完,就被羊當場頂死,這是巫術盛行時代曾采用過的斷獄方法。《左傳》記載了好幾樁訟獄之事,都要求雙方擺證據、辨是非,沒有采用神判的荒唐做法。《墨子》中里徼的故事,不會出自官方正史。
所以,《明鬼下》所述出于周、燕、宋、齊之《春秋》的幾則故事,實皆出于古代的“明神之志”、“天鬼之志”類志怪野史。先秦人把志怪野史也稱作《春秋》,如“古今紀異之祖”[8]377的《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9]7,《汲冢瑣語》遺文有記周、魯、齊、宋等國傳說的,“看來還會有《周春秋》、《魯春秋》、《齊春秋》等”[10]103。這些故事,內容迂誕,情節離奇,視其為歷史,則失之荒誕,如果當小說來讀,倒很引人入勝,能充分滿足人們的好奇心,應是中國古代志怪小說的早期作品。周內史過、墨子皆如數家珍,說明志怪在春秋戰國廣為流傳。《莊子·逍遙游》說:“齊諧者,志怪者也。”莊子也見過齊諧的志怪,志怪在先秦的創作與流傳,規模遠遠超出后人的想象。
先秦諸子“說”體中,大量援引志怪的,墨家最為突出。墨家對這些故事深信不疑,視其為信史。盡管顯得荒誕不經,但古代早期的志怪小說,正是通過《墨子》“說”體保存下來一些片段,通過這些文字,可以看出先秦志怪的特點。
第一,先秦志怪多出自史官之手。墨子把記載杜伯射周宣王、燕簡公殺莊子儀、襪子杖斃觀辜、中里徼之死及句芒賜鄭穆公十九年這些怪異故事的“明神之志”、“天鬼之志”稱為《春秋》,說明在墨家眼里,這些書籍同儒家經典中的《春秋》、《左氏春秋》一樣,都是信史,都出自史官之手,可以當做可靠的歷史典故援引。
《國語》的記載也可以印證這點。《國語》中一些荒誕不經的故事,也多出自史官。《國語·周語上》內史過論神降于虢,“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丹朱是傳說中堯的兒子,房后是周昭王的王后,幾千年前的丹朱的神靈竟然附于房后而生下周穆王,現在又降于虢,真乃咄咄怪事!無怪乎柳宗元批評說:“妄取時日,莽浪無狀,而寓之丹朱,則又以房后之惡德與丹朱協,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虢……其為書也,不待片言而迂誕彰矣。”[11]1272-1273《鄭語》中周史伯講述褒姒的身世,也是“迂誕”非常:
《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史伯所引《訓語》中褒之二君化龍的故事,是很早以前流傳的一則志怪。褒姒的出生,竟然是這則志怪的延伸和演繹:二龍之漦在周厲王時化為玄黿,使一女童無夫而孕,于周宣王時生下女嬰,丟棄路上,一對賣檿弧的夫婦收留她并帶到褒國,后由褒君獻給周幽王,此即褒姒。史伯用這個故事說明天命亡周,不可逆轉。《國語》因為記載了這些怪誕之事,受到柳宗元的貶斥,可這些故事皆出自周王室史官。內史過的“神明之志”,史伯所引的《訓語》,皆是春秋以前史官們的作品,內史過和史伯也成為演繹新志怪的生力軍。可見,先秦志怪許多出自史官之手之口,劉知幾謂“史氏之別流”[9]253,應是比較客觀的說法。
第二,先秦志怪不是出于娛樂的需要,而是從鬼神、宗教的角度再現歷史、解釋歷史,具有明顯的神道設教的意圖。為了增加可信度,先秦志怪一般都附著于真實的歷史事件和人物,歷史與鬼神雜糅,真實與虛構參半,似真似幻,迷離恍惚。
比如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都是歷史,《尚書》有記載,《左傳》、《國語》所載春秋大夫也多有論及,但這些記錄皆沒有《墨子·非攻下》的怪異:“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于廟,犬哭于市,夏水,地坼及泉,五谷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為了表現三苗之罪,用日妖、雨血、龍生、犬哭等怪異災變來渲染夸張,說明禹伐三苗乃順天之意,得天之助。這樣神秘詭異的文字,多出現于后代盛傳的讖緯書中。又說夏桀時“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谷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余”,渲染著詭秘恐怖的氣氛。武王伐紂,《尚書》的《泰誓》、《牧誓》、《武成》等篇及《逸周書·克殷解》皆有記載,但在《墨子》中,卻是另外一番恐怖怪異之象:“遝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亦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河出綠圖,地出乘黃。”一場場改朝換代被寫得如此驚天地、泣鬼神,這樣的文字,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后世《封神傳》中的情節和寫法。
先秦早期的志怪依附于歷史,與歷史事件、人物糾結在一起,是當時許多人眼中的信史。《竹書紀年》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三家分晉后述至魏安釐王二十年,其中就充斥著許多神怪的信息,如三苗將亡天雨血,青龍生于廟,胤甲時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宣王時馬化為狐等怪異之事,情景與《墨子》“說”體所述志怪一脈相承,《竹書紀年》的編者也把這些怪異之事當做信史來看待。
志怪版的歷史,正如魯迅所說:“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為小說。”[12]29但其故事離奇,情節生動,比正統史書更有吸引力,頗能滿足世俗之人的好奇心,“怪力亂神,俗流喜道”,“好者彌多,傳者日眾”。[8]374在中下層民眾中擁有相當的信眾,他們對志怪的興趣要遠遠超過正統史書,志怪野史是他們獲取歷史知識的主要來源。《墨子》“說”體中的志怪情節完整,故事生動,頗注意細節與環境的描寫。這樣的故事,“列于《搜神記》、《幽明錄》甚至《聊齋志異》中也毫不遜色”[13]。借歷史事件演繹鬼神故事,宣揚宗教思想,運用虛幻的小說手法,是中國唐前志怪的共同特點。漢魏六朝的志怪小說雖繁榮,但也沒有脫離神道設教的意圖,在這點上,與先秦志怪沒什么本質的不同。
第三,先秦志怪是后世志怪小說的源頭活水,后世有些志怪小說就取材于先秦。杜伯射周宣王故事在后世的發展演繹,也正體現了《墨子》“說”體對后世志怪小說的影響。
這個故事比較完整的情節,最早見于《墨子·明鬼下》,后來在《說苑·立節》篇又多了左儒這個人物,說左儒是杜伯之友,知道杜伯無罪,力諫宣王,宣王不聽,殺死杜伯、左儒。宣王為何殺杜伯,《墨子》和《說苑》都沒有交代。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在顏之推的《冤魂志》中就非常完整,開頭說:“杜伯之名曰恒,入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于宣王曰:‘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空錡殺杜伯。”[14]顏之推給加上一個女鳩以情色誣陷的開頭,交代杜伯之所以被周宣王所殺的緣由。《冤魂志》在《墨子·明鬼下》所述梗概之上,雜糅進《說苑·立節》中左儒這一人物,又增加了宣王妾女鳩、司空錡、祝、皇甫等人物,故事前因后果便很清楚、完整,情節更曲折,人物更繁雜。從《墨子》到《冤魂志》,這則故事的發展演繹之跡頗為清晰。《墨子》“說”體中的志怪片段對后世志怪小說的影響,可見一斑。
人類在鬼神崇拜中爬過一段漫長的歷史,“明神之志”、“天鬼之志”一類的記載產生得非常早,也非常多,所以志怪類應該是古代小說最早、最為普遍的題材之一。隨著社會的進步,理性思想的勝出,“明神之志”、“天鬼之志”的影響力日漸式微,孔子繼承歷代有識之士的理性態度,“不語亂、力、怪、神”(《論語·述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先進》)。在儒家眼里,這些“明神之志”、“天鬼之志”是“異端”,孔子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論語·為政》)儒家對鬼神的理性態度,促進了社會的文明進步,卻極大地擠壓著志怪野史小說的傳播空間。魯迅說:“孔子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實用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說,俱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無所光大,而又有散亡。”[12]12-13許多志怪小說因儒家的鄙棄而永遠湮沒了。
墨家門徒多來自社會下層,正是先秦志怪的讀者和信徒,在宣揚墨家鬼神思想時自然會資以為說,所以,《墨子》“說”體中的先秦志怪片段,在研究古代志怪小說方面,顯得彌足珍貴。可惜后來研究古代小說史的學者,大多未能注意到《墨子》在這方面的價值。如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于先秦只提到《山海經》、《穆天子傳》及《楚辭·天問》,對《墨子》“說”體中的志怪小說片段只字未提。李劍國先生把《汲冢瑣語》定為先秦第一部志怪小說[10]96,也是沒有考察《墨子》“說”體中的各國《春秋》的實質,也忽略了其中志怪故事片段的小說本質。
三、《墨子》“說”體與先秦軼事小說
《墨子》“說”體中涉及許多名人軼事,其中關于伊尹、晏子及孔子等歷史人物的故事最為著名,是先秦軼事小說的雛形。《墨子》“說”體在古代軼事小說發展史上,有重要的開啟之功。
伊尹是商湯之相,商初舉足輕重的人物。戰國時代,盛傳伊尹負鼎以滋味要湯的故事,《墨子·尚賢》、《莊子·庚桑楚》、《韓非子·說難》、《呂氏春秋·本味》,以及《說苑》的《尊賢》、《雜言》等,都有關于此事的記載。《墨子·尚賢上》說:“湯舉伊尹于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尚賢下》又說:“昔伊尹為莘氏女師仆,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貴義》篇還有一則湯親自往見伊尹的故事,稱伊尹為“天下之賤人”。湯舉伊尹于庖廚之中的記載,在現存先秦典籍中,《墨子》是最早的,應是此故事的始作俑者。
墨子出身下層,極力稱頌德才兼備的“賤人”,認為“古者圣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尚賢上》)。伊尹的故事寄托著墨子的人生理想,也有以伊尹自比之意。孟子對這個故事很不屑,時人盛傳“伊尹以割烹要湯”,弟子萬章就此請教孟子,孟子斷然否定。他認為伊尹本為一處士,耕于有莘之野,深諳堯舜至道,湯使人三次迎聘,伊尹才答應出仕。孟子說伊尹是“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他認為圣人之所以為圣人,皆因能潔身自好,以庖廚要湯乃“辱己”,必非伊尹所為(《孟子·萬章上》)。孟子的道德評價同等級觀念緊密聯系在一起。墨家尚賢體現了下層人士干政的訴求,伊尹舉于庖廚的故事給儒家提倡的傳統禮制以很大的沖擊,孟子當然要堅決否定。儒墨兩家關于伊尹的出身爭持不下,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也不知何去何從,只好兩說并存,但他更偏向庖廚說,墨家的影響也可見一斑。
《漢書·藝文志》道家類有《伊尹》五十一篇,小說家類有《伊尹說》二十七篇,皆散佚不可考。魯迅以為《呂氏春秋·本味篇》述伊尹以至味說湯之事,就是小說《伊尹說》的片段,“伊尹以割烹要湯,孟子嘗所詳辯,則此殆戰國之士之所為矣”[12]15。《伊尹說》是戰國時代的作品,這是沒問題的,但具體的時代不詳。李劍國先生以為“其中羅列天下至味,不厭其詳,涉及許多山川動植,顯然也屬于戰國流行的地理博物傳說”[10]142,視《伊尹說》為戰國中晚期的作品,應是有道理的。《伊尹說》成于《墨子》之后,應與墨家有很深的淵源關系。墨家的尚賢思想在戰國深入人心,“湯舉伊尹于庖廚之中”的故事也廣為傳播,小說家在此基礎上又進行一番生動的演繹,最后完成《伊尹說》二十七篇,與墨家相呼應。《墨子》“說”體中的伊尹故事,與《伊尹說》互相影響,互相促成,二者的關系直接而密切。
《墨子》中的晏子,更是經過了加工改造的形象,是墨家的傳聲筒。
晏子大孔子二十幾歲,是孔子崇敬的人物,孔子曾說:“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論語·公冶長》)《左傳》載晏子言行甚多,是一個崇禮、尚德、具有民本意識的貴族。
墨子對晏子也推崇備至,《晏子春秋》保存著兩則墨子對晏子的贊語,如《問上》說:“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為人,而失在為己。為人者重,自為者輕。景公自為,而百姓不與,為人,而諸侯為役,則道在為人,而行在反己矣,故晏子知道。’”墨家后學身處儒墨相排相斥最為激烈的時代,他們就借晏子之口詆毀孔子。如《墨子·非儒下》借晏子之口誣陷孔子同犯上作亂、不仁不義的白公勝有勾結,為人與白公勝相同。此事之不實顯而易見,《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之楚事在哀公六年,而白公勝與石乞為亂在哀公十六年,時孔子已故。白公勝之亂,在齊景公卒后十二年發生,而晏子之卒更在齊景公之前,晏子生前哪里會預知楚國白公勝之亂,故孫詒讓引蘇時學說:“此誣罔之辭,殊不足辨。”[7]298
《非儒下》還說孔子見齊景公,景公欲封之以尼谿,晏子批評說:“夫儒,浩眉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晏子批評儒家靡財好樂、久喪循哀、弦歌鼓舞、禮儀煩瑣,與《墨子·公孟》篇對儒家的批評如出一轍,所以,《墨子》中的晏子與歷史上晏子本人并不相符,儼然是墨子的化身。《左傳·襄公十七年》記載晏子為父治喪,“晏嬰粗锿斬,苴經、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晏子所行子喪父之禮,與《儀禮》中《士喪禮》及《喪服》所述,沒有什么大的不同。楊伯峻說:“三年之喪,周代果有此事。然春秋已不實行,故晏嬰行之。”[15]1034晏子謹守三年之喪,躬行崇喪循哀,他并非如墨家所塑造的非樂、薄葬、反禮之人。所以,《墨子》“說”體中的晏子,乃是經過墨家后學喬裝打扮、改造虛構的人物。
晏子是春秋末期齊國著名的賢相,他勤政愛民,廉潔機智,深得時人的愛戴。晏子去世后,有關他的傳聞故事還廣為傳誦,墨家在這些傳聞軼事中發現符合墨家主張的因素,就加以推揚演繹,甚至按照自己的需要,改編虛構晏子的言行事跡,專門來非儒毀孔。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后來也收在《晏子春秋》一書中。《晏子春秋》中表現晏子衣食弊薄、蔽車駑馬等故事,多出墨家之手。柳宗元《辨〈晏子春秋〉》說:“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其言不若是。”[11]114此誠卓識。清人張純一說:“綜核晏子之行,合儒者十三四,合墨者十六七。”[16]1在晏子傳聞的基礎上虛構一些故事,作為論辯之資,墨家的創作,使得《晏子春秋》一書更接近于軼事小說的匯編。
墨家后學不僅抬出晏子來打壓孔子,也給孔子編排了許多故事進行污蔑。
除了說孔子與白公勝有勾結外,《非儒下》還說孔子一手導演了齊國田氏之亂:孔子未封于齊,遷怒于齊景公和晏子,就讓鴟夷子皮(即范蠡)為臥底,攪得天下大亂,齊、越失國,伏尸無數,種種罪過,皆出于孔子之謀。孫詒讓引蘇時學說:“據《史記》,范蠡之吳后,乃變易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然之吳之歲乃孔子卒后六年,景公卒后十七年,又安知蠡之適齊而樹之田氏之門乎?此與莊周所言孔子見盜跖無異,真齊東野人之語也。”[7]301《莊子》虛構孔子見盜跖,雖是對孔子的嘲諷,也不乏幽默的因素,其寓言性不言而明,但墨家編造的這些故事,卻有居心叵測的人身攻擊之嫌。
當然,墨家對孔子的編排并非憑空虛構,而是充分利用孔子的經歷進行改編虛構。如《非儒下》說:
孔某窮于陳、蔡之間,藜羹不糂。十日,子路為享豚,孔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號人衣以沽酒,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某曰:“來!吾語汝:曩與女為茍生,今與女為茍義。”孔子平時衣食頗為考究,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席不正,不坐。生活節儉、衣食樸素的墨家,自然對孔子的這種做派反感之極,故意用其厄于陳蔡時的狼狽來說事,讓孔子罵自己“茍生”、“茍義”,諷刺儒家“饑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贏飽則偽行以自飾”的虛偽。這樣的故事,人物真實,孔子厄于陳蔡也真有其事,“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之類的細節的確來自孔子,但總體的情節和對話皆是虛構,雖非有意為小說,現在來看,小說意味十足。
墨家首先拉開非儒毀孔的序幕,之后道家、法家等紛紛效仿,以此作為宣傳自己的手段,孔子與儒家受到空前的批判與否定,而孟子正生活在這樣的時代,捍衛儒家學說,維護孔子的至尊地位,孟子責無旁貸,所以他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力辟楊、墨,對墨家所杜撰的這些詆毀孔子的故事,也予以駁斥。如《墨子·非儒下》說:
孔某與其門弟子坐,曰:“夫舜見瞽叟孰然,此時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耶?何為舍亓家室而托寓也?”這段文字虛構孔子與其弟子妄議舜與周公。孟子弟子咸丘蒙就曾以此事向孟子求教,孟子說:“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孟子·萬章上》)孟子的辟墨,首先要對墨家虛構的這些故事進行駁斥、證偽,他把這些故事一概斥為“齊東野人之語”,很不屑地揭示出它們道聽途說的小說本質。
盡管孟子辟墨不遺余力,但墨家編排的故事,還是流傳廣泛,影響深遠。比如《呂氏春秋·精通篇》、《淮南子·道應訓》就有孔子與白公勝的問答,孔子與弟子妄議舜與周公的故事,就被《韓非子》拿來大做文章,其《忠孝》篇說:“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法家對這些故事也深信不疑,還作為批判孔子的口實,足見墨家非儒毀孔的影響之大。
先秦的名人軼事小說,圍繞某個歷史人物杜撰一些故事,數量可觀,篇幅短小,情節引人入勝,手法夸張,具有娛樂和教育意義,因多與史不符,被視為街談巷語、道聽途說,孔門弟子子夏稱其為“小道”:“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論語·子張》)班固《漢書·藝文志》把它直接當做孔子的話,用來評價小說家。儒家肯定小說的辨智,其奇足以動人聽聞,其巧則有一時之近效,但因其終非六籍正典之善道,故主張與之保持距離。墨家不僅在這些傳聞中尋求證據,資以為說,而且還參與到名人故事的改編創作當中。小說《伊尹說》、《晏子春秋》的創作與流傳,都與墨家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從某一程度來說,儒墨之爭最具火藥味的地方,正體現在對“說”體故事的真偽論辯之上。
墨家把名人軼事作為論辯的武器,還加工、改編或虛構一些名人的故事,本出于壯大門派、打壓別人的目的,但在文學上卻引發了戰國諸子軼事小說的創作高潮,之后的《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都不約而同效仿墨家,或采舊說,或創新作,對先秦軼事小說的繁榮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飾小說以干縣令”(《莊子·外物》)的風氣,實始于墨家。
四、結語
《墨子》“說”體故事中所引諸國《春秋》,與儒家經典中的《春秋》及《左氏春秋》大相徑庭,它們是古代“明神之志”、“天鬼之志”類的志怪野史,是先秦志怪小說的早期作品。以儒家正統眼光來看,顯得頗有“異端”的色彩,但先秦志怪小說的一些片段,卻有賴《墨子》的“說”體而保存下來,后人可以借此管窺先秦志怪小說的內容和風格。
對志怪與名人軼事的援引,頗能體現墨家的本色和對先秦小說的貢獻,這些內容被孟子斥為“齊東野人之語”(《孟子·萬章上》),被荀子定為“淺者之傳,陋者之說”(《荀子·正論》),但在墨家手里變成論辯的武器。《墨子》開啟了“飾小說以干縣令”的風氣。《墨子》借重名人打壓孔子,用捕風捉影的故事詆毀孔子,這種做法為《莊子》、《韓非子》等發揚光大,成為各家非儒毀孔的常用手段。墨家拉開了百家爭鳴的序幕,也開啟了雜家小說創作的精彩紛呈。墨家本身尚質,不追求文辭的華美動人,但《墨子》對先秦小說的貢獻,卻正體現在其“說”體故事上。
戰國百家爭鳴的歷史環境造就了雜家小說的繁榮。《漢書·藝文志》認為小說“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所造也”,這只揭示了一部分小說的創作情況,也有相當數量的小說是應諸子論辯的需要而創作的,明人胡應麟的“小說,子書者流”[8]374的說法從某種程度揭示了諸子同小說家的依存關系。班固對此認識不足,所以他又說:“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這也是低估了戰國時代小說家的作用和影響,忽略了小說作為諸子論辯的利器的這一事實。從《墨子》說”體與先秦小說的關系可知,戰國諸子同小說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諸子論辯爭鳴的背后,從來沒有離開小說家的身影。
注釋:
①廖群先生在《“說”、“傳”、“語”,先秦“說體”考索》(《文學遺產》2006年第6期)一文中,認為先秦曾存在一種以講述故事為主旨的敘事文體,被時人稱為“說”、“傳”、“語”,鑒于與小說的關系,故統稱為“說體”。廖群先生把諸子“說”的來源記載稱為“說”體,而本文之“說”體是指諸子“說”中所有的敘事性材料,本文與廖群先生“說”體所指對象稍異。
【參考文獻】
[1]鄭良樹.韓非之著述及思想[M].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
[2]陸林.試論先秦小說觀念[J].安徽大學學報,1996, (6).
[3]向宗魯.說苑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7.
[4]徐克謙.論先秦“小說”[J].社會科學研究,1998, (5).
[5]魏征,等.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6]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7]孫詒讓.墨子間詁[M].北京:中華書局,2001.
[8]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M].北京:中華書局,1985.
[9]浦起龍.史通通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0]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11]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9.
[1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13]王恒展.《墨子》與中國小說[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04, (3).
[14]羅國威.《冤魂志》校注[M].成都:巴蜀書社,2001.
[15]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0.
[16]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M].諸子集成(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