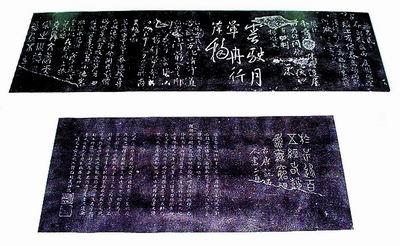-
沒有記錄!
張公巷:千年一喚醒
2013/12/7 10:40:01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在汝州市,張公巷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小巷。它像一條歷經滄桑的臥龍含辱夢垢地卷曲在灰色的老城之中,千百年來酣睡不醒。
2004年5月22日,從鄭州“張公巷窯考古新發現研討會”上傳來消息:汝州張公巷窯就是北宋官窯!千年一喚醒:張公巷終于抖落了歷史覆蓋在身上的塵埃,呼嘯一聲,騰飛太空!
二
對于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大多汝州人而言,“張公巷”名字的由來并不十分清楚。自從它一鳴驚人之后,關注它的人們越來越多。我查《汝州市志》得知:張公巷是因一個叫張維新的名人而得名的。張維新是明汝州東大街人。曾任山東冠縣(今聊城)縣令,后因政績突出升為給事中。他不阿權貴,敢于對社會弊端條陳上疏,向皇帝直述己見,促進了朝政改革。他提出的“改納折色”(把應納的糧不往北京運,而折成銀子就地交納,把銀子運往北京再買糧)和“互相代納”兩種辦法,既利國又利民,得到了朝廷的重用。張維新一生留下很多詩作,晚年和知州方應選和編出版了《汝州志》。張病故家鄉后,族人為他立了祠堂,他居住的那條街也因此被叫做“張公巷街”。
過去,張公巷因張公而得名,而今,張公巷因發現了宋官窯遺址而名揚天下。我每次去看張公巷的宋官窯遺址,思緒的野馬總要脫韁而去,它羈傲不馴地馱著我——一個鐘情于地域文化的現代人,四蹄飛舞,一頭鉆進了遙遠的歷史霧靄之中——
北宋是我國歷史上頗為輝煌的時期,中國陶瓷至此已發展到鼎盛階段。蜚聲中外的五大名瓷:“汝、官、鈞、哥、定”,更是爭奇斗艷,各領風騷。特別是由官窯燒造的貢御瓷器,獨壓群芳,不但工藝先進,而且制作精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
那時候的張公巷并不叫張公巷,是州衙外的一塊野地,并無人煙。忽一天這里熱鬧起來,一批出類拔萃的汝窯匠被秘密押來,方圓數里不但圈起了圍墻,而且還有重兵看守。不久,這塊野地的上空冒起了濃煙……
北宋晚期的宋徽宗是個“才子皇帝”,他不僅擅長筆墨書畫,而且還是一位好古成癖、崇尚自然含蓄和清淡質樸的道學家。他以“定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之后的某一天,忽然又心血來潮,特命建造皇家官窯,專為宮廷燒造御用瓷器。在追新求異的宋徽宗的“關愛”下,一個震古鑠今、彰顯尊貴奢華與皇室風范的新瓷器在汝州衙外誕生了……
北宋官窯把精美絕倫的官瓷技藝與典雅莊重的宮廷藝術巧妙融為一體,造型多仿秦漢古銅器、玉器,結構規整,棱角挺拔,古樸莊重,氣魄宏偉,造型卻區別于古銅器、玉器,蒼古幽雅,氣度不凡,其釉色潤美似玉,開片嶙嶙如波在裝飾藝術上,塑造追求天然,加之“紫口鐵足”的典型特征,其燒造技術和藝術境界達到了我國青瓷史上的又一高峰。
可惜的是一代名窯毀于戰火。金兵入侵,存世僅有18個春秋的官瓷在金兵鐵蹄下化為齏粉。由于燒造時間段,加之燒造的瓷器僅供宮廷使用,嚴禁流入民間,所以北宋官窯瓷器存世稀少,成為陶瓷界注目的焦點和世界各博物館爭相收藏的寶物。
一場戰火把北宋官窯的歷史燒斷了800年,歷史的塵埃把古窯遺址深埋起來。
800年,一個遙遠而漫長的歷程,當流動的歷史走到北宋官窯時,常讓人感到無奈和尷尬,因為歷史隱去了足跡。隨著歷史的推移,北宋五大名窯的哥、定、鈞窯遺址都相繼露出了神秘的面容,就連被考古界稱為千古懸案的汝官窯遺址也終現崢嶸,獨有官窯遺址一直不肯向世人露出芳容。
考古界在艱難的尋覓中苦苦的企盼著……
三
如今,北宋官窯終于沖破歷史的塵封,抖落了神秘的面紗,露出了千年一現的容顏。
張公巷醒了!
夢醒當謝醒夢人。那個首先驚醒她酣夢的人是“瓷癡”朱文立。朱文立曾因成功恢復了汝官瓷燒造技術而揚名中外,并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寶豐清涼寺汝官窯遺址發現后,朱文立根據自己多年來對汝官窯的調查和研究認為:北宋汝官窯應在便于朝廷管理的州衙附近。為此,他在仿燒汝官瓷的同時,又在汝州城內苦苦的尋找他心中的的汝官窯遺址。
10年尋覓不尋常。從1989年開始,無論誰家蓋房,朱文立總要守候在現場,有時還要拿起鐵锨翻土尋找。不知內情的人說他是一個“神經蛋”。2000年春的一天,張公巷一居民在院內見新房,朱文立在挖掘現場撿到了數十件典型的窯具,有盤式、桶式、漏斗式的。這些發現佐證了自己多年的猜想:這里是宋代的一個窯址,他和文化局的領導一起向省文物局匯報。省文物局委托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來調查挖掘。這次挖掘出土了一些瓷片和窯具。初步斷定它是一處窯址。2001年2月10日,市長丁少青在北京邀請陶瓷專家舉行汝官窯遺址研討會,專家一致認為在張公巷挖掘出的瓷片是汝窯瓷片。緊接著朱文立又帶著瓷片來到上海博物館。副館長、研究員、古陶瓷專家汪慶正等反復對瓷片進行了研究和比照,認為汝州張公巷出土的汝瓷片和 世界上僅有的現存上海博物館的4塊青釉標本是同一窯場、同一類型的產品。汪慶正萬分高興地說:上海博物館珍藏的4塊青釉標本終于在張公巷找到了娘家。汪慶正首次提出了張公巷窯可能是北宋官窯。
然而,歷史不能靠想象去補充,在對待歷史時我們只能采取嚴謹的態度。
二次挖掘開始了。張公巷窯址在一步步的挖掘中日益逼近了本真。
2001年5月,居住在張公巷1號的居民高某家翻建新房,文物部門前去鉆探,在該院內鉆出了一些素燒胎片。在北墻根的一棵樹下又出土來了60多片素燒胎片。通過證實性鉆探,又發現了比2000年春更為豐富的瓷片和窯具等,并發現了不明顯的作坊遺跡和較多的素燒坯碎片。二次挖掘證明了張公巷窯遺址的存在。
三次挖掘,張公巷展露輝煌。從2004年2月8日開始,省文物部門在張公巷1號與張公巷一路之隔的汝州中大街兩個居民院里同時開始了發掘。為了不漏過任何蛛絲馬跡,專家規定,每鏟土都要過篩子。雖然發掘面積不大,僅古錢幣就有330多枚。
經過一個多月的發掘,終于出現了驚人的景觀:在3號探方第六文化層發現了張公巷窯生產的青釉瓷堆積,其中一個灰坑內出土了能復原的青瓷器44件,彌足珍貴。接著,又在4號坑內發現了大量堆集制坯原料,地層里又出現了唯一的一件保存完整的骨質修坯工具。并發現了大量的匣缽。
驚人的發現,令世人矚目。
2004年5月22日,中外48位專家和學者聚首張公巷,對張公巷古窯遺址進行認定,初步判斷:張公巷就是陶瓷考古界苦苦尋覓許多年的的北宋官窯遺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孫新民向與會專家介紹說:青釉瓷是張公巷窯燒制的唯一產品。從整體上看,它既不同于臨汝窯的豆綠釉,也有別于寶豐清涼寺窯的天青色,釉色可分為卵青、淡青、灰青、青綠和天青等。出土的窯具以匣缽、墊圈為主。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匣缽外壁涂抹耐火泥 的部分占60%左右,這種工藝僅見于寶豐清涼寺汝窯,支燒工藝也于汝窯一致,這說明張公巷窯的燒造工藝來源寶豐清涼寺窯。張公巷窯燒制的產品制作講究,質量上乘,顯然不是一般的民間用瓷,它的性質是官窯。
中國古陶瓷學會會長、上海博物館副官長汪慶正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發言說:認定張公巷窯址為北宋官窯有兩個依據,一是它不同于汝窯(清涼寺);二是它與南宋官窯是傳承關系。從張公巷出土的瓷片來看,它有別于汝窯瓷片。一是瓷片的胎里含錳少,胎質比汝窯白;二是釉總體上來說呈乳濁狀,比汝窯的厚點;三是出現了較多的圓形支釘痕,汝窯為芝麻支釘痕;四是瓷片上的開片魚鱗紋較多。這就與南宋官窯聯系起來了,在杭州發現的修內司官窯和郊臺下官窯的瓷器上有圓形支釘痕,還有大量的魚鱗紋瓷片。這說明南宋官窯是從北宋官窯演變而來的,而北宋官窯的前身就是汝窯。張公巷出土的這批東西,除了官窯之外一般民窯絕不會有。這樣一來,就形成了這樣一個鏈條:汝窯(清涼寺)——北宋官窯(張公巷)——南宋的修內司官窯——南宋的郊臺下官窯。
四
醒來的張公巷名揚四海。
我想:張公巷北宋官窯遺址的發現,豐富了中國古代青瓷的內涵,還為破解北宋官窯的“千古之謎”找到了有力的證據。北宋官窯遺址在汝州的發現,豐富了汝州的文化內涵,為古老的汝州成為歷史文化名城增添了一抹亮色。隨著張公巷遺址的進一步發掘、保護和利用,這筆無形文化資產將為推動我市經濟發展起到巨大的作用。
當筆者結束此文時,又一個令汝州人歡呼雀躍的喜訊傳來:張公巷北宋官窯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第六批國保單位,這是繼家鄉風穴寺之后的第二個國保單位。汝州又有了一張厚重、晶亮、耀眼的歷史文化名片。
2006年3月12日修改定稿。【原標題:張公巷:千年一喚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