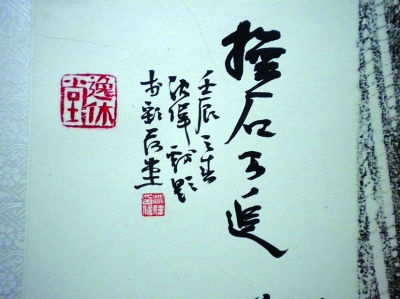-
沒有記錄!
什么樣的藝術品才值得收藏(2)
2013/11/20 15:34:06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徐志興:文人畫暢神抒情,不一定非要郁悶的時候才畫得出來。就像趙孟頫,他完全沉醉在自己的藝術當中,他通過文人畫抒發情感,表現自己對中國畫的美學取向。
我覺得中國畫的美從孔子時代就奠定了,那就是“真善美”,后來的文人畫都是以“真善美”來奠定基礎的。真善美如何表現呢?它需要畫家的情、意、神和客觀事物相融合在一起才能表現出來。就像鄭板橋畫竹子,他的題畫詩就寫到“疑似民間疾苦聲”,他聽到竹子的聲音就好像聽到民間疾苦的聲音,一枝一葉總關情,這說明他是關心勞苦大眾的,他的繪畫不單純是一種筆墨游戲,他通過筆墨表現的是他的情。在他看來,竹子是高潔的、積極向上的,人也應該如此。這就是中國古代強調的“天人合一”,是文人畫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國畫的最高境界。如果從王維開始,把各個朝代主要的文人畫畫家排除在外,那么中國美術史恐怕就缺失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豐富內容。
文人畫VS院體畫
趙利平:與“文人畫”這個概念相對應的是“院體畫”,對這兩種繪畫形式的爭論從古至今一直沒停過。從目前藝術品市場的受歡迎程度來看,價格最高的是齊白石等人的文人畫,但名氣不高的文人畫卻很難得到市場的承認,反倒是相對“匠氣”的院體畫更好賣。
劉斯奮:院體畫,我想絕大多數人都能欣賞,而文人畫想人人都能欣賞就比較難,即使是齊白石、黃賓虹的作品,如果不是他們的藝術地位已成為定評,恐怕照樣沒有多少人要。拿一張工筆畫和一張寫意畫讓老百姓挑選,絕大多數人選的還是工筆畫。因為對于超越技術層面的形而上的精神追求,總是不容易被廣泛理解和接受。但一部藝術史的“高度”,卻恰恰是由這一部分藝術家支撐起來的。歷史已經證明了,追求廣度往往必須放棄高度,而若立志追求高度,就不必太注重市場。
趙利平:文人畫和院體畫最大的區別在哪里?
劉斯奮:院體畫最初是為了滿足王公貴族的審美需要而產生的,畫面富麗堂皇,作畫認真仔細,還一定要偏寫實,這三大特點就形成了院體畫的主要特征。
院體畫的局限在于其創作模式的固定化。朝廷網羅的院體畫畫匠肯定也是民間的優秀人才,但他們一旦進入畫院,勢必要迎合王公貴族的審美趣味,個性發揮空間受到擠壓,結果整個畫風就不知不覺趨同了。技術上確是精益求精,甚至令人嘆為觀止,但較少創新和突破也是事實。它不像文人畫能夠了無拘束,發揮個性,大膽創新。兩相比較,院體畫可說是更偏重“技”,而文人畫更偏重“道”。當然文人畫決不等于可以亂畫一氣,而是絕對需要更高的藝術天賦和原創能力,不可以濫竽充數。
徐志興:但在藝術的提升上,院體畫也是功不可沒的。就像戴進、吳偉,他們的繪畫也帶有鮮明的個人風格,不能說毫無價值。潘天壽在吸取古代繪畫精華的過程中,對馬夏的院體畫就情有獨鐘,他認為南宗和北宗如果各取其長,豈不是更好?所以繪畫有時候也應該取長補短。
趙利平:現在院體畫和文人畫的界限好像不是很明顯了。
劉斯奮:院體畫本來就是體制內產生的,肯定要受到體制的制約。現在時代不同了,思想比較解放,在畫院里的畫家也完全可以畫大寫意,雖然也有一定的制約,但是相比古代的制約要少得多。
徐志興:的確是時代變了,你看浙江美院出了潘天壽,中央美院出了李苦禪、李可染,這些都是大寫意的高手。
周國城:但大寫意很難拿到專業美展的大獎。當然,我也不是說那些拿金獎的畫就不好,這些花了幾年工夫畫出來的一幅作品自然有其優點,但是這樣的作品,畫家一輩子能夠畫出多少?一個畫家如果一輩子不能留下大量的作品,這樣的畫家是難成大氣候的。例如,齊白石、吳昌碩等,他們有現在這么高的地位,絕對不是因為他們的一兩幅代表作,而是他們的整個藝術人生。所以現在很多美展上獲獎的青年畫家,大家經常都記不住名字,就因為除了獲獎的那一張畫,他們能讓人記住的作品實在太少了。
文人畫面臨消亡還是前途無量?
趙利平:作為一種文化遺產,在社會發生翻天覆地巨大變化的今天,文人畫還有沒有弘揚光大的必要?它是否還具備現代性意義?
劉斯奮:“文人”作為曾經的一個社會階層已經消亡,現在已經不可能產生以前那個時代的那種文人了。以前沒有一個畫家從小就想當一個文人畫畫家的,他們想的都是飽讀詩書,通過科舉入朝為官。后來一些科舉沒考上的人就開始畫畫了,當官了的在業余時間也畫畫,他們的文化底蘊是從小就積累下來的,不僅書法要寫得好,儒家經典、詩詞歌賦更要爛熟于心,現在這種人在美術界不能說沒有,恐怕也很少了。所以我們現在談文人畫就不要強調身份,而是要就傳統來談。
首先,文人畫的精神是完全可以繼承、發揚的。譬如深厚的文化素養,琴棋書畫的積累,現代人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又譬如在精神方面的哲理思考,形而上的追求,現代人也是可以培養的;最后是文人畫的創新精神、個性發揮,這也是現代人所追求的。如果能繼承到這些,就繼承了中國文人畫的優良傳統。至于怎么畫,我倒不主張一定要詩書畫印全部精通,精神相比形式來得更加重要,我覺得這就是當代文人畫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