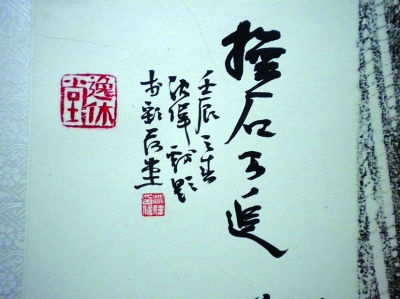熱點(diǎn)關(guān)注
專題推薦
-
沒有記錄!
熱點(diǎn)排行
岑參“詩化”西域史
2014/12/9 13:41:36 點(diǎn)擊數(shù): 【字體:大 中 小】
唐代詩人岑參兩次入疆,所著西域詩篇甚多,其價(jià)值不囿于文學(xué)一途,也進(jìn)入了歷史學(xué)、史地學(xué)的研究視野。野澤俊敬曾勾勒出岑參筆下的 “玉門故關(guān)、赤亭、火山、西州、銀山、焉耆、鐵門、龍泉(漢輪臺(tái))、安西、熱海”、“玉門關(guān)、瓜州(安西)、伊州、輪臺(tái)、陰山”等路線,涵括了唐代西域的重要地理節(jié)點(diǎn)。嚴(yán)耕望考察河隴磧西道路時(shí),將岑參詩中記錄的西北行程作為重要參考:“唐人行旅所經(jīng)之能詳考者,莫過于玄奘與岑參。”岑參西域詩的寫實(shí)固然與作者親歷邊疆、從軍塞外的經(jīng)歷有關(guān),同時(shí)也是其西域詩的史學(xué)特質(zhì)所決定的。
詩化的歷史實(shí)錄
與同時(shí)期唐詩中“天山、陰山、瀚海、大漠”等西域意象不同,岑參西域詩中的地名多是實(shí)指。《天山雪歌》、《銀山磧西館》所錄“銀山、銀山館、銀山峽”,《新唐書·地理四》云“西州交河郡……二百二十里至銀山磧,四十里至焉耆界呂光館。”再如《火山云歌送別》中的“赤亭口”,在《新唐書·地理四》中有:“伊州伊吾郡……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與伊西路合。”《吐魯番出土文書》多冊(cè)中也都錄有“赤亭、赤亭坊、赤亭館、赤亭鎮(zhèn)、赤亭烽”。這使岑參詩看上去更像是詩化了的記行之作。
地名的真實(shí)性還不足以彰顯其詩的史地學(xué)特征,更重要的這些地名往往以路線方式組合起來。如《經(jīng)火山》、《銀山磧西館》、《早發(fā)焉耆懷終南別業(yè)》、《題鐵門關(guān)樓》、《宿鐵西關(guān)館》、《安西館中思長(zhǎng)安》,組成了西州至安西的行程線。《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yíng)便呈高開府》中的熱海(蒲昌海)—鐵門(鐵門關(guān))—火山(火焰山),昆侖—蒲昌(羅布泊)—樓蘭(羅布泊西北岸)—交河(吐魯番)—赤亭(七克臺(tái))又構(gòu)成了絲綢之路北道。詩題可看做紀(jì)行組詩,但具體到詩中涉及的地理名稱也依照路線的先后次序出現(xiàn),可以看出詩人在文學(xué)想象的同時(shí),也重視真實(shí)記錄歷史。正因如此,岑參西域詩才擁有了史學(xué)實(shí)錄性。
需提醒的是,岑詩的真實(shí)記錄仍是建立在詩歌的藝術(shù)加工上的,其中也有作者的主觀創(chuàng)造成分,試舉 “輪臺(tái)”為例。《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云:“輪臺(tái)縣,長(zhǎng)安二年置。”《舊唐書·地理志三·隴右道》云:“輪臺(tái),取漢輪臺(tái)為名。”唐在今烏魯木齊附近設(shè)置過輪臺(tái)縣,與漢代輪臺(tái)重名,岑參詩中的“輪臺(tái)”究竟何指,曾引發(fā)眾多學(xué)者爭(zhēng)論,其結(jié)論有“米泉”、“烏拉泊古城”、“昌吉”、“吉木薩爾”等,未有定讞。這正是過于強(qiáng)調(diào)岑詩的寫實(shí)性,忽略了詩歌文學(xué)性的結(jié)果。在《登北庭北樓呈幕中諸公》中,岑參自敘喜好“輪臺(tái)”的原因:“嘗讀《西域傳》,漢家得輪臺(tái)。”《漢書·張騫李廣利列傳》記載李廣利伐大宛,攻打輪臺(tái):“至輪臺(tái),輪臺(tái)不下,攻數(shù)日,屠之。”足見漢家得“輪臺(tái)”不易。唐代詩人多有報(bào)國(guó)封侯的宏愿,岑參遠(yuǎn)赴西域,也是如此。不論是《送李副使赴磧西官軍》中的“知君慣度祁連城,豈能愁見輪臺(tái)月……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還是《臨洮泛舟,趙仙舟自北庭罷使還京》中的“白發(fā)輪臺(tái)使,邊功竟不成”,應(yīng)都與功業(yè)相關(guān),不指實(shí)際地名,代指建功立業(yè)的場(chǎng)所。
文學(xué)細(xì)節(jié)中的歷史真實(shí)
岑參西域詩在記錄地名的同時(shí),還描述了自然地理風(fēng)貌。其《經(jīng)火山》有:“我來嚴(yán)冬時(shí),山下多炎風(fēng)。人馬盡汗流,孰知造化功。”今天吐魯番冬季平均溫度大約是零下8攝氏度。學(xué)界普遍認(rèn)為唐代的氣溫較今略高,但仍不足以造成炎風(fēng)、汗流。對(duì)此,學(xué)者考證認(rèn)為,8世紀(jì)上半葉,新疆哈密大南湖至鄯善沙爾湖間,存在煤炭自燃帶。地下煤炭一燃燒,很難熄滅。岑參自附近路過,人馬汗流是符合實(shí)際情況的,詩中細(xì)節(jié)為我們提供了一幅直觀的歷史畫面。
同樣是奇景的 “熱海”就值得商榷了。岑詩《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作于天寶十三載 (754),《新唐書·地理志下》對(duì)“熱海”的位置有詳細(xì)記錄,指位于碎葉城與怛羅斯城北的高山湖泊伊塞克湖(今吉爾吉斯境內(nèi)),唐時(shí)稱 “大清池”。《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說明了“熱海”得名之由:“清池亦云熱海,見其對(duì)凌山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溫也。”
“熱海”就是“不凍湖”,湖水鹽分大,冬季不易結(jié)冰,《大唐西域記》注 “大清池”云:“或名熱海,有謂咸海。”水尚且不溫,何談沸熱?岑詩描述的景象與實(shí)情差距很大:“側(cè)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海上眾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zhǎng)且肥。岸旁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遙旋滅。蒸沙爍石燃虜云,沸浪炎波煎漢月。”
天寶十載,高仙芝兵敗怛羅斯,唐中央政府已失去了對(duì)蔥嶺以西的控制能力,岑參此后親歷伊塞克湖地區(qū)頗為困難。因此,詩中首句就表明“熱海”情況是“側(cè)聞”而來,真實(shí)性自然不足。但詩后半部又說:“陰火潛燒天地爐,何事偏烘西一隅?勢(shì)吞月窟侵太白,氣連赤坂通單于。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見夕陽海邊落。柏臺(tái)霜威寒逼人,熱海炎氣為之薄。”似乎又確實(shí)在“熱海”邊送別。
解決這個(gè)矛盾,還是要將詩歌的藝術(shù)真實(shí)和歷史事實(shí)結(jié)合起來討論。詩的前半段所描述的熱海,是藝術(shù)加工,既然是來自胡兒的傳聞,表明作者未至“西頭熱海”(伊塞克湖)。真正的送別之地,是詩中的“月窟”。《獻(xiàn)封大夫破播仙凱歌六章》其二:“官軍西出過樓蘭,營(yíng)幕傍臨月窟寒。蒲海曉霜凝馬尾,蔥山夜雪撲旌竿。”“月窟”的位置很明白,即樓蘭南部的蒲昌海。《漢書·西域傳》:“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與伊塞克湖一樣,蒲昌海也是高鹽分的“不凍湖”。
蒲昌海是絲綢之路北道的一站,處在中央王朝的管理下,在這里送使者東歸,符合邏輯。岑參夸大西頭熱海的描述,為后文鋪墊:“何事偏烘西一隅?”暗喻天寶十載后西域的局面,而主兵事的“太白”金星說明戰(zhàn)事或會(huì)影響到蒲昌海地區(qū),但只要朝廷御史仍在邊疆巡查,則“炎氣”可降,戰(zhàn)火可熄。
岑參西域詩是唐代西域歷史地理的側(cè)寫,也是研究西北史地的重要資料。通過對(duì)岑詩中歷史地名的考辨,有利于我們還原天寶年間封常清統(tǒng)領(lǐng)安西、北庭的重要?dú)v史事件。在岑參西域詩中構(gòu)建史學(xué)和文學(xué)的雙重分析視角,會(huì)為研究拓展出新的視域。作者:夏國(guó)強(qiáng)
作者單位:新疆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暨西域文史研究中心
詩化的歷史實(shí)錄
與同時(shí)期唐詩中“天山、陰山、瀚海、大漠”等西域意象不同,岑參西域詩中的地名多是實(shí)指。《天山雪歌》、《銀山磧西館》所錄“銀山、銀山館、銀山峽”,《新唐書·地理四》云“西州交河郡……二百二十里至銀山磧,四十里至焉耆界呂光館。”再如《火山云歌送別》中的“赤亭口”,在《新唐書·地理四》中有:“伊州伊吾郡……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與伊西路合。”《吐魯番出土文書》多冊(cè)中也都錄有“赤亭、赤亭坊、赤亭館、赤亭鎮(zhèn)、赤亭烽”。這使岑參詩看上去更像是詩化了的記行之作。
地名的真實(shí)性還不足以彰顯其詩的史地學(xué)特征,更重要的這些地名往往以路線方式組合起來。如《經(jīng)火山》、《銀山磧西館》、《早發(fā)焉耆懷終南別業(yè)》、《題鐵門關(guān)樓》、《宿鐵西關(guān)館》、《安西館中思長(zhǎng)安》,組成了西州至安西的行程線。《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yíng)便呈高開府》中的熱海(蒲昌海)—鐵門(鐵門關(guān))—火山(火焰山),昆侖—蒲昌(羅布泊)—樓蘭(羅布泊西北岸)—交河(吐魯番)—赤亭(七克臺(tái))又構(gòu)成了絲綢之路北道。詩題可看做紀(jì)行組詩,但具體到詩中涉及的地理名稱也依照路線的先后次序出現(xiàn),可以看出詩人在文學(xué)想象的同時(shí),也重視真實(shí)記錄歷史。正因如此,岑參西域詩才擁有了史學(xué)實(shí)錄性。
需提醒的是,岑詩的真實(shí)記錄仍是建立在詩歌的藝術(shù)加工上的,其中也有作者的主觀創(chuàng)造成分,試舉 “輪臺(tái)”為例。《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云:“輪臺(tái)縣,長(zhǎng)安二年置。”《舊唐書·地理志三·隴右道》云:“輪臺(tái),取漢輪臺(tái)為名。”唐在今烏魯木齊附近設(shè)置過輪臺(tái)縣,與漢代輪臺(tái)重名,岑參詩中的“輪臺(tái)”究竟何指,曾引發(fā)眾多學(xué)者爭(zhēng)論,其結(jié)論有“米泉”、“烏拉泊古城”、“昌吉”、“吉木薩爾”等,未有定讞。這正是過于強(qiáng)調(diào)岑詩的寫實(shí)性,忽略了詩歌文學(xué)性的結(jié)果。在《登北庭北樓呈幕中諸公》中,岑參自敘喜好“輪臺(tái)”的原因:“嘗讀《西域傳》,漢家得輪臺(tái)。”《漢書·張騫李廣利列傳》記載李廣利伐大宛,攻打輪臺(tái):“至輪臺(tái),輪臺(tái)不下,攻數(shù)日,屠之。”足見漢家得“輪臺(tái)”不易。唐代詩人多有報(bào)國(guó)封侯的宏愿,岑參遠(yuǎn)赴西域,也是如此。不論是《送李副使赴磧西官軍》中的“知君慣度祁連城,豈能愁見輪臺(tái)月……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還是《臨洮泛舟,趙仙舟自北庭罷使還京》中的“白發(fā)輪臺(tái)使,邊功竟不成”,應(yīng)都與功業(yè)相關(guān),不指實(shí)際地名,代指建功立業(yè)的場(chǎng)所。
文學(xué)細(xì)節(jié)中的歷史真實(shí)
岑參西域詩在記錄地名的同時(shí),還描述了自然地理風(fēng)貌。其《經(jīng)火山》有:“我來嚴(yán)冬時(shí),山下多炎風(fēng)。人馬盡汗流,孰知造化功。”今天吐魯番冬季平均溫度大約是零下8攝氏度。學(xué)界普遍認(rèn)為唐代的氣溫較今略高,但仍不足以造成炎風(fēng)、汗流。對(duì)此,學(xué)者考證認(rèn)為,8世紀(jì)上半葉,新疆哈密大南湖至鄯善沙爾湖間,存在煤炭自燃帶。地下煤炭一燃燒,很難熄滅。岑參自附近路過,人馬汗流是符合實(shí)際情況的,詩中細(xì)節(jié)為我們提供了一幅直觀的歷史畫面。
同樣是奇景的 “熱海”就值得商榷了。岑詩《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作于天寶十三載 (754),《新唐書·地理志下》對(duì)“熱海”的位置有詳細(xì)記錄,指位于碎葉城與怛羅斯城北的高山湖泊伊塞克湖(今吉爾吉斯境內(nèi)),唐時(shí)稱 “大清池”。《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說明了“熱海”得名之由:“清池亦云熱海,見其對(duì)凌山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溫也。”
“熱海”就是“不凍湖”,湖水鹽分大,冬季不易結(jié)冰,《大唐西域記》注 “大清池”云:“或名熱海,有謂咸海。”水尚且不溫,何談沸熱?岑詩描述的景象與實(shí)情差距很大:“側(cè)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海上眾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zhǎng)且肥。岸旁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遙旋滅。蒸沙爍石燃虜云,沸浪炎波煎漢月。”
天寶十載,高仙芝兵敗怛羅斯,唐中央政府已失去了對(duì)蔥嶺以西的控制能力,岑參此后親歷伊塞克湖地區(qū)頗為困難。因此,詩中首句就表明“熱海”情況是“側(cè)聞”而來,真實(shí)性自然不足。但詩后半部又說:“陰火潛燒天地爐,何事偏烘西一隅?勢(shì)吞月窟侵太白,氣連赤坂通單于。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見夕陽海邊落。柏臺(tái)霜威寒逼人,熱海炎氣為之薄。”似乎又確實(shí)在“熱海”邊送別。
解決這個(gè)矛盾,還是要將詩歌的藝術(shù)真實(shí)和歷史事實(shí)結(jié)合起來討論。詩的前半段所描述的熱海,是藝術(shù)加工,既然是來自胡兒的傳聞,表明作者未至“西頭熱海”(伊塞克湖)。真正的送別之地,是詩中的“月窟”。《獻(xiàn)封大夫破播仙凱歌六章》其二:“官軍西出過樓蘭,營(yíng)幕傍臨月窟寒。蒲海曉霜凝馬尾,蔥山夜雪撲旌竿。”“月窟”的位置很明白,即樓蘭南部的蒲昌海。《漢書·西域傳》:“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與伊塞克湖一樣,蒲昌海也是高鹽分的“不凍湖”。
蒲昌海是絲綢之路北道的一站,處在中央王朝的管理下,在這里送使者東歸,符合邏輯。岑參夸大西頭熱海的描述,為后文鋪墊:“何事偏烘西一隅?”暗喻天寶十載后西域的局面,而主兵事的“太白”金星說明戰(zhàn)事或會(huì)影響到蒲昌海地區(qū),但只要朝廷御史仍在邊疆巡查,則“炎氣”可降,戰(zhàn)火可熄。
岑參西域詩是唐代西域歷史地理的側(cè)寫,也是研究西北史地的重要資料。通過對(duì)岑詩中歷史地名的考辨,有利于我們還原天寶年間封常清統(tǒng)領(lǐng)安西、北庭的重要?dú)v史事件。在岑參西域詩中構(gòu)建史學(xué)和文學(xué)的雙重分析視角,會(huì)為研究拓展出新的視域。作者:夏國(guó)強(qiáng)
作者單位:新疆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暨西域文史研究中心
責(zé)任編輯:C009文章來源: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報(bào)(2014-04-23)
下一條:沒有了上一條:漢代已有地圓說 張衡曾認(rèn)為地球如同蛋黃浮在宇宙
相關(guān)信息
沒有記錄!
精彩展示
沒有記錄!
評(píng)論區(qū)
友情鏈接
商都網(wǎng)
中國(guó)網(wǎng)河南頻道
印象河南網(wǎng)
新華網(wǎng)河南頻道
河南豫劇網(wǎng)
河南省書畫網(wǎng)
中國(guó)越調(diào)網(wǎng)
中國(guó)古曲網(wǎng)
博雅特產(chǎn)網(wǎng)
福客網(wǎng)
中國(guó)戲劇網(wǎng)
中國(guó)土特產(chǎn)網(wǎng)
河南自駕旅游網(wǎng)
中華姓氏網(wǎng)
中國(guó)旅游網(wǎng)
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藝術(shù)網(wǎng)
族譜錄
文化遺產(chǎn)網(wǎng)
梨園網(wǎng)
河洛大鼓網(wǎng)
剪紙皮影網(wǎng)
中國(guó)國(guó)家藝術(shù)網(wǎng)
慶陽民俗文化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