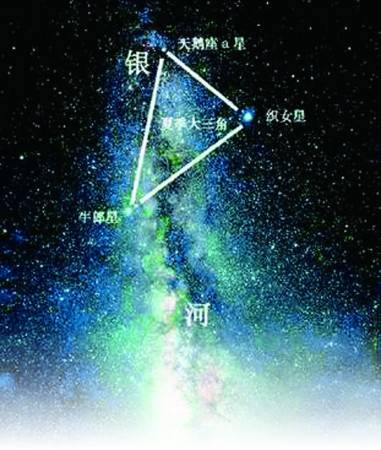精彩推薦
熱點關注
- 1、鈞瓷發展經歷的幾個重要階段
- 2、***鳳凰臺 一座新城的崛起
- 3、比賽競技顯風采,象棋文化得發揚
- 4、鈞窯瓷器的價值
- 5、王莽趕劉秀在魯山留下趣名趣事
- 6、金水河:繁華穿城而過
- 7、商丘古城里的“鬧龍街”
- 8、相思樹
專題推薦
-
沒有記錄!
熱點排行
- 1、鈞瓷發展經歷的幾個重要階段
- 2、***鳳凰臺 一座新城的崛起
- 3、比賽競技顯風采,象棋文化得發揚
- 4、鈞窯瓷器的價值
- 5、王莽趕劉秀在魯山留下趣名趣事
- 6、金水河:繁華穿城而過
- 7、商丘古城里的“鬧龍街”
- 8、相思樹
“大哉嵩山·女皇封禪篇”系列之三
2013/6/21 10:02:47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武則天封禪嵩山,所留的最要緊的文獻,無疑是她親自撰寫、立在嵩山之巔登封壇東南的《大周升中述志碑》。《舊唐書》云:“登封壇南有槲樹,大赦日于其杪置金雞樹。則天自制《升中述志碑》,樹于壇之丙地。”
什么是槲樹?
槲樹是一古老的樹種,初夏開花,雌雄同株,落葉喬木,木質似松,但不似松的疙疙瘩瘩與枝枝丫丫,樹干力爭向天,樹葉橢圓婆娑,將溫柔與堅毅、婀娜與雄強融于一身。這是武則天崇奉槲樹的原因?
什么是金雞樹呢?
也許本沒有什么金雞樹。“其杪置金雞樹”——在槲樹樹梢上,怎么置金雞樹,樹上種樹呀?對此,《新唐書》曰:“登封壇南有大槲,赦日置雞其杪,賜號‘金雞樹’”。自制《升中述志》,刻石示后。”
因為“養”了雞,槲樹就叫金雞樹,這種解釋是合情合理的。之所以樹上放雞——當然該是雄雞了,無非是雞鳴通天的傳說起了作用,則天想借雞“生蛋”,“讓雞報告天帝她的登封告成與大赦天下。在這兒,雞是溝通工具。”鄭州大學升達學院教授郭殿忱先生說。
《新唐書》作者歐陽修曾兩登嵩山之巔,說不定那時槲樹還在,他的說法是可信的。
北宋名士、曾以編修官參與修纂真宗朝國史的謝絳在1032年《游嵩山寄梅殿丞(梅堯臣)書》中說,他與尹洙、歐陽修等同登嵩山,“午昃,方抵峻極上院,師魯(尹洙)體最溢,最先到;永叔(歐陽修)最少,最疲”。于是,在峻極上院“浣漱食飲”,補充體力后,“從容間躋封禪壇”,于此下瞰群峰,“謂非插翼不可到者”,望山下“邑居、樓觀、人物”等,“視若蟻壤”,感慨道:“世所謂仙人者,仆未知其有無,果有,則人世不得不為其輕蔑矣。”“武后封視(禪)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有‘皆’、‘著’、‘著’等填此空字,記者猜測此字有些不恭,被拿掉過)姓名于碑陰,不虞后代之譏其不典也。碑之空無字處,睹圣俞(梅堯臣)記樂理國而下四人同游,(‘刺’的意思,有些開涮梅堯臣)刻尤精。”謝絳冷嘲熱諷完武則天朝的名賢大儒后,還不忘譏笑他的朋友梅堯臣在封禪碑上刻“到此一游”,亦非君子:“仆意古帝王祀天神,紀功德于此,當時尊美甚盛,后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也。”
歷史就是歷史,謝絳對待歷史的態度,無疑值得梅堯臣等認真學習。
但悲劇還是很快發生了,這恐怕是梅堯臣都不敢猜想的——因為他的“到此一游”和武則天的“功業之碑”一起被“毀掉”了。
感謝趙明誠、李清照泣血撰寫、整理的《金石錄》為我們殘存了一點兒歷史信息并為毀碑立此“存照”:周武后《升中述志碑》,武后撰,睿宗書。碑極壯偉,立于嵩山之巔。其陰鐘紹京書,字面皆工妙。(徽宗)政和中,河南尹上言,請碎其碑,詔從之。
《升中述志碑》遭毀,碑文亦不見于任何史料,這讓今天的我們“造假”都無從下手。
謝絳“輕薄”的“當時名賢”到底是誰,我們倒還能猜個大概:狄仁杰、張柬之、姚崇、宋 、鐘紹京、魏元忠、李嶠、薛曜、懷素、崔融、桓彥范、張說、沈期、武承嗣、武三思、薛懷義、來俊臣、李旦(睿宗)、太平公主……
這些光耀千秋或遺臭萬年的名字,也許沒全都刻在《大周升中述志碑》,就是少去仨倆,還有我的掛一漏萬墊底。
《大周升中述志碑》“星光閃耀”可謂是不爭的事實——如果它現在仍“鎮守”嵩山之巔,那無疑是“險峰”的“無限風光”。
窺探封禪的神秘禮儀
《舊唐書》云:“封禪,所以告成功,祀事無重于此。”
在中國的政治架構中,封禪是超越帝王登基、天子駕崩乃至太廟祭祀的國家大禮,無超其右;行過封禪大禮的皇帝,數來數去就那么六七位。但無論哪位封禪者,其禮儀都鮮有史書記載。
公元696年,武則天封禪嵩山時,已是73歲的老人。關乎她的封禪禮儀,無論是《舊唐書》、《新唐書》還是《資治通鑒》等,都語焉不詳——也許天機不可泄露,神秘的事業本就不該廣為傳播吧!不然,自秦皇漢武到高宗則天,他們把封禪搞得轟轟烈烈,恐人不知,為什么史籍中總是難以留下一點兒細節的力量呢?當然,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司馬遷在《史記·封禪書》中所說:“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通‘梁甫’)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余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闋然湮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
封禪“門檻”太高,是帝國時代的“非常祀”。“三年不為禮,禮必廢。”況百年不為一次的封禪“非常祀”乎。
司馬遷也曾參與漢武泰山封禪,也許終歸是“邊緣人”,也許他自認漢武封禪禮儀有點兒“荒誕不經”,所以《史記·封禪書》對此次封禪前因后果的記述不厭其詳,但說到禮儀卻語焉不詳。與司馬遷不同,李嶠雖不是史家,卻以十二分的激情參與則天封禪嵩山,自謙“謬忝司牧,躬陪錯事”,是整個封禪活動的靈魂人物,他撰寫的《大周降禪碑》碑文,對封禪禮儀著墨較多。該碑與則天撰寫的《大周升中述志碑》并立在嵩山之巔、登封壇南,《大周升中述志碑》在東南,《大周降禪碑》在西南。
惜乎,該碑后來下落不明,連怎么“人間蒸發”的,現在都無從追問。
幸賴李嶠“凌云之筆”,《全唐文》不棄收留——文字有些古奧,禮儀是個大約,因實在難得,稍加轉述:第一,是齋戒儀式。則天入齋宮沐浴齋戒,以示對天地神 的虔誠:“萬乘停鑣,百司就列……天子乃幸齋寢,披仙幄……惟夫蠲意澄心,所以至誠盡敬。于是乎,山 護野,風伯清塵,玉醴潛滋,金沙涌。神鐘驚曙,峰巖傳九乳之音;寒律移暄,草樹動三陽之色。征祥之報,影響不違。”第二,是太室之南舉行柴燎儀式,祭祀昊天上帝。“壬申(臘月初九),柴燎祀昊天上帝于岳南,顯祖立極文穆皇帝、太祖無上孝明高皇帝侑神做主。天子戴圓冕,披大裘,登三垓,植四邸,藉陳葙秸,器用陶匏。高炎四施,耀流沙而燭滄海;廣樂六變,來象物而降天神。感霏煙瑞露之征,延薰風景星之祉。”第三,是最隆重的祭天儀式。“(柴燎)大禮既畢,嘉應既臻,思欲契精爽于高明,剖靈符于峻極。甲申(十一日),御金蹕,登玉輿,環拱百神,導從群后,遂陵桂萼,攀松磴,跨崢嶸而出煙道,排列缺而 天門。羽節高揮,上干鳥星之次;黽壇下映,俯瞰鵬云之色。瓊文秘檢,絡之以銀繩;寶算休期,探之于金策:交大靈于咫尺,受洪 于億萬。然后徜徉煙霄,怊悵(悲憫)古昔,凝神于九天之上,游目于八 之表……仰斗杓之運行,仍布維新之令。是日大赦,改元為萬歲登封元年……千齡之統,由圣代而連九皇;萬歲之音,自神山而周四海。休氣低而翔輦,神光起而屬天。舞相趨,以降于行殿。”第四,舉行祀地儀式,祭后土于少室山。“丁亥(十四日),禪祭后土于少室下趾東南。顯祖妣立極文穆皇后、太祖妣無上孝明高皇后侑神做主。戈矛山立,玉帛星陳,登澗沼之毛,輯江淮之物。禹會之殊方異俗,俱執豆籩;漢祠之偉獸珍禽,悉加壇墀。撫空桑之琴瑟,斟郁鬯之樽,咸秩眾靈,遍祀群望……陽烏珥而仙鶴飛,紫云騰而黃霧起。靈之來兮如雨,瑞之委兮如山。”第五,也是最后,為朝覲儀式。則天登朝覲臺,接受百官及諸國使者朝賀:“于是事畢功宏,禮周慶洽。方欲輯圭璧,陳 任,鋪六代之禮文,受萬邦之朝賀。宏規大業,其盛矣哉……我后乎出帝先(則天自稱武姓嫡出三代之周),遂康天步,登封降禪,拉宇宙之樞衡;立顯崇功,定皇王之軌式。鴻勛上格于穹昊,厚福旁浸于黎元。煒煒煌煌,亙寰區而宣壯麗;巍巍蕩蕩,橫山丘而殷聲名……天下之大功成矣,域中之能事畢矣。”
至于武則天為什么封禪嵩山,《大周降禪碑》開篇就講得一清二楚:歷數封禪之舉,“未有回輿按驛,覲中土之神靈;刻石泥金,崇外方(嵩山)之 祀:名臣于是乎斷其去就,良史于是乎題其失得”。雖然“民主”熱議,讓人評說,但說到緣何封禪嵩山,卻“驕橫”地舍我其誰:“然則置表測日,陽城當六氣之交;祭林奠山,太室為九封之長:神翰降生于廊廡,王畿仰矚于峰岫。風雷所蓄,俯鎮于三河;辰緯所躔,旁臨于四岳:立崇乾事坤之兆,疏就下(禪地)因高(封山)之位,舍此地也,疇(誰)其尚焉!“
封天禪地的轟然倒掉
“知崇高之可封,悟梁甫之虛躡。”《大周降禪碑》的最后結語,可謂震天撼地——這不只是自我作古,簡直是摧枯拉朽。
封天禪地的“思想基礎”源自先哲架構的“天人合一”,“法理案例”則是傳說的堯舜乃至黃帝用事泰山梁甫,這是秦始皇以降歷代帝王封泰山禪梁甫的根本。而封天禪地不能異地進行,這也是個根本——懷疑梁甫,無疑是藐視泰山。
《大周降禪碑》雖由李嶠撰寫,但毫無疑問的是則天“定稿”。
作為政治家,他們當然不能信口雌黃,總要鋪墊泰山倒掉的理由:“秦嬴(秦始皇)極暴,企踵于無為之朝;漢徹(漢武帝)窮奢,厚顏于盛德之事(封禪):人不見義,其來自久……”在這兒,《大周降禪碑》肯定秦皇漢武泰山封禪的“不義”,其實也就等于否定了他們泰山封禪的正當性。
這還不算完,接著《大周降禪碑》又“踐踏”傳說中封禪泰山的先驅,張揚嵩山封禪的神圣:“躪(踐踏)前賢之規模,開含靈之耳目。方使炎農抱愧,愕睨于梁甫之阿;堯舜欽風,延佇于崇高之路:天下之大功成矣,域中之能事畢矣……神功與二儀并運,顯號將七曜俱懸。豈可使時邁無詩,于皇不作?臣嶠謬忝司牧,躬陪錯事:末光幸煦,長傾捧日之心;仟石徒攀,終愧凌云之筆。”
武則天封禪嵩山無疑是中國封禪史上的“成湯革命”:盡管“承天受命”的封禪大典是該在“天地之中”的嵩山與天交通,《大周降禪碑》所言所說自不是強詞奪理。但任何神秘主義都是怕擺事實講道理的——一旦進入理性的思辨,封禪就不免走上世俗乃至消亡的不歸路。
也因此,接下來玄宗復辟李唐,封禪泰山幾乎成為一種天下重歸李家的宣告儀式——天子的側重點不再是與天交通,世俗的象征意義遠多于向天的神秘祈求,是有史以來最為“透明”的封禪活動。當中書令張說等共賀玄宗封天告成時,玄宗說:“朕以薄德,恭膺大寶……皆是卿輔弼之力。”而禪地時,玄宗露立祈請,仰天自誓,曰:“某身有過,請即降罰,萬人無福,亦請某為當罪。”——這純粹是借天地之神說“人話”,意不在天而在籠絡臣下與黎民了。
而前代帝王都說些什么“鬼話”呢?按賀知章的猜測,“或禱年算,或思神仙”,這事兒,是“秘請”,只有封禪者自己心知肚明——登封泰山前,玄宗問賀知章:“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秘之?”賀知章曰:“玉牒本是通于神明之意,前代帝王祈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為蒼生祈福,更無秘請;宜將玉牒出示百僚。”玉牒之辭是:“有唐天子臣某,敢詔告于昊天上帝:天啟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佑,錫臣忠武……”
玄宗一個“更無秘請”,讓神秘的封禪光明起來。而封禪的根本是與天交通,玄宗走到這個份兒上,也就等于宣告封禪走上窮途末路。
接下來,宋真宗把天書封禪搞成了一場政治運動,意在消解“澶淵之盟”的不爽,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位封禪者。
真宗在位25年,干了兩件事:一是簽下“澶淵之盟”,一是上了“天書封禪”項目。
“澶淵之盟”雖系城下之盟,但也不是特別過不去的丟臉事兒。偏偏王欽若為排擠寇準,硬把澶淵之盟“暗示”為“不堪”的事,讓真宗天天和自己過不去,越想越郁悶,總覺得要再上個漂亮的項目,沖淡“澶淵之盟”的羞恥。
“說實在的,真宗是歷史上最不應該封禪的帝王。”登封市史志辦主任呂宏軍先生說。
真宗這么一“狗尾續貂”,就再沒有什么帝王“鼠尾續狗”了。(原標題:“大哉嵩山·女皇封禪篇”系列之三)
什么是槲樹?
槲樹是一古老的樹種,初夏開花,雌雄同株,落葉喬木,木質似松,但不似松的疙疙瘩瘩與枝枝丫丫,樹干力爭向天,樹葉橢圓婆娑,將溫柔與堅毅、婀娜與雄強融于一身。這是武則天崇奉槲樹的原因?
什么是金雞樹呢?
也許本沒有什么金雞樹。“其杪置金雞樹”——在槲樹樹梢上,怎么置金雞樹,樹上種樹呀?對此,《新唐書》曰:“登封壇南有大槲,赦日置雞其杪,賜號‘金雞樹’”。自制《升中述志》,刻石示后。”
因為“養”了雞,槲樹就叫金雞樹,這種解釋是合情合理的。之所以樹上放雞——當然該是雄雞了,無非是雞鳴通天的傳說起了作用,則天想借雞“生蛋”,“讓雞報告天帝她的登封告成與大赦天下。在這兒,雞是溝通工具。”鄭州大學升達學院教授郭殿忱先生說。
《新唐書》作者歐陽修曾兩登嵩山之巔,說不定那時槲樹還在,他的說法是可信的。
北宋名士、曾以編修官參與修纂真宗朝國史的謝絳在1032年《游嵩山寄梅殿丞(梅堯臣)書》中說,他與尹洙、歐陽修等同登嵩山,“午昃,方抵峻極上院,師魯(尹洙)體最溢,最先到;永叔(歐陽修)最少,最疲”。于是,在峻極上院“浣漱食飲”,補充體力后,“從容間躋封禪壇”,于此下瞰群峰,“謂非插翼不可到者”,望山下“邑居、樓觀、人物”等,“視若蟻壤”,感慨道:“世所謂仙人者,仆未知其有無,果有,則人世不得不為其輕蔑矣。”“武后封視(禪)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有‘皆’、‘著’、‘著’等填此空字,記者猜測此字有些不恭,被拿掉過)姓名于碑陰,不虞后代之譏其不典也。碑之空無字處,睹圣俞(梅堯臣)記樂理國而下四人同游,(‘刺’的意思,有些開涮梅堯臣)刻尤精。”謝絳冷嘲熱諷完武則天朝的名賢大儒后,還不忘譏笑他的朋友梅堯臣在封禪碑上刻“到此一游”,亦非君子:“仆意古帝王祀天神,紀功德于此,當時尊美甚盛,后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也。”
歷史就是歷史,謝絳對待歷史的態度,無疑值得梅堯臣等認真學習。
但悲劇還是很快發生了,這恐怕是梅堯臣都不敢猜想的——因為他的“到此一游”和武則天的“功業之碑”一起被“毀掉”了。
感謝趙明誠、李清照泣血撰寫、整理的《金石錄》為我們殘存了一點兒歷史信息并為毀碑立此“存照”:周武后《升中述志碑》,武后撰,睿宗書。碑極壯偉,立于嵩山之巔。其陰鐘紹京書,字面皆工妙。(徽宗)政和中,河南尹上言,請碎其碑,詔從之。
《升中述志碑》遭毀,碑文亦不見于任何史料,這讓今天的我們“造假”都無從下手。
謝絳“輕薄”的“當時名賢”到底是誰,我們倒還能猜個大概:狄仁杰、張柬之、姚崇、宋 、鐘紹京、魏元忠、李嶠、薛曜、懷素、崔融、桓彥范、張說、沈期、武承嗣、武三思、薛懷義、來俊臣、李旦(睿宗)、太平公主……
這些光耀千秋或遺臭萬年的名字,也許沒全都刻在《大周升中述志碑》,就是少去仨倆,還有我的掛一漏萬墊底。
《大周升中述志碑》“星光閃耀”可謂是不爭的事實——如果它現在仍“鎮守”嵩山之巔,那無疑是“險峰”的“無限風光”。
窺探封禪的神秘禮儀
《舊唐書》云:“封禪,所以告成功,祀事無重于此。”
在中國的政治架構中,封禪是超越帝王登基、天子駕崩乃至太廟祭祀的國家大禮,無超其右;行過封禪大禮的皇帝,數來數去就那么六七位。但無論哪位封禪者,其禮儀都鮮有史書記載。
公元696年,武則天封禪嵩山時,已是73歲的老人。關乎她的封禪禮儀,無論是《舊唐書》、《新唐書》還是《資治通鑒》等,都語焉不詳——也許天機不可泄露,神秘的事業本就不該廣為傳播吧!不然,自秦皇漢武到高宗則天,他們把封禪搞得轟轟烈烈,恐人不知,為什么史籍中總是難以留下一點兒細節的力量呢?當然,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司馬遷在《史記·封禪書》中所說:“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通‘梁甫’)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余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闋然湮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
封禪“門檻”太高,是帝國時代的“非常祀”。“三年不為禮,禮必廢。”況百年不為一次的封禪“非常祀”乎。
司馬遷也曾參與漢武泰山封禪,也許終歸是“邊緣人”,也許他自認漢武封禪禮儀有點兒“荒誕不經”,所以《史記·封禪書》對此次封禪前因后果的記述不厭其詳,但說到禮儀卻語焉不詳。與司馬遷不同,李嶠雖不是史家,卻以十二分的激情參與則天封禪嵩山,自謙“謬忝司牧,躬陪錯事”,是整個封禪活動的靈魂人物,他撰寫的《大周降禪碑》碑文,對封禪禮儀著墨較多。該碑與則天撰寫的《大周升中述志碑》并立在嵩山之巔、登封壇南,《大周升中述志碑》在東南,《大周降禪碑》在西南。
惜乎,該碑后來下落不明,連怎么“人間蒸發”的,現在都無從追問。
幸賴李嶠“凌云之筆”,《全唐文》不棄收留——文字有些古奧,禮儀是個大約,因實在難得,稍加轉述:第一,是齋戒儀式。則天入齋宮沐浴齋戒,以示對天地神 的虔誠:“萬乘停鑣,百司就列……天子乃幸齋寢,披仙幄……惟夫蠲意澄心,所以至誠盡敬。于是乎,山 護野,風伯清塵,玉醴潛滋,金沙涌。神鐘驚曙,峰巖傳九乳之音;寒律移暄,草樹動三陽之色。征祥之報,影響不違。”第二,是太室之南舉行柴燎儀式,祭祀昊天上帝。“壬申(臘月初九),柴燎祀昊天上帝于岳南,顯祖立極文穆皇帝、太祖無上孝明高皇帝侑神做主。天子戴圓冕,披大裘,登三垓,植四邸,藉陳葙秸,器用陶匏。高炎四施,耀流沙而燭滄海;廣樂六變,來象物而降天神。感霏煙瑞露之征,延薰風景星之祉。”第三,是最隆重的祭天儀式。“(柴燎)大禮既畢,嘉應既臻,思欲契精爽于高明,剖靈符于峻極。甲申(十一日),御金蹕,登玉輿,環拱百神,導從群后,遂陵桂萼,攀松磴,跨崢嶸而出煙道,排列缺而 天門。羽節高揮,上干鳥星之次;黽壇下映,俯瞰鵬云之色。瓊文秘檢,絡之以銀繩;寶算休期,探之于金策:交大靈于咫尺,受洪 于億萬。然后徜徉煙霄,怊悵(悲憫)古昔,凝神于九天之上,游目于八 之表……仰斗杓之運行,仍布維新之令。是日大赦,改元為萬歲登封元年……千齡之統,由圣代而連九皇;萬歲之音,自神山而周四海。休氣低而翔輦,神光起而屬天。舞相趨,以降于行殿。”第四,舉行祀地儀式,祭后土于少室山。“丁亥(十四日),禪祭后土于少室下趾東南。顯祖妣立極文穆皇后、太祖妣無上孝明高皇后侑神做主。戈矛山立,玉帛星陳,登澗沼之毛,輯江淮之物。禹會之殊方異俗,俱執豆籩;漢祠之偉獸珍禽,悉加壇墀。撫空桑之琴瑟,斟郁鬯之樽,咸秩眾靈,遍祀群望……陽烏珥而仙鶴飛,紫云騰而黃霧起。靈之來兮如雨,瑞之委兮如山。”第五,也是最后,為朝覲儀式。則天登朝覲臺,接受百官及諸國使者朝賀:“于是事畢功宏,禮周慶洽。方欲輯圭璧,陳 任,鋪六代之禮文,受萬邦之朝賀。宏規大業,其盛矣哉……我后乎出帝先(則天自稱武姓嫡出三代之周),遂康天步,登封降禪,拉宇宙之樞衡;立顯崇功,定皇王之軌式。鴻勛上格于穹昊,厚福旁浸于黎元。煒煒煌煌,亙寰區而宣壯麗;巍巍蕩蕩,橫山丘而殷聲名……天下之大功成矣,域中之能事畢矣。”
至于武則天為什么封禪嵩山,《大周降禪碑》開篇就講得一清二楚:歷數封禪之舉,“未有回輿按驛,覲中土之神靈;刻石泥金,崇外方(嵩山)之 祀:名臣于是乎斷其去就,良史于是乎題其失得”。雖然“民主”熱議,讓人評說,但說到緣何封禪嵩山,卻“驕橫”地舍我其誰:“然則置表測日,陽城當六氣之交;祭林奠山,太室為九封之長:神翰降生于廊廡,王畿仰矚于峰岫。風雷所蓄,俯鎮于三河;辰緯所躔,旁臨于四岳:立崇乾事坤之兆,疏就下(禪地)因高(封山)之位,舍此地也,疇(誰)其尚焉!“
封天禪地的轟然倒掉
“知崇高之可封,悟梁甫之虛躡。”《大周降禪碑》的最后結語,可謂震天撼地——這不只是自我作古,簡直是摧枯拉朽。
封天禪地的“思想基礎”源自先哲架構的“天人合一”,“法理案例”則是傳說的堯舜乃至黃帝用事泰山梁甫,這是秦始皇以降歷代帝王封泰山禪梁甫的根本。而封天禪地不能異地進行,這也是個根本——懷疑梁甫,無疑是藐視泰山。
《大周降禪碑》雖由李嶠撰寫,但毫無疑問的是則天“定稿”。
作為政治家,他們當然不能信口雌黃,總要鋪墊泰山倒掉的理由:“秦嬴(秦始皇)極暴,企踵于無為之朝;漢徹(漢武帝)窮奢,厚顏于盛德之事(封禪):人不見義,其來自久……”在這兒,《大周降禪碑》肯定秦皇漢武泰山封禪的“不義”,其實也就等于否定了他們泰山封禪的正當性。
這還不算完,接著《大周降禪碑》又“踐踏”傳說中封禪泰山的先驅,張揚嵩山封禪的神圣:“躪(踐踏)前賢之規模,開含靈之耳目。方使炎農抱愧,愕睨于梁甫之阿;堯舜欽風,延佇于崇高之路:天下之大功成矣,域中之能事畢矣……神功與二儀并運,顯號將七曜俱懸。豈可使時邁無詩,于皇不作?臣嶠謬忝司牧,躬陪錯事:末光幸煦,長傾捧日之心;仟石徒攀,終愧凌云之筆。”
武則天封禪嵩山無疑是中國封禪史上的“成湯革命”:盡管“承天受命”的封禪大典是該在“天地之中”的嵩山與天交通,《大周降禪碑》所言所說自不是強詞奪理。但任何神秘主義都是怕擺事實講道理的——一旦進入理性的思辨,封禪就不免走上世俗乃至消亡的不歸路。
也因此,接下來玄宗復辟李唐,封禪泰山幾乎成為一種天下重歸李家的宣告儀式——天子的側重點不再是與天交通,世俗的象征意義遠多于向天的神秘祈求,是有史以來最為“透明”的封禪活動。當中書令張說等共賀玄宗封天告成時,玄宗說:“朕以薄德,恭膺大寶……皆是卿輔弼之力。”而禪地時,玄宗露立祈請,仰天自誓,曰:“某身有過,請即降罰,萬人無福,亦請某為當罪。”——這純粹是借天地之神說“人話”,意不在天而在籠絡臣下與黎民了。
而前代帝王都說些什么“鬼話”呢?按賀知章的猜測,“或禱年算,或思神仙”,這事兒,是“秘請”,只有封禪者自己心知肚明——登封泰山前,玄宗問賀知章:“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秘之?”賀知章曰:“玉牒本是通于神明之意,前代帝王祈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為蒼生祈福,更無秘請;宜將玉牒出示百僚。”玉牒之辭是:“有唐天子臣某,敢詔告于昊天上帝:天啟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佑,錫臣忠武……”
玄宗一個“更無秘請”,讓神秘的封禪光明起來。而封禪的根本是與天交通,玄宗走到這個份兒上,也就等于宣告封禪走上窮途末路。
接下來,宋真宗把天書封禪搞成了一場政治運動,意在消解“澶淵之盟”的不爽,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位封禪者。
真宗在位25年,干了兩件事:一是簽下“澶淵之盟”,一是上了“天書封禪”項目。
“澶淵之盟”雖系城下之盟,但也不是特別過不去的丟臉事兒。偏偏王欽若為排擠寇準,硬把澶淵之盟“暗示”為“不堪”的事,讓真宗天天和自己過不去,越想越郁悶,總覺得要再上個漂亮的項目,沖淡“澶淵之盟”的羞恥。
“說實在的,真宗是歷史上最不應該封禪的帝王。”登封市史志辦主任呂宏軍先生說。
真宗這么一“狗尾續貂”,就再沒有什么帝王“鼠尾續狗”了。(原標題:“大哉嵩山·女皇封禪篇”系列之三)
責任編輯:C006文章來源:大河網 2006-11-13 作者:于茂世
下一條:“大哉嵩山·女皇封禪篇”系列之四上一條:“大哉嵩山·女皇封禪篇”系列之二
相關信息
沒有記錄!
著名人物
沒有記錄!
精彩展示
沒有記錄!
評論區
友情鏈接
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