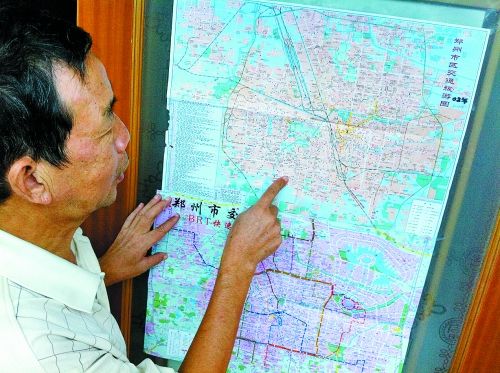精彩推薦
熱點關注
專題推薦
-
沒有記錄!
熱點排行
魏德忠:用鏡頭記錄一個時代
2013/7/26 11:50:47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人物檔案
魏德忠,1934年生于河南新蔡,新中國成立之初開始攝影工作,1957年任河南日報攝影記者。1980年當選為河南省攝影家協會副主席,1996年當選為協會主席。現任河南省攝影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攝影家協會理事、鄭州大學客座教授、河南省紅旗渠精神研究會秘書長等職務。曾多次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國家領導人拍照,用鏡頭記錄了近半個世紀以來河南人民在社會主義征途上的風風雨雨,積累了大量珍貴的歷史照片。他堅持10年拍攝紅旗渠工程,出版大型畫冊《紅旗渠》。其作品先后在國內外展出和獲獎,《小水庫顯神威》獲第十四屆荷蘭世界新聞攝影大賽榮譽獎,出版有《鏡頭感知錄》等文集。
歷史滾滾向前的車輪中,中華兒女在自強不息、勤勞勇敢的民族精神指引下,創造出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跡。有著60多年“攝”齡、今年79歲的攝影家魏德忠,正是一位執著于用鏡頭記錄下那些時代發展的脈搏,頌揚著、傳播著偉大民族精神的“勇士”——8次拍攝毛澤東,6次拍攝周恩來,獨家跟蹤記錄紅旗渠10年建設歷程,為“紅旗渠”精神的傳播和發展做出不可替代的貢獻……作為攝影界的老前輩,魏德忠用一張張照片定格下那些火紅年代的經典瞬間,用自己的鏡頭記錄著、頌揚著奮發向上的時代。“除了攝影,一輩子沒干過別的大事”的魏德忠,也因攝影綻放了生命的光輝。
放下筆桿拿起“槍”
1949年,15歲的魏德忠響應國家號召,從高中校園走進部隊,憑借著“小知識分子”的身份,被安排進宣傳科開展宣傳工作。
“當時有個戰斗英雄馬春雨,在部隊做教導員,我就寫了一篇關于他的小稿子,沒想到很快就在《前進報》上全文發表了。”回憶起半個多世紀前的舊事,魏德忠依然歷歷在目,“這篇報道讓領導一下子注意到了我,而這個時候正好宣傳科需要一名攝影干事,就把我選上了。”
就這樣,在大部分人還沒見過照相機的時候,魏德忠已經端起了相機。“我的第一部相機是戰利品,德國蔡司折疊式相機。”魏德忠告訴記者,由于當時條件限制,用的相機都是戰斗中收繳的,膠卷更是異常珍貴,連快門都不能輕易按下,只能在無數次的想象中調焦、構圖,練習攝影技術。
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魏德忠摸索出了很多“絕招”,一卷照12張相片的膠卷,經過他的處理,能照到16張;甚至自己動手加工拼接膠卷,使之得到充分的利用……從1950年到1953年的短短幾年里,魏德忠的作品頻頻發表在《邊防戰士》《東北戰士》等刊物上,一張張反映軍旅生活的生動作品,帶給戰士們極大的鼓舞和安慰,他也因此榮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
為了在更廣闊的天地里實現自己的抱負,1957年魏德忠選擇轉業,到《河南日報》任攝影記者。果然,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里,人們熱切希望建設社會主義的信念、上下一心的團結精神,深深鼓舞、感染了魏德忠,他作為一名攝影記者的創作生涯,也由此展開。
與偉人的一段緣
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等老一輩革命領導人都在他鏡頭中散發光彩——得到這樣的信任和肯定的攝影家,在全國也沒有幾名,魏德忠正是其中之一。這段際遇,成為魏德忠豐富精神財富中的重要部分。
“1958年11月1日,第一次鄭州會議在鄭州召開,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第一次拍毛主席。”回憶起當時的情形,魏德忠依然十分激動,“主席走進會場,大家十分激動,主席也摘下帽子向群眾揮手致意……”
更令魏德忠感動的是,毛主席視察燕莊時,為了攝影記者的拍攝需要,專門從馬路走進剛剛下過雨的麥田。“公路高,麥田低,不好拍照。但當時田里剛下過雨,泥濘不堪,陪同人員擔心主席下到麥田的路不好走,但主席非常善解人意,主動走進麥地。”魏德忠激動地告訴記者,拍完照,毛主席還說了一段令他一輩子也忘不了、一輩子受益的話:“主席非常幽默地說,‘你們是一只眼睛看人,目標集中——不過以后你們要把鏡頭對準群眾,不要對準我,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
主席的話,指導魏德忠數十年的記者生涯——把鏡頭集中在人民群眾身上;而周恩來總理則是春風化雨般,使魏德忠感受到記者職業的神圣和職責。“周總理視察的時候,對群眾永遠是那么親切、隨和。就連在職工食堂吃完飯,還要向他們致謝,這些事情,連一個鄉鎮干部都不曾做到。”魏德忠還記得,跟隨周總理去關虎屯視察棉花地時,總理小心地和群眾一起蹲下來,還招呼記者:“記者同志,腳下留情啊!”
如今,屹立在繁華金水路曼哈頓商業區的“毛主席視察燕莊紀念亭”內,一座栩栩如生的毛主席銅像記錄著那段歷史,而銅像的形象就依據魏德忠在毛主席視察燕莊時拍攝的歷史照片為主要參考。
“紅旗渠”代言人
稍縱即逝的歷史瞬間,一個分神就會溜走,但魏德忠緊緊地抓住了它們——提到魏德忠,除了記錄伴隨數億農民度過20多個春秋的“人民公社”,不能不說到他與紅旗渠的故事、他十年如一日的拍攝對“紅旗渠精神”至關重要的宣傳和影響。
“那是1960年2月,一個乍暖還寒的春天,我跟河南日報采訪團一起,在當時林縣縣委書記楊貴陪同下,采訪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的山區建設。”談起拍攝“紅旗渠”的經歷,魏德忠邊回憶、邊敘說。當采訪團走到林縣和山西平順縣交界的大山腳下時,看到一片工地上紅旗招展,螞蟻搬家似的運料獨輪車如織如梭,有許多人吊在半空中,凌空開鑿身輕似燕,掄錘打釬,那勁頭令人興奮,那場面令人震撼。
得知這個“引漳入林”工程,要在山上修一條渠,把山西的漳河水引到林縣來、解決缺水問題時,魏德忠來了精神,“這不就是喚醒沉睡的高山、讓那河流改變了模樣嗎?這不就是愚公移山、大禹治水嗎?” 魏德忠告訴記者,“他們那種不怕苦,不怕累,知難而上的精神,深深打動了我,我決定改變原來的采訪計劃,留在工地繼續采訪。”
1960年正是國家三年困難時期,當時人均每天只有半斤糧食,吃不飽肚子,修渠人就在山上采野菜充饑,“早晨湯,中午糠,晚上稀飯照月亮”就是當時的生活寫照,但林縣人民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憑著一錘一釬一雙手,逢山鑿洞,遇溝架橋,經過10年的拼搏,克服了重重困難,斬斷了1250座山頭,鑿通了211個隧道,架設了152座渡槽,修成了高4.3米、寬8米、設計引水25個流量、140華里的總干渠,加上干渠支渠3000華里的紅旗渠。
紅旗渠修了10年,魏德忠就拍了10年——他坐火車到安陽、又坐汽車到林縣,接著自己騎著自行車跟隨修渠大軍上了太行山,與修渠的同志同吃、同住、同勞動,從每一寸渠岸到每一個具有艱難標志的施工點,從每一個令人心動的細節到每一處紀念碑式的建筑,都準確生動地記錄下來,把那些動人的瞬間定格,成為永恒的、鮮活的歷史見證,并最終整理成冊《紅旗渠》,成為紅旗渠精神研究極其珍貴的資料,更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財富。
2006年,魏德忠拍攝的“紅旗渠”作為時代代表精神之一,入展中國影協主辦的“攝影中國1949-2006大型攝影展覽”; 2008年,紅旗渠精神研討會在安陽舉行,魏德忠的珍貴照片成為傳播“紅旗渠精神”最直觀、最震撼的藝術形式。近半個世紀后的今天,人們講述與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脈相承的紅旗渠精神,世界稱頌著中國的“水長城”、“人工天河”,而正是魏德忠的堅守與付出,使“紅旗渠”精神走得更遠、傳揚得更廣……
“修建紅旗渠是艱苦的,拍攝紅旗渠也是一樣。”魏德忠拍攝紅旗渠的代表作《凌空除險》,角度、光線、構圖甚至那一瞬間的表情,都在那一刻聚合,達到最為完美的視覺效果——誰能想到,這是魏德忠把自己綁起來,掛在懸崖邊以求得最佳角度拍攝的。而為了拍好林縣人民戰天斗地的精神,魏德忠躺渣石、攀樹枝、爬山頭、扒危巖、鉆隧洞、蹚河水,被人稱為“是個拍照片不要命的人”。
有人不能理解魏德忠10年如一日的堅守,但他說:“攝影記者最大的職責,是把時代的足跡記錄下來,留為永恒。”而他的堅持也是在修渠人的精神感染和激勵下進行的,“那種偉大民族精神的激勵、那種忘我勞動的場景,總是給我一股股暖流,給人一種力量。我希望這些作品,也能在幾十年甚至更遠的將來,給后人不斷的精神激勵!”
青年一代要勇于擔當
“攝影的魅力在于它的真實,在于它瞬間定格的永恒。每張照片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有它瞬間的思考。”“攝齡”比很多人的年紀都要長很多的魏德忠說,一個攝影師終會蒼老、會死去,但他拍的有價值的照片永遠不會消失,甚至可能會深深地影響幾代人,所以攝影師無論用什么型號的相機,都要學會尋找照片中所含的普遍性的意義。
“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記者是一個光榮的職業,要樹立文獻記錄的觀念,做一個忠實的時代記錄者。”魏德忠告誡年輕一代新聞工作者,“年輕人要到火熱的生活中去,到第一線去抓真實的生活,把瞬間變為永恒,作為歷史的見證永久留給后人,這是我們的責任和義務。”他還認為,攝影作品應該讓人欣賞,不是自我欣賞,因而要反映真善美、能帶給群眾美的享受和激勵,使人們得到一些有益的東西。
魏德忠提出,雖然攝影器材越來越先進,看似對技術沒有要求了,但攝影精神層面的思考更為重要,講究“抓細節”,追求最生動的典型、探尋照片背后蘊含的思想藝術性也未改變。“對有時代價值、歷史意義的題材,要反復去拍。”魏德忠說,如不交“皇糧”這些中國歷史上的大事件,需要有代表性作品;社會發展催生的民工潮,可謂是一個歷史階段的時代的腳印,也需要拍出能以反映出群眾精神狀態、民族精神的代表性作品,“這也是其他藝術形式不能取代的。”
“攝影記者這個職業,是艱苦的工作、奉獻的工作,也是光榮的工作。通過真實可信的形象,讓人毫不懷疑地相信新聞事件,從中印證歷史的真實面目。”魏德忠再三叮囑:“這是人民和國家交給你的光榮使命,應當不負使命,把生活年代的重大事件、時代的足跡忠實記錄下來。”
“綠城”稱號的功臣
很多人都知道,鄭州有著“綠城”的別稱,這一稱號從何而來?答案竟然是因為上世紀70年代初,魏德忠在《解放軍畫報》上發表的《綠滿鄭州》的大幅照片,綠樹成蔭、郁郁蔥蔥的清新畫面,使鄭州自此有了“綠城”之稱。
“1954年,河南省會從開封遷至鄭州,這時候開始,鄭州大面積種植法桐。到70年代初,這些樹已經長得非常茂盛了。”魏德忠回憶,他參加航拍鄭州的活動后,把拍攝的作品寄到了《解放軍畫報》并得到發表,一下子改變了全國人民對鄭州的印象、提升了鄭州的形象,更得到了“綠城”的美譽。
時任法國外交部長舒曼看到這些照片、得知法桐在鄭州“安營扎寨”后也大為贊賞;1971年,受到吸引的舒曼來鄭州,更是稱贊鄭州是“綠色的海洋”。
魏德忠對鄭州的“貢獻”遠不止此——鄭州作為“二七歷史名城”,二七廣場、二七紀念塔從最初的建設、后期的擴建、今天的新貌,魏德忠一一記錄在冊,并適時發表以正視聽;最早的河南飯店、中州賓館是什么模樣?魏德忠的作品會告訴您最真實的鄭州……
“其實我想告訴現在的年輕人,鄭州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不管是經濟建設還是綠化、環境改造,都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魏德忠語重心長地表示,過去鄭州鹽堿沙荒比較厲害,風一吹屋子里就是一層沙,春天一片白茫茫,而現在已經得到了很好的治理,“大家不要再動不動就抱怨,要懂得珍惜現在的幸福生活。”
笑口常開不老翁
1994年,魏德忠從《河南日報》退休,隨后在省攝影家協會擔任副主席、主席、名譽主席等工作。養花、種菜,整理資料、參加攝影活動……日子依然過得忙忙碌碌,笑口常開。
“我是一個樂觀開朗的人,在我眼里社會和他人都是美好的。”魏德忠笑言,老伴曾無奈地評價他“看誰都是好人”。“這或許是因為我趕上了好時代,我受那個年代的鼓舞、受人民群眾的影響,變得樂觀、積極。”魏德忠告訴記者,“文革”后期時,他也被人貼了大字報,甚至兩次入獄。
“有一次我犯的是‘走私罪’。還上了《河南日報》頭版,說‘魏德忠犯走私罪依法逮捕’……”說到當年的經歷,魏德忠哈哈大笑。原來,當年他出于好心,把別人推薦的一些進口相機介紹給同行,自己一分錢沒落著,就成了“走私犯”。“我問心無愧呀,當時在監獄里還想,最多判我一兩年吧,出來以后總有水落石出的時候。”魏德忠說,自己有著堅定的信念,相信黨、相信群眾,心態非常好,“我想,不能把身體搞垮,在監獄里該吃吃、該喝喝,出獄后大家還奇怪,魏德忠怎么沒有瘦?那是因為我沒把這些事放在心上!”本該“慘痛”的回憶,魏德忠卻講得活靈活現,十分風趣,似乎在談一個別人的故事。
魏德忠的老伴也告訴記者,因為他的作品多,且多與鄭州舊貌新顏息息相關,不少飯店“自發”把他的作品掛到了飯店的大廳、包間里,但魏德忠卻“默許”了,“那也是一種宣傳吧!”他說。
年近耄耋,魏德忠依然精神十足,除了手頭正在籌備的毛主席誕辰120周年攝影展,他還制作了一套“紅旗渠”照片,準備進行高校巡展。在各種工作機會中,他還樂意培養年輕的攝影師,“能支持的支持,能幫助的幫助。讓年輕人上就是我的幸福。”魏德忠說,“我的心寬著呢!以前當記者的時候,跟毛主席坐過專列,去林縣也蹲過運料驢車;我是‘有福能享,有罪能受’!”
風風火火拍了60多年,魏德忠淘汰掉自己不滿意的作品,留下了十幾麻袋見證了時代的膠卷和成堆的資料。“我把過去生活年代的足跡留給后世,供后人研究,無愧于自己所處的時代、貢獻于時代,這是我的使命和追求!”
多么崇高的使命和追求!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魏德忠依然孜孜不倦地追求著,不僅用鏡頭頌揚著河南數十年的時代巨變,更展現出中原兒女自強不息、勤勞勇敢的偉大精神;而他的名字,也必將隨著他鏡頭下無聲的絢麗世界,隨著多彩的時代,愈傳愈響亮!本報記者 張子明 左麗慧 文 楊 光 圖【原標題:用鏡頭記錄一個時代——中原之子系列人物之魏德忠】
責任編輯:C009文章來源:鄭州日報 2013-7-26
下一條:“西瓜哥”雕刻西瓜走紅上一條:鍋碗瓢盆“交響曲” 專門唱給農民工
相關信息
沒有記錄!
精彩展示
沒有記錄!
評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