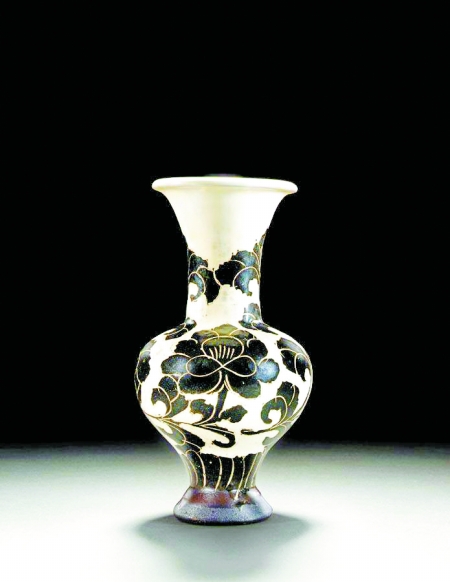-
沒有記錄!
千古滄桑話大晟
2016/1/15 10:44:08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故宮博物院藏有一組北宋時期的“大晟”編鐘(見圖),共8枚。它們大小相近,形制相同。形制上,這些編鐘與先秦古鐘十分接近,是北宋徽宗崇寧年間,仿照當時出土的春秋宋公戌鐘鑄造的。
宋公戌鐘于北宋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出土于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崇福院內,共六枚。據古書記載,宋人是商人的后代,而商人出自傳說中的帝王顓頊。顓頊所用的古樂號“六莖”,古鐘恰好有六枚,時人便以為是六莖所用樂器。再加上應天府是宋太祖趙匡胤的“龍潛”之地——黃袍加身之前,趙匡胤的官職是后周歸德軍節度使,治宋州,故而登基后取“宋”為國號。宋州后來也就改名為“應天”,以示“應天之命”。在受命之邦挖出了帶有皇朝國號的古器,舉朝以為是祥瑞。宋徽宗便命大司樂劉昺按這幾口古鐘的形制,仿制一套編鐘,再現上古的雅樂。
古鐘的形制容易效仿,制作技藝卻無法復原。先秦的編鐘,大小相次,一鐘雙音,這種工藝早已失傳。當時的編鐘,大小一致,厚薄不同,每枚鐘只能發出一個樂律的樂音。
傳統上,樂音根據音高的不同分為“十二律”: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其中,黃鐘律是基準。但世異時移,黃鐘律已無法確定。為此,宋帝下詔,博求“知音”之士。后來,官員們終于在西蜀尋訪到一位九十余歲的老者,名叫魏漢津,自稱學過“鼎樂之法”。漢津向徽宗進言,認為黃帝創設黃鐘之律,律管長九寸。夏禹效法黃帝,“以身為度”,將左手中指第三節、無名指第三節、小指第三節的長度合為九寸。他請求徽宗將左手這三節的長度賜予臣下,以確定黃鐘律的律管長度,再由律管推定容積。先鑄造九鼎,以象征天下九州;再鑄造高九尺、容九斛的大鐘,以為標準器;最后再鑄造新樂編鐘。
這番說法迎合了篤信道教的徽宗皇帝的心思。于是,在劉昺的督導下,負責樂器鑄造的機構——“鑄瀉務”,便按照魏漢津的理論,參照宋公戌鐘,開始了緊鑼密鼓的興造。同年七月,作為標準器的景鐘鑄成。次年七月,九鼎成。八月,編鐘等新樂樂器成。按照當時的禮制,大晟鐘共有十二編,每編二十八枚,包括正聲鐘十二枚、中聲鐘十二枚、清聲鐘四枚,共336枚。
九月朔,徽宗駕臨大慶殿,與百官慶賀“鼎樂”落成。在新樂演奏的時候,居然有白鶴數只,從東北方飛來。于是龍顏大悅,下詔褒美。至于新樂的名號,既然堯樂稱“大章”,舜樂稱“大韶”,今樂直追上古,徽宗便賜名“大晟”。新樂編鐘被稱為“大晟鐘”。創制大晟樂是徽宗的得意之作。在接下來的數年里,大晟鐘被寶藏于宮中,大晟樂則被頒行于四方。
可是,四海弦歌擋不住金人的鐵蹄。大晟鐘鑄成之后二十二年,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攻入汴梁,徽、欽二帝被俘往北方。336枚大晟鐘,或在圍城之際被宋人埋入汴梁城下,或作為戰利品被金人賞賜臣下,或被解往金都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
八年之后,徽宗死于五國城(今黑龍江省依蘭縣),大晟鐘卻繼續在金人宮廷里演奏。只是,金太宗名完顏晟,為了避諱,金人磨去了鐘上的“大晟”,而重刻了“大和”二字。入元后,大晟鐘流入元宮。元明鼎革,明人仍“斟酌用之”(明代朱載堉《樂律全書》),直至清初。到了乾隆年間,梁詩正、王杰等人奉敕將宮中所藏古銅器編纂成書,發現內廷有四件刻有“大和”字樣的古鐘。時人已不知曉它們的來歷,以為是周代的古器,便將其編入了《西清古鑒》及《西清續鑒乙編》。其中兩件民國時被運往臺灣,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另兩件下落不明。
如今,已知存世的大晟鐘僅有25枚。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八枚,有兩件是清宮舊藏,其余六枚則來自購買、調撥和捐獻。1958年購藏的那件,刻有“大和”二字,并且有明顯削磨過的痕跡,顯然是靖康之難的見證者。這八枚囊括了大晟鐘的全部三個類別,涉及了七種樂律,是音樂史研究的重要材料。經檢測,它們仍能發出清晰的樂音。裊裊余聲中,它們似乎還在訴說著汴京的繁華、亡國的悲涼和千年的滄桑。
陳鵬宇(作者單位:故宮博物院器物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