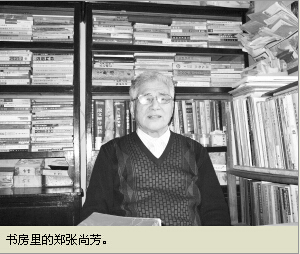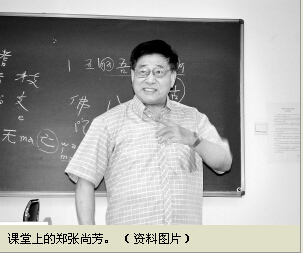精彩推薦
熱點關注
專題推薦
-
沒有記錄!
熱點排行
(河洛春秋 李賀故事)昌谷覓蹤:尋找李賀故里
2014/12/4 16:43:18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中唐詩人李賀,宜陽人,才華奇絕,號稱詩鬼,是毛澤東最為推崇的詩人。他7歲能詩,15歲名滿京華,27歲去世,短暫的生命如一道閃電劃破詩壇夜空。“天若有情天亦老” ,詩魂年年哭早夭!我們在痛惜李賀早逝的同時,也為洛陽擁有這樣一位天才詩人而自豪——今日起,本報推出李賀系列,全面展現李賀短暫而又悲愴的一生。
現在看到的這通碑,立在鄭盧路北側三鄉鄉政府對面,顯然是紀念詩人李賀的。我站在這里看了半天,心里非常不是滋味——碑亭周圍放著許多雜物,無論從哪個角度拍照,都會有不諧調的雜物進入鏡頭。碑亭環境治理得不怎么樣,但為了爭奪李賀故里,當地人卻下了很大工夫——迄今為止,至少有兩個村莊在爭奪這張名片。李賀故里究竟在哪里?文字官司一直打了幾十年。
田野里擱淺的一條路
前往李賀故里,正是立秋前夕,天氣不怎么熱,公路兩旁一片綠色。從洛陽出發,沿鄭盧路一直向西,快到三鄉鄉政府時,路邊一位老人指著田野里一條荒廢的路對我說,順著這條路往北走,才是真正的李賀故里——西柏坡。
我聽了很是驚訝,這里怎么也有個西柏坡?老人見我不信,便彎腰撿起一根樹枝,在地上寫下了村名,這個名字竟跟河北省平山縣那個“西柏坡”一字不差。老人調侃道,宜陽的這個西柏坡,雖不是革命圣地,但也有些來歷,它是李賀故里!
這把我搞糊涂了!“李賀故里”不是在那個碑亭處嗎?此前我曾多次到過那里,早認得那個碑亭了,離這兒還有一段路呢,怎么這里又冒出了個李賀故里呢?老人告訴我,關于李賀故里的爭論,至今沒有停止過,幾個村莊為此爭斗不休,這事兒曾在本世紀初鬧得沸沸揚揚。
當時,有人認為李賀故里在西柏坡,也有人認為在西村。記者實地看了一下,這兩個村莊同屬三鄉鄉,只不過西柏坡靠近洛陽,西村靠近洛寧,中間夾著鄉政府和連昌河,兩村之間的距離也就四五里。為了爭奪李賀故里的擁有權,兩個村莊官司不斷,搞得地方官員都有點不好意思,但記者聽了,反覺得有意義!這說明如今的農民,頗有地方文化保護意識,他們除了關心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之外,還關注文化,這是好現象。
李賀故里的具體位置到底在哪里?的確很難說。唐詩人李賀英年早逝,“復無家室子弟”,他去世不到二百年,家園就已荒蕪。宋代詩人張耒來過李賀的老宅,說這里“清溪水拱荒涼宅,幽谷花開寂寞春”,從而發出了“天上玉樓終恍惚,人間遺事已成塵”的感慨。張耒當年看到的李賀故里房屋都已坍塌,只留殘墻,何況千年之后的今天?
李賀故居究何在
李賀在詩里說自己的家鄉在“昌谷”,但“昌谷”是個大概念,《辭源》解釋為“水名,一名昌澗,又稱刀環川。源出河南澠池界,東南流之宜陽入于洛。唐詩人李賀的故里,即今昌水與洛河匯流處的三鄉一帶”。
但據記者了解,《辭源》的這種解釋,本身就是錯誤的,因為“昌澗”本名連昌河,不是發源于澠池,而是源于陜縣的馬頭山,向東流來時,呈西北——東南走向,經過洛寧楊坡,一路來到宜陽三鄉,其間的河谷地帶,廣義上都可稱為“昌谷”,包括澠池、洛寧、宜陽境內的整個連昌河谷地帶。李賀故里的昌谷,只是其中一段,那么,李賀家的具體位置在哪兒呢?
后來,山西大學教授楊其群、湖南師大教授劉衍也認為,把李賀故居定在“昌谷”太籠統,他們經過實地考察,最后認定李賀故居應在大澗溝“長巒谷口”。
那么,大澗溝“長巒谷口”在什么地方?
據當地人描述,大澗溝為一條自然河谷,長約幾華里,深約三四丈;“長巒谷口”在漢山光武廟南的幽谷出口附近,位于西村正北六七百米處,此處向東四五里,就是西柏坡村了。這就是說,李賀故居離西村近,距西柏坡遠。
針對這種說法,宜陽縣歷史文化研究會會長喬文博表示懷疑,他說,楊其群把李賀故居定在大澗溝,顯然不妥,因為大澗溝寬不過十丈,深不過三丈,只是條小土溝而已,如此狹促的地方,怎能建宅?楊先生還根據李賀詩中不斷出現的“山居”二字,把李賀所謂的“山居”定在山口北面的山坡上,把南邊所謂的“銳峭長圓形山頭”稱之為“南山”,把目前已經干涸的小水溝夸大為“唐時水勢大到可以釣魚,可以下網、可以泛舟”的河,這一系列的推斷實難令人信服。
喬先生認為,中唐時期,人丁稀少,土地廣袤,李賀的父親李晉肅做過縣令,這樣的官宦之家,怎會選個小土溝安家?再說了,李賀所稱的“山居”,并不一定是居住在山里,因為文人寫詩,有時為了營造意境,便說自己的家園為“山居”;有時候為了自謙,便說自己居住于“窮巷”、“陋室”、“草堂”、“茅廬”。這本是慣常的寫法,如果僅僅根據“昌谷山居”幾個字,就把李賀故居定在山坡上,那就不能理解為李賀住在平地上、西柏坡上?李賀的詩用“憶山居”為題,不過是為了突出他鄉居生活的情趣,若把“昌谷山居”理解為昌谷山坡上的房子,就情趣全無了。
喬先生說,楊其群先生為了支持自己的“山居”觀點,還以李賀的詩句“我在山上舍,一畝蒿磽田”為例證,認為此句“明白無誤地指明李賀故居在‘山上’”。其實“我在山上舍,一畝蒿磽田。夜雨叫租吏,舂聲暗交關”這首詩,不過是李賀極言其家境困頓而已——家里種著一畝薄田,時有官吏催租。這顯然是夸大之詞,從李賀當時的境況來看,“山上舍”只是說李賀家為照看山上的田地提供給長工居住的“別舍”,而非“本宅”。李賀生活的德宗、順宗、憲宗時期,全國人口不過3000萬,地廣人稀,人均耕地絕對不止一畝,在這樣一個人口稀少,而耕田頗廣的地方,一戶人家擁有數十畝耕地應該不是難事,更何況李賀家里還養著長工短工?
所以,喬先生認為僅憑“山上居”幾個字,不能斷定李賀故居就在山上,而“一畝蒿磽田”,也不能說明李賀家就僅有一畝地。記者聞聽此言,就地觀察了西柏坡村,發現此村雖在一片平地之中,但北面有山,南面有竹園。喬先生說,李賀詩中多次提到的“北園”,應該就在西柏坡村附近,李賀故居應離這個園子很近,不會往西跑到大澗溝里。
盼建紀念館 及早慰詩魂
針對這種說法,曾在洛陽電視臺《河洛論壇》欄目中講述過《李賀其人其詩》的王愷先生不同意。王先生也是宜陽三鄉人,現在洛陽執教,多年來研究李賀,積累了不少資料。他對記者說,他的家鄉離李賀故居很近,他曾多次考察過大澗溝,認為楊其群先生的觀點是正確的——李賀故居就在大澗溝內,不在西柏坡。
王愷先生說,要考證李賀故居,必須從李賀及古人的詩歌中去找信息——李賀故居的第一個特征是“清溪幽谷”。曾在宜陽做官的北宋詩人張耒寫過《春游昌谷訪李賀故居》一詩,開頭便是“連山忽中開,砑若敞雙戶”,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李賀故居在一個狹長的深谷之中;李賀在《南園十三首》第十一首詩中也稱“ 長巒谷口倚嵇家,白晝千峰老翠華”,這說明“嵇家”是李賀的近鄰,“長巒谷口”乃其故居所在。直到今天,三鄉人仍把“長巒谷口”稱做“嵇家圪塔”。
至于說現在大澗溝干涸無水,不等于唐代也無水。王愷舉了一個例子,20年前,西村村民曾在大澗溝打水井,先后打了七眼井,開始時都是黃土,容易掘進,但打到一定深度后,便全都打在了石頭上——原來下面是條連在一起的河床!這說明大澗溝原來很深,后來因為水土流失,淤泥堆積,看起來才像是小土溝了。
他說70年前,這里還有清清溪水,年長的人還記得婦女們在澗邊洗衣的情景。西村磚場在大澗溝挖土時,曾挖出過一個“船錨”,可見過去這里可行船,水勢很大。1958年,大澗溝曾修建過一個水庫,池水泱泱,皆澗水所匯,豈能無水?李賀詩中顯現出的字眼,明確地指出他家附近“青溪水拱”,有山,有水,有竹林,這正是詩人故居獨有的特征。
王先生說,我們應當用發展的眼光來看事物,不應以今天澗溝無水就斷定古代也無水。歲月悠悠,已逾千年,地理氣候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有多少條河流的水量在減少?又有多少個山谷被淤平?自然生態的改變可以讓一條河流在我們眼皮兒底下慢慢干涸,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所以,唐時的大澗溝應該有水,這符合人們逐水而居的特點;而山谷坡地正好依山建房,背依青山,面對溪水,符合風水學建房筑宅的規律。李賀詩“家泉石眼兩三莖,曉看陰根紫脈生”(《昌谷北園新筍四首》之三)應是其家門前溝中溪水邊的景象;這門前的溝谷,亦或為李家的宅居屬地。這“幽谷”、“家泉”、“清溪水拱”,以及“水曲春沙上”、“新篁拔玉清”的綜合地理環境,均符合大澗溝的地望風景,而連昌河以東的西柏坡一帶,則與這樣的地理環境相悖——一個“幽”字,已把西柏坡的平曠地帶給排除了。
另外,李家乃官宦之家,不是耕稼農家,李賀詩“我在山上舍,一畝蒿磽田”(《送韋仁實兄弟入關》)是詩人的自謙,是詩化的語言。這兩句詩只可考證第一句,第二句不可當真,李賀家絕不只有“一畝”薄田,否則二十幾歲的他不可能還留著長指甲,終日騎著瘦馬,帶著書童,悠游于田野之中,到處吟詩了。“昌谷山居”說明李家有充足的物質生活保障,然后才能悠閑地居住在山野中,遠離耕田稼穡之苦。
宜陽舊縣志記載,唐朝不少詩人,都有詠三鄉的詩,其中多次提到“三鄉城”。唐時的三鄉城殘破不全,但仍有城墻在。“長巒谷口” 東二十多米的地方便是城墻大門,上有斜橋架構,李賀故居在其西鄰,也就是今天的西村一帶。
好了!雙方的辯論若江河濤聲不絕于耳。記者聽了,一方面為他們的求證精神所感動,一方面又為李賀著急——因為如今這里除了一兩個李賀紀念碑外,紀念館等設施還沒建成,這怕是詩魂最最遺憾之事!
孫欽良
責任編輯:C006文章來源:洛陽網(2009-08-14)
下一條:沒有了上一條:火神廟村抱犢寨的三次“轉身”(洛陽傳統村落)
著名人物
沒有記錄!
精彩展示
沒有記錄!
評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