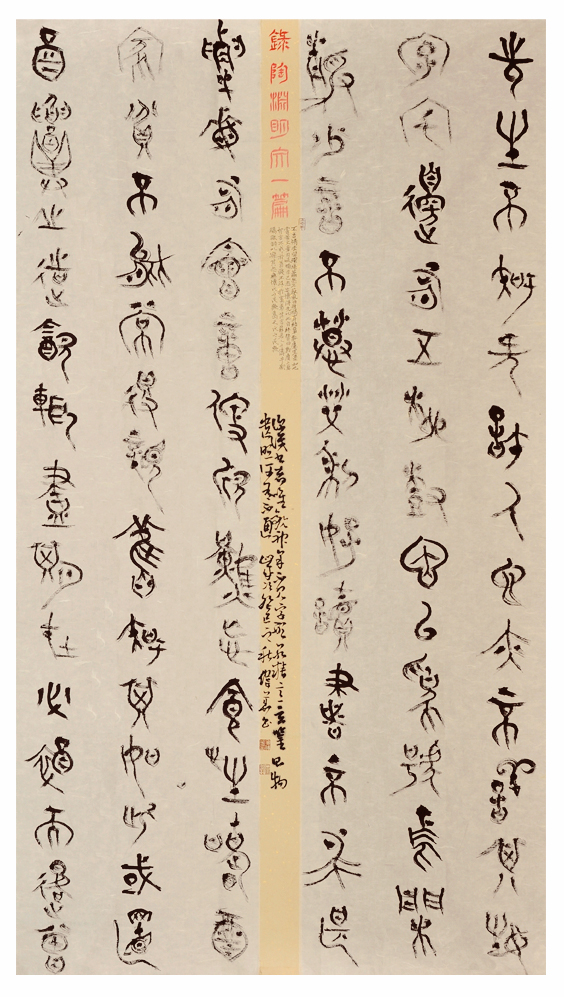-
沒有記錄!
孔子為何推崇《詩經》?
2013/10/30 9:46:31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10月8日《今晚報》刊出來新夏先生的《說〈詩經〉》一文,講到周朝以禮、樂為教化之本,伴音樂之詩在民間流傳,最后形成三百篇之編,因其有很高的藝術水平,流傳開來。除了因為《詩經》本身有其獨特的史料價值外,來先生還說:“三百篇為人所重,則因孔子之推重。”至于《詩經》為什么受孔丘推重,來先生沒有細說。
周朝以禮、樂為教化,這沒什么疑問。唯應探討的是周朝所謂的禮、樂各是什么。從現存的文字文獻和出土文物實證來看,夏朝只是傳說中的一個歷史階段,沒什么禮、樂可言,到了商朝,留下來的確鑿可信資料也不多。孔子距離這兩個朝代并不太遠,他已經說“文獻不足”(見《論語·八佾》),他的弟子對夏商之禮卻說得頭頭是道,這說明他們沒有老師在學術上態度那么端正。
到了周朝,承繼了商朝的文化。商人推崇天神,周朝人不信,持強烈的懷疑態度。但周朝人在現實中也很推崇天神,看起來奇怪,實際也不矛盾:他在自己原來的子民那里,對天神的存在進行質疑,以表示對前朝的否定;而在被他占領的、原來是商朝遺民居住的地域繼續推行天神思想:完全當作愚民政策,來統治信仰天神思想的商朝遺民。在這個過程中,周朝形成了一套嚴格的禮儀,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實際上就是維護統治者統治地位的一套嚴刑峻法。
然而,為了掩蓋真實意圖,統治者又以樂為外衣,給嚴刑峻法罩上一層美麗的彩飾。班固在《漢書·禮樂志》里講得不少,孔子說:“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這就把樂的作用無限拔高,到了與天齊肩的地步:以為文化發達了什么問題都能解決,人們就能安居樂業。其實,這也是統治者麻痹人民、渙散其斗志的一個手段。當年,德國和日本的文化不可謂不發達,但卻給世界人民留下了慘痛的記憶,這也能從側面否定孔子所夸大的“樂”的作用。
在中國古代,特別是周朝,“樂”的意義很廣泛,不僅僅指音樂、舞蹈、詩歌,也包括繪畫、雕塑、建筑,甚至田獵、廚藝、祭祀儀式等也含在內。從這個意義來說,舉凡人們感官的享受內容,似乎都可以囊括進“樂”這個大雜燴的盤子里。
在周朝時,學者不多。隨著社會的發展,中國學術發展史出現了繁榮的諸子百家的景象,各家對“樂”的態度也是不同的;從他們不同的態度里,也反映出中國古代學者對社會的各種認知和識見。
不用說,墨家主張“非樂”,因為他們認為樂費財費時費力,所以墨子說“為樂非也”;道家更走極端,根本就認為無為最好,五色五聲等“皆生之害也”。
與上述兩家的思想相反,儒家是主張享受的。作為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并不總是一本正經,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論語》里就多次記述了他的“樂”生活,例如“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活脫脫一個風流倜儻的樂人形象。但是,他并不是為藝術而藝術的所謂知識分子,而是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主張與民同樂,是為了讓人民更聽話,更喜歡這些樂。為達到這目的,就必須進行良好的樂的創造和制作,以使人民熱愛它,利用它,從而能更好地維護封建帝王的統治秩序。而《詩經》恰好是一個良好的載體,因此,孔子研究它,推重它。從學理上說,孔子推動了《詩經》的傳播;從根本上看,孔子是順應其儒家思想體系的。(原標題:孔子為何推崇《詩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