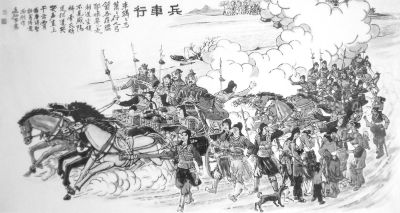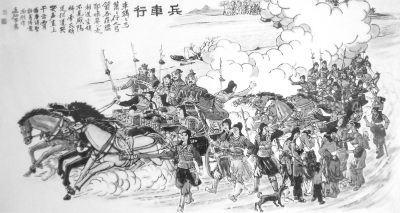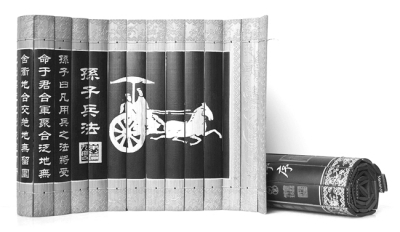-
沒有記錄!
謀道取勢贏天下——從劉伯承元帥的一聲嘆息說開去
2013/11/11 10:07:12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特邀嘉賓 國防大學軍隊建設與軍隊政治工作教研部主任 李升泉 少將
所謂文明,其實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那些東西。那么軍事文明,其實就是對軍事行動中野性行為的一種規范和約束。比如從虐殺俘虜到不殺俘虜再到寬待俘虜,從攻城掠地,玉石俱焚到不傷及無辜等等。同其他文明一樣,中國文化中有著非常豐富的軍事文明。
我軍事文明的內核
中國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一部戰爭史。當然,這不是說中華民族是一個好戰的民族,而是有著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國有著追求統一的歷史傳統。兩千多年,歷經無數的分裂和動亂,但終歸要統一。所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分于戰爭;合,也合于戰爭。其次,中國的地理位置,一面臨海,三面高山峻嶺和大漠,地勢局促。由于農業生產力水平的低下,人口繁衍到一定程度,社會財富和土地集中到一定程度,民眾便不能維持生存,只有起來造反,用武力來實現財富和土地的重新分配。再次,封建社會的皇權統治和與此相伴隨的地主貴族專制,阻止了社會精英改變地位的渠道和機會,只有改朝換代才能實現他們的政治抱負。這幾種因素相結合,于是便出現中國所特有的戰爭文化或者說軍事文明。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文明中政治經濟等著述相對較少,但兵書很多;中華民族在人類歷史上的發明創造并不多,但軍事謀略學卻非常豐富,并且與宮廷陰謀、官場斗爭相交織,至今為人們所津津樂道;中國歷史上真正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寥若晨星,但軍事家卻相對較多;還有一個現象,就是大政治家也大多同時是軍事家。這樣一種情況造成的結果是,大部分情況下戰爭成為了解決問題的選擇和最后手段,中華民族經受了深重的戰爭災難。宋人張養浩在一首《山坡羊·潼關懷古》里寫道:“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中國真正的大軍事家,都是胸懷大愛,而非斬首萬級以博取名位之輩。據說,劉伯承元帥在每次戰爭發起前都徹夜難眠,嘆息道,不知又會有多少孤兒寡母啊!這是戰爭中的人性光輝。因此,在充滿權謀和詭詐的中國戰爭史上,軍事家們提出以道勝,止戈為武;以勢勝,不戰而屈人之兵等重要思想。“謀道取勢而不以戰勝”,這是我們民族文明和智慧的體現,是我國軍事文明的本質內核。
立足這些變化來思考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人類文明的進步,今天的世界,政治斗爭形式、利益獲得的方式、戰爭的形態和樣式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新型軍事文明建設,也應立足這些變化來思考。這些發展變化,有哪些具體表現呢?第一、戰爭與政治的關系更加密不可分,戰爭可以是政治的繼續,也可能是政治的先導,或者本身就是政治。第二、人在戰爭中的作用更加復雜,人的決定因素不僅體現在戰爭中,更多的是體現在戰爭的現場之外。軍人和非軍人的界限將更加縮小,軍民融合將在更高層次更深遠的意義上實現。第三、軍事戰略與軍事戰術的界限更加模糊,軍事戰略與軍事謀略正在逐漸融為一體,無論戰略還是謀略,都必須是國家層面才有意義,個別軍事指揮人員的所謂謀略已變得不那么重要。第四、國家疆域的內涵正在發生改變,土地的內涵已不是現代國家疆域的唯一表達,利益疆域成為國家疆域的一部分,戰爭對國家疆域的保護也有著新的要求。第五、軍人戰斗精神的培育和養成,已不能單憑正義的激勵或物質的刺激,必須賦予軍人所從事的戰爭以崇高的意義。第六、世界歷史上,國際格局的變化總是用戰爭來完成,這種狀況正在改變,以和平和發展的方式實現國際格局的不斷調整,正在變為現實,這將是人類的最大福音。因為在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下,許多過去需要戰爭解決的問題、達成的妥協,現在是可以通過經濟等綜合的手段來完成的。第七、現代戰爭可以做到的精確打擊,改變了傳統戰爭主要以殺傷有生力量來削弱敵方,以達成戰爭目的的情況。第八、一個國家經濟力量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不僅是軍事力量建設的條件和后盾,越來越多本身就是軍事力量建設。因此國家的發展戰略與國家的軍事戰略的一致性更加突出。
大眼界與大謀劃
從新的時代條件戰爭樣式的新變化新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出3個特點:一是當今時代的軍事或戰爭,對國家實力的依賴已經非常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等同于軍事實力。二是由于軍事和戰爭越來越昂貴,勝負越來越取決于國家的整體實力。所以,對世界上絕大多數中小國家來說,新軍事革命和現代戰爭是一件消費不起的奢侈品。真正意義上的戰爭,已不大可能在實力懸殊的大國與小國之間出現。三是戰爭的實現目的,今天已經可以有多種手段去實現,大國之間的戰爭實際上已經變化為一種態勢的營造,一種道義的爭取,一種威勢的形成。這樣一來,就與中國傳統軍事智慧的“以勢取”“以道勝”的思想高度契合。
中國傳統軍事智慧講究的“謀道用術”“設勢造局”“取經衡權”。實際上就是兩個層面的東西,一個是道義層面、規律層面、戰略層面,就是“道”、是“勢”、是“經”;另一個是具體層面、操作層面、戰術層面,就是“術”、是“局”、是“權”。道在中國文化中,是一個莫測高深的詞匯,是哲學層面的智慧,是中國智慧的頂端。所謂謀道取勢,就是在對事物主要矛盾正確認識、對發展趨勢準確把握的基礎上,促使朝著有利于我的方向發展。而術,則是解決具體問題的具體方法。道和術的關系,是主和從、本和末、決定和被決定的關系。我們可能把每一件與外國的軍事關系都處理得不錯,我們可能沒有丟失一寸土地,我們可能在每一次爭端中都占據著上風,但沒有道的支撐和依恃,偏離了勢,可能某一天會猛然發現,我們不知不覺間已經處于一個很不利的位置和態勢。我們天天在交朋友,可能有事時卻發現真正的朋友不多;我們在盡力處理每一次爭端,可能有一天卻發現事情正在變得復雜。這里的原因就在于,缺乏一個“道”字。如果沒有大眼界,就不會有大謀劃;如果缺乏明確的大目標、大思路,就不會有大戰略、大格局,也就談不上經略之道、經營之術。軍事文明是為國家大局服務的。建設現代軍事文明,既要研究“術”的運用,更要在“謀道取勢”上下功夫。比如,我們的軍隊發展、武器裝備研發、戰場建設、國防動員等等,是站在我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應謀之“道”、應取之“勢”上來思考謀劃,還是在一件一件具體問題的應對上來設計決策,這區別是很大的,結果也會根本不同。(原標題:謀道取勢贏天下——從劉伯承元帥的一聲嘆息說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