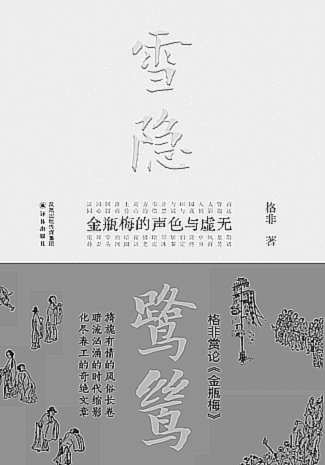中西文學史上常有這樣的著作,要跨越數十年乃至數百年的時間維度,人們才能比較清晰地認識其不朽的藝術價值。這正如久藏地下而被挖掘出來的寶劍,越磨而越見其炫目光亮與無比鋒利。《金瓶梅》正是這樣部獨特的小說。這部小說曾經很不名譽,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與探究的深入,特別是新時期以來,《金瓶梅》研究取得了甚為豐碩的成果。
近日,譯林出版社出版了清華大學教授、著名作家格非的《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作者從文本細讀入手,不但緊密結合明代社會史與思想文化史,更以世界文學與文化的眼光,悉心解讀這部“天下第一奇書”,使人們對之有了許多全新的認識。本書分為三卷。第一卷為《經濟與法律》,側重從經濟與法律的角度去解析《金瓶梅》;第二卷為《思想與道德》,重點研討《金瓶梅》的思想內容與道德判斷;第三卷為《修辭例話》,旨在發掘《金瓶梅》不落凡俗、令人驚嘆不已的敘事藝術。格非采用的是例話與隨筆的寫作方式,凡82篇,讓人讀來輕松自如,如沐春風。
一
格非研讀《金瓶梅》讀得非常仔細。真可謂洞微燭幽,而其立論則高屋建瓴,殊為深邃。格非在第一卷中悉心梳理《金瓶梅》中若干重要地理位置,分別寫了《清河》《清河國》《臨清》《鈔關》《淮上》和《南方》等數篇,頗多創見。在《清河》篇中作者寫道,《金瓶梅》沿用《水滸傳》“武十回”情節,將《水滸傳》的陽谷縣改回到了清河縣,“表面上看或許是屬于細枝末節”,實則關系重大。這不但“為正面描述依托北運河而興盛之北方商業經濟社會,選擇一個相對可信的地理位置”,更為重要的是,“表明作者在呈現明代商業經濟活動影響之下的社會現實和倫理方面,有了全新的考慮”,亦即“在描述社會現實方面另開新局”。因此,這種“地理細讀”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金瓶梅》這部作品非同凡響的敘事策略。
在《南方》篇中,格非指出:“作者似乎故意模糊了南北方的界限,南北交匯混雜。地理如此,經濟、商業如此,人物如此,風俗、器物、食貨、方言、戲曲、游戲也莫不如此。這種虛實結合的構思,不僅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明末社會由于商業的發展、社會形態和思想觀念的重大變革而導致南北文化交相融匯的基本面貌,也充分體現了作者全新的地理、人文和社會視野,展現了作者獨辟蹊徑的嶄新敘事氣度和格局,揭示出作者在藝術表現手法及修辭方面的野心。”《金瓶梅》中的地理位置,并非沒有人研究過,但像格非這樣見微知著,通過“地理細讀”,讀出《金瓶梅》作者如此巨大的良苦寫作用心,進而給人以耳目一新、豁然開朗的藝術啟示,當世恐無人能出其右者。
二
格非研究《金瓶梅》有著宏大的學術視野。本書序云:“如果不把《金瓶梅》放置于16世紀前后全球社會轉型和文化變革的背景中考察,如果不聯系明代的社會史和思想史脈絡,《金瓶梅》中涉及的許多重大問題,都得不到很好的解釋。”格非研究《金瓶梅》確乎不僅僅用中國小說史與文化史的眼光,還具有世界小說史與文化史的學術視野,將《金瓶梅》所描寫的有關問題給以“全球定位”,進而揭示其世界性的價值。
例如,在《同心圓》篇中,格非指出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在勾畫1400年—1800年間的世界經濟地圖時所看到的一個“同心圓”,與我們在《金瓶梅》中看到的“同心圓”,有重合的部分。作者因此在本文最后得出這樣的判斷:“全球格局的重大變化,特別是經濟格局的變化,迫使中國自明代開始,出現了微妙而深刻的社會轉型。傳統道德、法律及社會管理模式與經濟發展的慣性和動能之間,產生出極大的沖突和矛盾。而所有這些方面的沖突和矛盾,在《金瓶梅》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現。”顯然,倘若只通曉中國學術,很難充分認識到《金瓶梅》所反映的社會生活,事實上已與當時的世界經濟格局緊密聯系在一起。
此外,在《倫理學的暗夜》《自然、本然與虛無》等篇中,作者更是從廣闊的西方哲學史與文學史背景入手,特別是將《金瓶梅》的創作與18世紀法國作家薩德的情色文學創作作比較,指出它們以共有的情色修辭敘事藝術與激烈的反道德傾向,表達對社會的批判精神,是對他們所處時代與世界所認可價值的“蓄意顛倒”。在《故事》篇中,格非指出,《金瓶梅》新舊交織的敘事方式,完全可以與《棄兒湯姆·瓊斯的歷史》和《堂吉訶德》相提并論。《桂姐唱曲》篇則說:“《金瓶梅》中‘共時性’的場景敘事模式,在西方小說史上,要遲至20世紀初才被發明出來。”凡此,作者無不以世界文學與文化的廣闊視野,多方彰顯《金瓶梅》在世界文學史上卓爾不群的藝術成就。
與此同時,格非也從比較的視野,指出《金瓶梅》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的獨特價值。如《市井與田園》篇寫道,即使從描寫商業活動看,“對比明清之際的其他小說,《金瓶梅》從布局、主題到題裁,都堪稱一部全新的作品”;《真妄》篇云:“‘真妄’或真偽觀的確立,也為中國的章回體小說開辟了一個全新的天地”;《自然、本然與虛無》篇說:“如果說《金瓶梅》是對于一個世界的蓄意顛倒的話,那么,它偉大的后繼者《紅樓夢》則對它進行了再次顛倒。”
三
格非研究《金瓶梅》具有強烈的當代意識。格非寫作此書,不時與當下社會聯系起來。他在序中說:“我甚至有些疑心,我們至今尚未走出《金瓶梅》作者的視線。換句話說,我們今天所經歷的一切,或許正是四五百年前就開始發端的社會、歷史和文化轉折的一個組成部分。”《金錢崇拜》篇云:“西門慶人格的矛盾與偽善,毫無疑問,與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與偽善如出一轍。”無論中國還是西方當下社會,較之四五百年前,無疑是大踏步地向前發展了,但在社會人情的某些重要方面,卻并不同時進步。寧宗一先生就曾指出,《金瓶梅》是留給后人的禹鼎,它“所發出的回響,一直響徹至今”。因此,格非作上述判斷時,其內心無疑是無比沉痛的。這一方面固然展示了他之俯察古今與中西宏闊的學術襟懷,但同時也體現了一個嚴肅學者從事學術研究時所具有的強烈的現實關懷與深深的憂患意識。
格非在評論《金瓶梅》主要思想傾向與西門慶這個人物形象時也是徹其底蘊,頗多新見。《書名之寓意》篇云:“作者透過色欲展現世情人倫,透過世情來書寫16世紀中國社會的經濟、商業、道德、法律、官場及種種世態,方為全書的關鍵。”《無善無惡》篇進一步指出:“《金瓶梅》的立足點,在于對社會現實的全方位批判。這種批判過于嚴厲,不留任何余地,使作品彌漫著強烈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氣息,以至于作者不得不引入佛道,作為世人在絕望現實中可能的超越性出路。”這就既簡要而又深刻地闡明了本書副標題所揭示的《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此主要思想傾向。
(作者為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