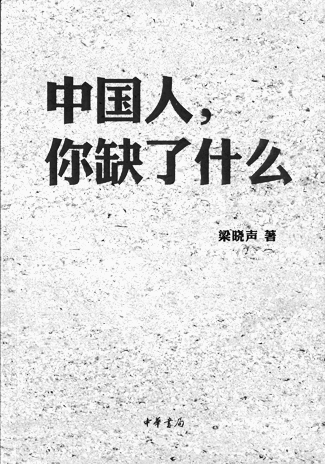-
沒有記錄!
百年文化的表情
2013/7/23 18:38:35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歷史的塵埃落定,前人的身影已遠,在時代遞進的褶皺里,百余年文化積淀下了怎樣的質量?又向我們呈現著怎樣的“表情”?
《聊齋志異》刊行于世二百多年。要越過百年先論此書,實在因為它是我最喜歡的文言名著之一。也因近百年中國文化的扉頁上,分明染著蒲松齡那個朝代的種種混雜氣息。
蒲公筆下的花精狐魅,鬼女仙姬,幾乎皆我少年時夢中所戀。
《聊齋志異》是出世的。
蒲松齡的出世是由于文人對自己身處當世的嫌惡。他對當世的嫌惡又源于他仕途的失意。倘他仕途順遂,富貴命達,我們今人也許—就無《聊齋》可讀了。
《聊齋》又是入世的,而且入得很深。
蒲松齡背對他所嫌惡的當世,用四百余篇小說,為自己營造了一個較適合他那一類文人之心靈得以歸宿的“擬幻現世”。美而善的妖女們所愛者,幾乎無一不是他那一類文人。自從他開始寫《聊齋》,蒲松齡幾乎一生浸在他的精怪故事里,與他筆下那些美而善的妖女眷愛著。
但畢竟,他背后便是他們嫌惡的當世,所以那當世的污濁,漫過他的肩頭,淹向他的寫案——故《聊齋》中除了那些男人們夢魂縈繞的花精狐魅,還有《促織》《夢狼》《席方平》中的當世丑類。
《聊齋》乃中國古代文化“表情”中亦冷亦溫的“表情”。作者以冷漠對待他所處的當世,將溫愛給予他筆下那些花狐鬼魅……
《水滸》乃中國百年文化前頁最為激烈的“表情”。由于它的激烈,自然被朝廷所不容,被列為禁書。它雖產生于元末明初,所寫雖是宋代的反民英雄,但其影響似乎在清末更大,預示著“山雨欲來風滿樓”……
而《紅樓夢》,撇開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主線,讀后確給人一種盛極而衰的挽亡感。
此外還有《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游記》《孽海花》——構成百年文化前頁的譴責“表情”。
《金瓶梅》是中國百年文化前頁中最難一言評定的一種“表情”。如果說它畢竟還有著反映當世現實的重要意義,那么其后所產生的不計其數的所謂“艷情小說”,散布于百年文化的前頁中,給人,具體說給我一種文化在淪落中麻木媚笑的“表情”印象……
百年文化扉頁的“表情”是極其嚴肅的。
那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政治思想家輩出的歷史時期。在這扉頁上最后一個偉大的名字是孫中山。這個名字雖然寫在那扉頁的最后一行,但比之前列的那些政治思想家們都值得紀念。
于是中國百年文化之“表情”,其后不僅保持著嚴肅,并在相當一個時期內是凝重的。
于是才會有“五四”,才會有“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百年文化“表情”中相當激動相當振奮相當自信的一種“表情”。
作家魯迅的“表情”個性最為突出。《狂人日記》振聾發聵;“彷徨”的精神苦悶躍然紙上;《阿Q正傳》和《墳》,乃是長嘯般的“吶喊”之后,冷眼所見的深刻……
“白話文”的主張,當然該算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事件。倘我生逢那一時代,我也會為“白話文”推波助瀾的。但我不大會是特別激烈的一分子,因為我也那么地欣賞文言文的魅力。
“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之爭論,無疑是現代文學史上沒有結論的話題。倘我生逢斯年,定大迷惘,不知該支持魯迅,還是該追隨“四條漢子”。
這大約是現代文學史上最沒什么必要也沒什么實際意義的爭論吧?
但是于革命的文學、救國的文學、大眾的文學而外,竟也確乎另有一批作家,孜孜于另一種文學,對大文化進行著另一種軟性的影響——比如林語堂、徐志摩、周作人、張愛玲……
他們的文學,仿佛中國現代文學“表情”中最超然的一種“表情”。
甚至,還可以算上朱自清。
我從前每以困惑不解的眼光看他們的文學。怎么在國家糟到那種地步的情況之下還會有心情寫他們那一種閑情逸致的文學?
現在我終于有些明白——文學和文化,乃是有它們自己的“性情”的,當然也就會有它們自己自然而然的“表情”流露。表面看起來,作家和文化人,似乎是文學和文化的“主人”,或曰“上帝”。其實,規律的真相也許恰恰相反。也許—作家們和文化人們,只不過是文學和文化的“打工仔”。只不過有的是“臨時工”,有的是“合同工”,有的是——‘終生聘用”者。文學和文化的“天性”中,原有愉悅人心,僅供賞析消遣的一面,而且,是特別“本色”的一面。倘有一方平安,文學和文化的“天性”便在那里施展。
這么一想,也就不難理解林語堂在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與魯迅相反的超然了;也就不會非得將徐志摩清脆流利的詩與柔石《為奴隸的母親》對立起來看而對徐氏不屑了;也就不必非在朱自清和聞一多之間確定哪一個更有資格入史了。當然,聞一多和他的《紅燭》更令我感動,更令我肅然。
歷史消弭著時代煙靄,剩下的僅是能夠剩下的小說、詩、散文、隨筆——都將聚攏在文學和文化的總“表情”中……
繁榮在延安的文學和文化,是中國有史以來,氣息最特別的文學和文化,也是百年文化“表情”中最純真爛漫的“表情”——因為它當時和一個最新最新的大理想連在一起。它的天真爛漫是百年內前所未有的。說它天真,是由于它目的單一;說它爛漫,是由于它充滿樂觀……
建國后,前十七年的文學和文化“表情”是“好孩子”式的。偶有“調皮相”,但一遭眼色,頓時中規中矩。
“文革”中的文學和文化“表情”是面具式的。
“新時期文學”的“表情”是格外深沉的。那是一種真深沉。它在深沉中思考國家,還沒開始自覺地思考關于自己的種種問題……
上世紀80年代后期的文學和文化“表情”是躁動的……
上世紀90年代前五年的文化“表情”是“問題少年”式的。它的“表情”意味著——“你”有千條妙計,“我”有一定之規……
上世紀90年代后五年的文化“表情”是一種“自我放縱”樂在其中的“表情”。“問題少年”已成獨立性很強的“青年”。他不再信崇什么。它越來越不甘被拘束。他渴望在“自我放縱”中走自己的路。這一種“自我放縱”有急功近利的“表情”特點。也每有急赤白臉的“表情”特點,還似乎越來越玩世不恭……
據我想來,以后的中國當代文學和文化,將會在“自我放縱”的過程中漸漸“性情”穩定。歸根結底,當代人不愿長期地接受喧囂浮躁的文學和文化局面。
歸根結底,文學和文化的主流品質,要由一定數量一定質量的創作來默默支撐,而非靠一陣陣的熱鬧及其他……《中國人,你缺了什么》 梁曉聲著 中華書局 (原標題:百年文化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