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記錄!
- 1、阮咸與琵琶的故事
- 2、管仲齊勸諫桓公止封禪
- 3、胡秋萍書法欣賞
- 4、白居易 牡丹 牡丹詩
- 5、讓每個人都有勞動出彩的機會
- 6、焦作市召開勞動模范表彰大會
- 7、他想在南京找找謝安的后人
- 8、黃帝的傳說故事
東漢蔡邕與南國山水相伴的十二年
2013/2/26 16:53:45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2012年10月19日,寧遠九嶷山玉琯巖。永州市文物管理處的楊宗君正忙于對此處的摩崖石刻進行拓片,他手下的《九嶷山碑(記)》據記載由漢蔡邕所作,后由宋人李挺祖書寫于此。據楊宗君介紹,這是永州3處與蔡邕有關的石刻之一。

紹興縣,2003年重修的柯亭。傳說,公元180年左右的一個深秋,蔡中郎取這座漢代驛亭的東第十六根椽竹做了一根竹笛。2012年10月25日,重修的柯亭,乾隆的詩碑在亭子的走廊里,只是,柯亭已“無處問中郎”。

溧陽市觀山村,遍植松柏、大栗樹的山中,“蔡邕讀書臺”,除了山腳下一塊溧陽市政府立的文物指示碑外,沒有任何標志可以讓人將這座荒山坡與歷史聯系起來。不時出現一只鹿安靜地吃草,毛已脫落,鹿角被割掉,看起來是如此蒼老。

瀟水河邊,古道州八景之一,含暉巖摩崖石刻。除據傳由蔡邕手書的“水天一色”外,此處石壁上還有宋、明、清歷代石刻17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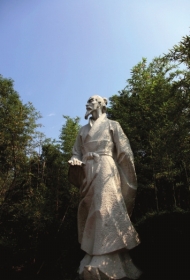
人物 蔡邕(133年-192年),字伯喈,河南開封人,東漢文學家、書法家,書法精于篆、隸,通經史,但未完成續修漢史的愿望。漢獻帝時曾拜左中郎將,故后人也稱他“蔡中郎”。后漢三國時期才女蔡琰之父。

蔡邕足跡地圖。
□撰文/劉見華攝影/馬金輝張松
他,流放于北國,亡命于江南。廣義的江南,包括吳地,包括零陵。
在零陵,他只有石刻;在吳地,也僅有柯亭笛的音樂才能千古流傳。而這些,似乎都浮于表面。他內心深處的憂傷與憧憬呢?我們追隨了他在零陵與吳地(湖南與江蘇)的蹤跡,但似乎總和這“憂傷與憧憬”有些距離,不勝惶恐。何處問中郎?
永州之野、柯水之岸、溧水之北,1800多年前,那個已是中年的人,仍然帶著他的灑脫、飄逸,行走在中國南方的青山綠水或是窮山惡水間。
公元178年,他因評說國家大事被判罪充軍朔方郡(今烏蘭布和沙漠,當時仍為草原),一年后大赦,又在包頭的宴會上得罪了太守王智,再次被告發。他只好“亡命江海”。在南方山水間“積十二年”,從中年到老年。一生,續修漢史的理想從未實現,甚至從未開始。
小家伙已經不稀罕蔡邕石刻巖洞了,母親可憐他“除了縣城,哪里也沒去過”
永州之野。
《后漢書》中蔡邕亡命之地在吳地,今天的江浙一帶,無官無職無家業的他,靠“泰山羊氏”的救濟為生。但是,作為正史,沒有片言只語關于他來當時的零陵郡、今天的永州。
只有明萬歷《永州府志》、清光緒《湖南通志》等記載:蔡邕入永州后,凡名山勝跡,到處品題。
他“可能”在永州的三個地方留下石刻:寧遠玉琯巖、道縣含暉巖、江華秦巖。
2012年10月19日-20日,在高速公路仍不發達的三縣,我們依次走寧遠、道縣、江華。
這個線路與蔡邕當年可能的路線不一致。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長吳順東推測,如果他到過零陵,最有可能的,是從湘江轉瀟水直達道縣、江華。道縣往寧遠只能走陸路,但易迷路,艱難到一千多年后的徐霞客來此時還要沿途掛布條以標識。
玉琯巖就在九嶷山,山以舜帝出名,《史記》:“舜南巡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巖與舜帝有關,舜命樂工以玉琯十二支演奏韶樂,是為玉琯。
1800多年前,那個到處亡命的書法家、精通音律的高手一路披荊斬棘,到了這南國的叢林。他是沖著玉琯巖前的舜帝廟來的。
2002年至2004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發現漢代以來祭祀舜帝的祠廟遺址,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2年10月19日,我們到來時,考古所在進行后續發掘,這里將要建考古遺址公園和博物館。
蔡中郎該是站在南嶺之巔,望著“巖巖九疑,峻極于天”,然后,他的銘文里就是歌頌舜的圣德,“芒芒南土,實賴厥勛”之類。短短二三十字的文章,沒有抒發他的內心,沒有向千年后的我們展示他是愁苦還是灑脫。倒是現代人稱“這是最早的直接以永州風物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也是湖南文苑中最早的一篇銘文。”
銘文也不是蔡邕手跡,它是南宋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李挺祖補刻的。之所以由李來書寫,就是因為他工于漢隸,而蔡邕就是隸書大家。
也因為要建考古遺址公園,當地在進行碑文的拓片。除了蔡邕的銘文,還有后代大小二十余方石刻。做拓片的楊宗君是“永州最好的師傅”,自稱熟知山野中的每一方石刻。為證明自己的熟知,他脫口而出永州的三個蔡邕石刻:玉琯巖、含暉巖、秦巖。
道縣含暉巖取“山水含清暉”之意,位于縣城東3公里的上關鄉中山石村。石刻在溶洞內,南臨瀟水,現存宋至清代摩崖石刻27方。除蔡邕外,還有周敦頤、何紹基(清代書法家)等來此。
蔡邕的“水天一色”石刻在絕壁之上,下臨瀟水,只有在船上才能看到。村里現在很少有船,隨同我們前來的道縣文物局退休職工黃代新老人,幫我們找到一個漁民的小船。
黃代新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瀟水上還有運輸,江華產的木材順流而下到長沙,甚至還有放排。這可能是千百年來的景象,從蔡邕到周敦頤到何紹基。現在,瀟水只剩挖沙船,寧遠、藍山、新田都在這取沙。
40余歲的張鳳在菜地里,她的小兒子在旁邊玩耍。小家伙已經不稀罕巖洞了,羨慕外面的世界,母親可憐他“除了縣城,哪里也沒去過”。
秦巖在江華,三省交界地,東靠廣東清遠,南近廣西賀州。據說蔡邕到此時,書“秦巖”二字。現存11方石刻,多數已模糊不清。不管是否為真,碑文中說它是“研究江華早期歷史的實物”,對一個山區小縣有此功績,也是它的一種價值。
江華是瑤族自治縣,這里是瑤鄉,村子就叫“秦巖村”。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怕旅游公司知道后有麻煩”,他說,2003年以前他們是可以自由進洞玩的。事實上,“秦巖”在洞口,風景區雖以它為名,但游客是沖著溶洞來的,沒有人會注意石刻。
“就像明星分一、二線一樣,他在我們這只算二線人物”
2012年10月23日,我們從長沙過江西,夜宿諸暨,第二天至紹興縣。
1800多年前的蔡邕,從吳地至零陵,恐不會走這條路。在南方仍是茫茫山林,整個江西省所在的豫章郡才“四十萬戶”的時代,長江水道可能是當時最便捷的選擇。《中國歷史地理》記述:秦漢時代,南方的東西交通,多由長江水道。
號稱東方威尼斯的紹興,多水、多橋、多香樟。紹興縣駐地柯橋鎮,2000年紹興市、縣分離,當地人稱呼紹興縣仍按習慣中的“柯橋”名之。這里的一切都因“柯”字為名,柯山之下有柯水,水上有柯橋、柯亭。2003年,紹興縣把柯亭建成了現在這個有水榭、石橋、竹林的1萬平米的小公園。
公元180年左右的一個深秋,蔡中郎避難會稽,一路南下來到這個并不起眼的漢代驛亭。中郎該是累了,在亭中歇腳,一陣風吹來,使得亭椽咝咝作響,發出悅耳的聲音。仔細一看,是亭東第十六根椽竹被風吹出了樂聲。嘉慶《山陰縣志》載,他“知有奇音”,于是截取椽竹一段,制得竹笛一根,抵舌輕吹間,聲色清亮。
這是一個小巧的江南園林,翠竹環繞,前臨浙東運河(由浙江寧波至蕭山的古運河,與京杭大運河相連)。重建的柯亭是兩層、黑瓦的木構建筑,廊柱已變成黑色,漆也脫落。柯亭對面是“中國輕紡城”,柯橋的汽車站也叫輕紡城汽車站,這里以輕紡為名。
看門的園林局工人來自紹興鄉下,自稱“只讀了三年級,連字也不認識幾個”。他們平均幾個月就調換一次,并不知道自己看守著誰。
在公園晨練的江英,原在柯橋中學讀書,現已退休。“之前,這里就是柯橋中學,除了幾棵樹是老的,其余都是新建的。”
公園里的竹子也是新栽的,是為了映襯柯亭笛的傳說,但誰也說不清楚是否為當年的竹子品種。那笛子已永遠消失。
紹興縣園林局。蔚偉林局長拿明星作比,“就像明星分一、二線一樣,蔡邕在我們這也只算是二線人物。紹興市有魯迅,有周恩來,還有秋瑾。”“秋瑾,還是半個湖南人。”
蔡邕讀書臺所在山包被人承包、養鹿,旁邊開農莊,名字就叫“讀書臺”
無論是永州,還是紹興,可能都只是蔡邕亡命生涯中的浪跡之地,是否定居,千年后無人能說。溧陽,是唯一“能說”的他的居住地。
它位于江蘇省西南部,蘇浙皖三省交界。
1800多年前,溧陽西南,觀山腳下蒹葭蒼蒼的黃山湖,秀山麗水之間,蔡邕帶著全家找到了一個可以安頓的地方。
黃山湖中有一小島,山腳下的村子,臨水傍湖,雞犬桑麻,亦耕亦漁。山麓前是一條曲溪,溪通湖水,泛舟即達咫尺小島。蔡邕在島上筑臺讀書,撫琴習字,世稱“讀書臺”。
2012年10月26日,我們出溧陽市區,沿329省道南行。觀山迎面秀立,左側平疇田野里,一座孤峰遺世獨聳,這就是蔡邕讀書臺。
黃山湖在光緒年間尚碧波萬頃,后來湖面縮小,隨著大溪水庫的修建,古湖早變成了良田。
關于“蔡邕讀書臺”最早的史料,是宋朝景定年的《建康志》:“蔡邕讀書臺,在溧陽縣太虛觀東北”,到清代時,已是“牧童歌上讀書臺”(清宋璜詩),已無建筑。
南宋陸游曾有詩:“滿村聽說蔡中郎。”我們到這里時,村主任一聽說是“找一些歷史的”,也知道是讀書臺。這“滿村聽說”一直延續著。
讀書臺所在的山包已于2008年被一個叫彭學鋒的村民承包。他在山上養十來只鹿,割鹿茸,旁邊開農莊。農莊就叫“讀書臺”,繁體漢字。
我們找到彭學鋒,但此時卻是鹿的發情期,不能上山,“鹿隨時會出來撞人”。他攤開手臂的傷痕給我們看,“不僅是生人,我給他們喂食都是隔著鐵絲網扔過去”。他的生意很忙,甚至不愿意帶我們到山包上看一看,我們自己走到了讀書臺下。
為防止鹿跑掉,山包周圍被彭用鐵絲網圍住。因為有文物部門的告誡,這里是文物點,山體不能再被破壞,植被也不能毀壞,他就在上面養鹿。
這里屬于天目湖景區,只是待開發,所謂的湖,其實是兩個水庫。讀書臺所在的山包,在大壩下面,水庫灌溉著下面的農田。站在壩上,看到山間盆地中的讀書臺,很是突兀,可以想象它當年湖中小島的景觀。
溧陽市史志辦,一袁姓科長表示“對此不是很清楚,資料也很少”,主要是“讀書臺在溧陽不是很有名氣”。2001年,由溧陽文化局主編的《溧陽文物》中,甚至壓根沒有提到讀書臺。
[身后]
生于何地?“你就說河南開封人吧,不要具體到縣”
葬于何處?江蘇人說,他死前最眷戀吳地的安逸
《后漢書》記蔡邕是“陳留圉人”,這個不太清楚的記載,為今天河南開封市杞縣和尉氏縣的爭論留下了“隱患”。
連線尉氏縣史志辦時,可以感受到電話那頭的憤憤不平。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稱,只是因為郭沫若寫過《蔡文姬》,到過杞縣,郭又是當時的文化旗手,從此杞縣就把蔡邕、蔡琰當成他們的了。
“我們近些年找一些史料,剛做完報告,已經寄到《辭海》編輯部,要他們更正原來‘蔡邕’詞條中‘生于杞縣’的說法。我們已建成蔡邕紀念館,還準備建蔡邕碑林。一個月后,還有一個蔡邕誕辰研討會。”
最后,這位工作人員又帶著誠懇的語氣說,鑒于目前爭論還沒有結果,“你就寫是河南開封人吧,不要具體到縣”。
杞縣文化局則對這個爭論持謹慎的態度,他們覺得“不好說”,無論是文化局,還是文物處,“都不能解答這個問題”。
蔡邕墓更是“疑冢重重”,除了其“故里”杞縣和尉氏外,還有河南的開封縣、禹州市有“蔡邕墓”之說,甚至遠在江蘇的常州,地方志也有蔡邕死后葬于該地的記載。
開封縣文物管理所覺得“爭論沒啥意思”,“出現多個墓葬的很正常”。
禹州文物局的工作人員則在電話那頭討論了一陣,最終回復“還沒有這個文保單位”。
常州流傳的蔡邕墓在武進區,常州溧陽市文聯主席路發今在七八年前曾去看過,當時已經被村民建房,墓土早已在文革時被挖盡。他們一個流傳頗廣的說法是,蔡邕死前在獄中曾對人說:生于杞縣一生憂,死后東葬方得安。他不愿歸葬常年兵火連天的河南老家,而愿葬身風光秀麗、尚少戰事的吳地。那也是他一生中度過最安逸時光的地方。
[鏈接]
蔡邕、蔡琰(蔡文姬)與曹操:為報答恩師,曹操將蔡邕流落匈奴的女兒贖回來
大約在蔡邕38歲、曹操16歲時,兩人在洛陽相識,他們引為知己,也是師徒關系。曹操是個愛音樂的人,西晉張華《博物志》載,曹操“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桓譚、蔡邕善音樂,……太祖皆與奪能”,曹丕自稱“家公與蔡伯喈有管、鮑之好”,以春秋齊國管仲、鮑叔牙的友誼來比擬。
蔡邕無子,僅蔡琰一女。在他死去的那一年,蔡琰被入侵的匈奴俘虜,嫁給了匈奴左賢王,飽嘗了異族異鄉異俗生活的痛苦。她還學會了吹奏“胡笳”,學會了一些異族的語言。像其父蔡邕亡命江海十二年一樣,蔡琰也在匈奴生活了十二年。
在這十二年中,曹操也完成了北方的統一。當他得知恩師蔡邕的女兒還在南匈奴時,他立即派使者用重金贖回了蔡琰。京劇《文姬歸漢》就以此為藍本。
蔡邕立志仿效班固續修漢史,并因此理想而到洛陽追隨董卓,但到董卓被司徒王允誅殺時,他又被逮捕下獄。在獄中,蔡邕請求砍去雙腳,只為能“繼成漢史”,但最終沒能得免,死于獄中。
蔡琰則以班固之妹班昭為榜樣,希望替父親完成遺愿。但他們父女沒有班氏兄妹那般幸運。直到二百多年后,他們的心愿才由南朝的范曄完成(《后漢書》),此時,蔡邕父女也已成為書中人物。【原標題:東漢蔡邕,亡命南國山水十二年】
來源: 瀟湘晨報 時間:2012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