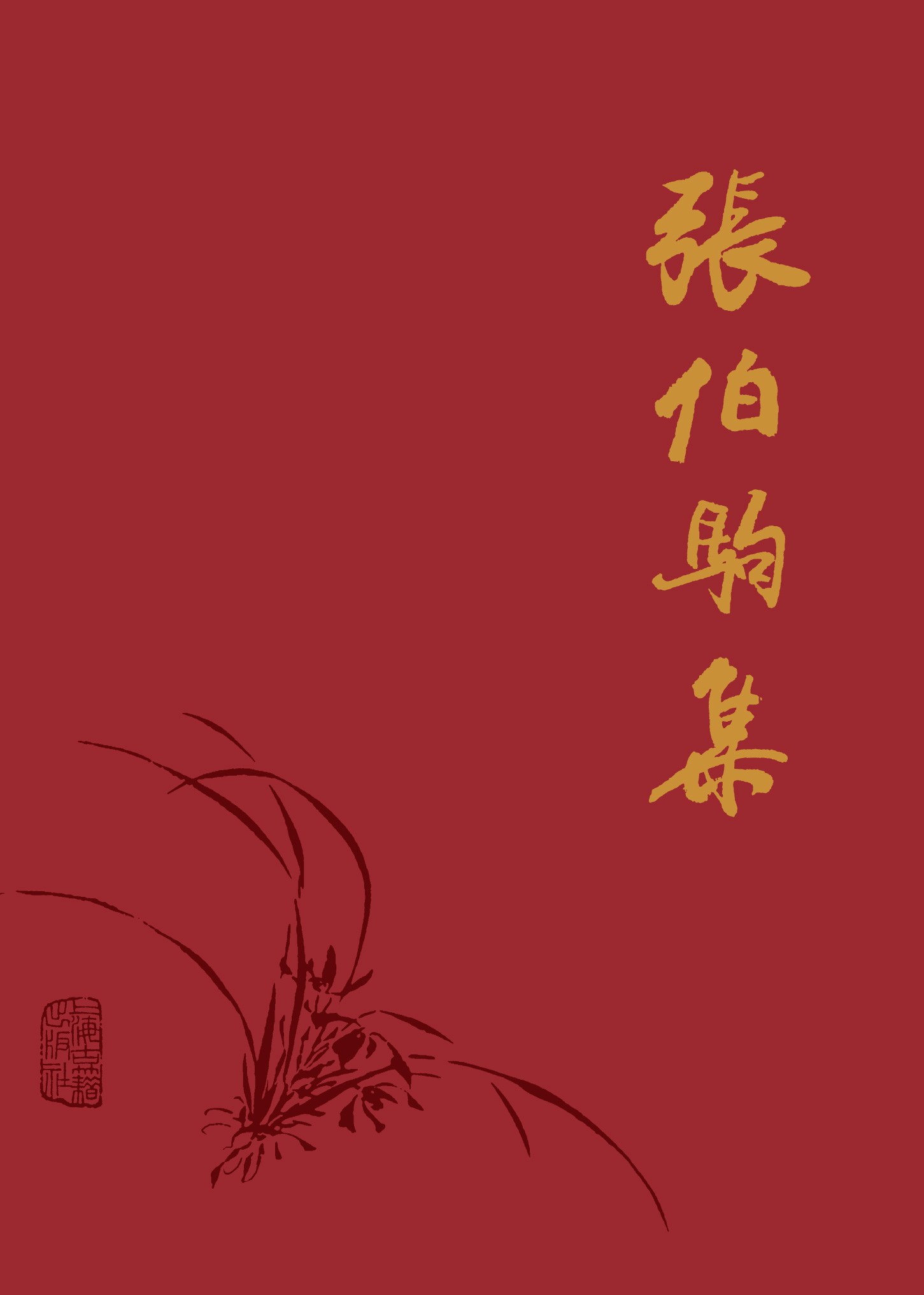-
沒有記錄!
張伯駒和京劇——讀《張伯駒集》隨筆
2014/12/24 10:44:48 點(diǎn)擊數(shù): 【字體:大 中 小】
張伯駒對于中國戲曲藝術(shù)具有廣博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理論,以此做出了很多獨(dú)到的評論。這些評論,也許不夠全面,那是因為他過分局限于“神韻”這唯一的標(biāo)準(zhǔn),而對其他美感有所忽視,這才會有對言菊朋和馬連良的過分貶損。但從深刻性來看,確實夠得上“第一義諦”。
張伯駒先生在中國戲曲界的名聲頗盛,趣聞尤其多。只是口耳相傳一久,就不免越傳越走樣,其形象也就不真實了。這不真實的形象,會影響到我們對于張伯駒戲曲藝術(shù)研究價值的認(rèn)知。因此,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的《張伯駒集》,甚為興奮。畢竟,張伯駒親手寫下的東西,對于我們認(rèn)識他的戲曲研究至關(guān)重要。
張伯駒的著作出版已久,重印的不多,所以搜求不易。這次出版的《張伯駒集》,將他的著作一網(wǎng)打盡,給讀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其中和戲曲尤其是京劇相關(guān)的資料主要是《紅氍紀(jì)夢詩注》和《亂彈音韻輯要》。(《亂彈音韻輯要》可謂京劇音韻學(xué)的扛鼎之作,但研究太專業(yè),這里就不評述了。)另外,《續(xù)洪憲紀(jì)事詩補(bǔ)注》和《春游瑣談》里也有一些,只是前者和《紅氍紀(jì)夢詩注》重復(fù)了不少。根據(jù)這些材料,可以容易地看到,一些傳聞實在不可靠。
比如說,大家一般都認(rèn)為,張伯駒在京劇上的獨(dú)到之處,是靠了豐厚的束脩和誠懇的態(tài)度,從余叔巖那里學(xué)到不少“掏心窩子”的東西,因此,他是個“純余派”。捧之者如此說,貶之者也如此說。可是不論捧之貶之,都有這個言外之意:張伯駒不知道也就不懂別的流派,只懂余派。如果看看他自己的文字,就知道這是個誤會。
張伯駒對于京劇的興趣,是從幼年培養(yǎng)起來的,并不是因為結(jié)識了余叔巖。他五歲被過繼給伯父張鎮(zhèn)芳(生父叫張錦芳),七歲跟隨張鎮(zhèn)芳來到天津,從此開始了他看戲的生涯。天津作為京劇演出的一個重要碼頭,名角演出極多。根據(jù)《紅氍紀(jì)夢詩注》的記述,他看過的老生名角就有譚派創(chuàng)始人譚鑫培、孫派創(chuàng)始人孫菊仙、劉派創(chuàng)始人劉鴻聲、許(蔭棠)派傳人白文奎,還有“小小余三勝”時代的余叔巖。另外,武生楊小樓、李吉瑞,武丑張黑,武旦九陣風(fēng),剛出科的青衣尚小云等,也是他看過的。甚至其他地方戲他也看。不過那時候他的欣賞水準(zhǔn)還不夠,所以兩次看譚鑫培,都不知欣賞。“余十一歲時,……偶過文明茶園,見門口黃紙大書‘譚’字,時晝場已將終,乃買票入園,正值譚鑫培演《南陽關(guān)》,朱粲方上場,余甚欣賞其臉譜扮相,而竟不知誰是譚鑫培也。”(《詩注》一三)“先君壽日……譚扮戲時,余立其旁,譚著破皇靠,棉褲彩褲罩其外,以胭脂膏于左右頰涂抹兩三下,不數(shù)分鐘即扮竣登場,座客為之一振,惜余此時尚不知戲也。”(《詩注》一九)也就不能分辨演員的高下,他說:“當(dāng)時譚、劉、孫齊名,但余在童時尚不懂戲,孰為高下,則不知也。”(《詩注》二七)不過他七歲時卻學(xué)會了孫菊仙的唱法。“余七歲時,曾在下天仙觀其演《硃砂痣》,當(dāng)時即能學(xué)唱‘借燈光’一段,至今其唱法尚能記憶。”(《詩注》二)相信幼時的張伯駒,對于京劇肯定是很熟悉的。甚至還會唱幾句山西梆子。“元元紅山西梆子老生唱法,人謂其韻味醇厚,如杏花村之酒。有人謂其《轅門斬子》一劇,尤勝于譚鑫培。余曾觀其演《轅門斬子》,其神情作風(fēng),必極精彩。惜在八九歲時,不能領(lǐng)會。惟尚記對八賢王一段唱辭。……童時余還能學(xué)唱。”(《詩注》一〇)
幼年的熏陶使得張伯駒逐漸對于中國戲曲藝術(shù)有了深入的認(rèn)識,也形成了極高的欣賞品味。他認(rèn)識到,中國的戲曲藝術(shù)和其他傳統(tǒng)藝術(shù)具有內(nèi)在的相通之處,它們具有相同的衡量標(biāo)準(zhǔn)。標(biāo)準(zhǔn)中最高的,他以“神韻”來概括。他說:“王漁洋詩主神韻,有論詩品詩,如其《過露筋祠》詩……即富于神韻者。詞以到禪境為最佳,如南唐后主詞‘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北宋晏小山詞‘落花人獨(dú)立,微雨燕雙飛’,皆臻禪境,亦即神韻。余自七歲觀劇,而認(rèn)為堪當(dāng)神韻二字者只有五人,乃昆亂錢金福、楊小樓、余叔巖、程繼仙,曲藝劉寶全也。汪桂芬余未趕上,譚鑫培、孫菊仙余曾趕上,但在童時,尚不懂戲也。”(《詩注》一〇七)這是他自己的心得,余叔巖未必能夠概括出來。可見,張伯駒選擇余派,不是因為偶然結(jié)識余叔巖的機(jī)會,而是基于多年的鑒賞實踐后高度的理論概括。說他只懂余派,顯然是“想當(dāng)然耳”的說法。再說,以他當(dāng)時對戲曲的癡迷和經(jīng)濟(jì)能力,怎么會不去看看別人的演出呢?而且,張伯駒也學(xué)過余派之外的戲,如跟錢金福“學(xué)《五雷陣》《九龍山》兩出,一飾孫臏老生戲,一飾楊再興小生戲”。(《春游瑣談·贈錢金福金縷曲詞》)當(dāng)然還不止此。因此,說張伯駒不懂余派之外的戲,純屬誤會。
當(dāng)然,有關(guān)張伯駒的傳聞走樣失真,也不是沒有他自身的原因。出身貴公子,不免帶上些習(xí)氣。習(xí)慣了受人逢迎的張伯駒,往往天真地把別人的客套當(dāng)做了現(xiàn)實,有些話看來實在太像自我標(biāo)榜了。他說:“夏日院內(nèi)置藤椅竹床,客坐于外,余與叔巖在室內(nèi)吊嗓,彼唱《桑園寄子》,余則唱《馬鞍山》;彼唱《馬鞍山》,余則唱《桑園寄子》。外面客不能分為誰唱,必至室內(nèi)問詢,始知也。”(《詩注》一四二)“與尚小云演《打漁殺家》,小云大為賣力,內(nèi)行謂之曰‘啃’,是日對啃,演來極為精彩,臺下甚為滿意。后有人云‘尚小云未啃倒張某人’,一時傳為話柄。”(《詩注》一六四)張伯駒的說戲錄音還有流傳,帶有較重的河南口音,說他的唱和余叔巖不能分辨,幾乎是不可能的。他畢竟是票友,缺乏專業(yè)演員高強(qiáng)度的幼工、演出鍛煉,要和名列四大名旦的尚小云爭長,恐怕也只能說是自不量力。
一旦別人把他這樣的習(xí)氣看作自我標(biāo)榜,就會認(rèn)為他的戲曲藝術(shù)評論也出于標(biāo)榜。比如,不少人會認(rèn)為,張伯駒只捧和余叔巖關(guān)系好的演員,反之,就加以貶損。其實,這也是個誤解。基本上說,張伯駒的評論還是忠實于他自己的藝術(shù)理論的。他既以“神韻”作為中國戲曲藝術(shù)的最高標(biāo)準(zhǔn),對于其他演員的衡量,也都是根據(jù)這個標(biāo)準(zhǔn)的。“神韻”要求擺落人工痕跡和感官愉悅,就和雕琢、甜熟格格不入。所以,張伯駒最傾服余叔巖,卻很不喜歡言菊朋和馬連良。他說言菊朋:“菊朋后下海演老生,宗譚鑫培,自命為譚派傳人。梨園內(nèi)行嘲其為‘言五子’……按言亦知音韻,如陰平高念,陽平低念,上聲滑念,去聲遠(yuǎn)念,入聲短念之類;但不知變化運(yùn)用,每韻尚有三級之妙;又以嗓左,遂至學(xué)譚反而映山隔嶺,奇腔怪調(diào),無一是處。”(《詩注》七八)按說,言菊朋和余叔巖同宗譚鑫培,張伯駒不該對言菊朋評論如此苛刻,所以有人以為是言菊朋和余叔巖存在競爭關(guān)系,張伯駒刻意貶低言。但實際上,言菊朋學(xué)老譚,幾于亦步亦趨,技巧的運(yùn)用不夠空靈,加上為嗓音所限,晚年唱腔更是走向險怪。這就不免于雕琢,和張伯駒的“神韻”標(biāo)準(zhǔn)相去較遠(yuǎn)。他說馬連良:“馬連良初師賈洪林,后亦不似,《借東風(fēng)》為其拿手戲。但武侯知天文學(xué),計時應(yīng)有臺風(fēng),因用火攻破曹軍,非能借東風(fēng)也。連良演此戲,竟使武侯如一妖道,乃腹無文學(xué)之故。”(《詩注》八一)這都近于吹毛求疵了,但仍然是因為馬連良“腹無文學(xué)”的原因。即馬連良的唱腔過于甜熟,近乎“元輕白俗”,顯得缺少深湛的修養(yǎng),和“神韻”相悖。可以說,張伯駒的評論還是從他自己的藝術(shù)理論出發(fā)的,和黨同伐異沒有關(guān)系。
對于這一點(diǎn),可以舉出一個反例。其實,余叔巖還有一個更大的競爭對手,就是已經(jīng)被人遺忘的王鳳卿。余叔巖二次出山搭梅蘭芳的“喜群社”時,頭牌老生就是王鳳卿。余叔巖一直被王鳳卿壓制,演出的戲碼也要經(jīng)常回避王鳳卿的。由于梅蘭芳第一次到上海演出時,得到王鳳卿的極力幫助,加之王鳳卿確有實學(xué),余叔巖無法動搖他的地位,最終自行組班。如果張伯駒真是黨同伐異,對王鳳卿也不應(yīng)該有較高的評價,可是恰恰相反。他說:“王鳳卿唱法用腦后音,為汪派傳人。《過昭關(guān)》《浣紗記》《魚腸劍》《取成都》《戰(zhàn)長沙》皆其拿手戲。飾《戰(zhàn)長沙》關(guān)羽,以胭脂揉臉,不打油紅臉,乃取法程大老板。鳳卿好書法,常臨劉石庵、翁同龢書。余曾贈以劉石庵書冊,彼甚寶之。”(《詩注》五九)沒有任何貶損。究其原因,還是王鳳卿的汪派古樸唱法和“神韻”是不大沖突的。
細(xì)讀《張伯駒集》,不難看到:張伯駒對于中國戲曲藝術(shù)具有廣博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理論,以此做出了很多獨(dú)到的評論。這些評論,也許不夠全面,那是因為他過分局限于“神韻”這唯一的標(biāo)準(zhǔn),而對其他美感有所忽視,這才會有對言菊朋和馬連良的過分貶損。但從深刻性來看,確實夠得上“第一義諦”。所以,《紅氍紀(jì)夢詩注》歷述京昆名角,簡直可以作為一部民國京劇小史來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