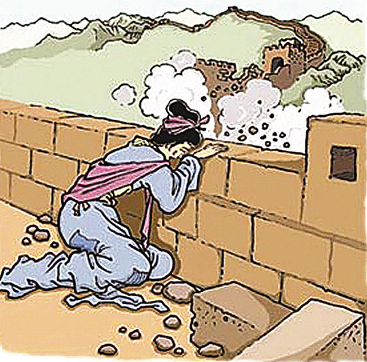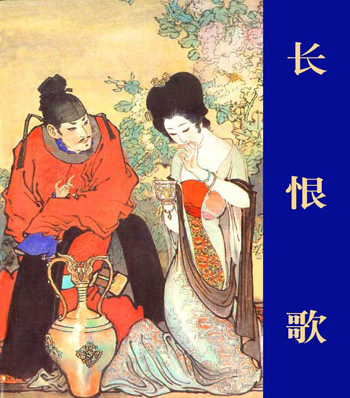精彩推薦
專題推薦
-
沒有記錄!
熱點排行
- 1、包公廟的由來
- 2、張字白的故事
- 3、交朋友的故事
- 4、小鐵錘相親的故事
- 5、摘心臺的故事
- 6、鬼谷子在王莊的傳奇故事
- 7、外甥不給姥爺穿孝的來歷
- 8、麥子只長一個穗的故事
盧太學的故事
2013/9/3 11:40:54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明朝嘉靖年間,浚縣出了一個大才子盧楠,人稱盧太學。盧太學家有良田千頃,巨資萬貫。光一個后花園就有幾十畝大。花園里種有奇花異草,一年里四季長青鮮花不斷。盧楠自幼廣涉詩、書、經、傳,才學過人,恃才傲世。在黃河以北是有名的才子。盧楠吟詩寫文出口成章,編成《蠛蠓集》廣為流傳。盧楠盧太學的名字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這一年新來浚縣上任的縣官人稱汪知縣。原是南方人,生在江南多才子的地方。汪知縣也很有才學,能詩會文,過目成誦。常邀風流雅士吟詩作賦歌唱升平。聽說本縣有個盧太學很有才氣。就想會一會盧太學。汪知縣是想約盧楠進縣衙,與一般文人學士聚會,共同歡娛。盧楠是想邀請汪知縣親臨府上,飲酒對弈,研討詩文,勝人一籌。盧太學就借迎春賞梅為由,向汪知縣發出請帖。汪知縣因公務纏身沒來。盧太學諒解了。三月,盧太學以賞牡丹花為由邀請汪知縣,又沒來。六月,以頌蓮高潔為由邀汪知縣又沒來。盧學士那種恃才傲物的勁頭就有點按捺不住啦。不過偏巧汪知縣差衙役送來個便條。說因公務纏身未能赴約的道歉話。并表示再次一定如期赴約。盧太學還算心情平靜一些。一直到九月,盧太學又以菊花盛會為名,邀請汪知縣赴宴,汪知縣也答應如期赴約。可到天晌午啦酒席筵宴都擺好了,咋等汪知縣就沒影兒。盧太學邀請的其它文人學士,同鄉豪紳一直等汪知縣不來,都餓得上街四散就餐啦。剩下盧太學光桿一人,一直等到日偏西,汪知縣還沒來。盧太學那股恃才傲物的勁頭兒,象大火一樣升騰起來啦。“狗屁!你汪汪狗說話算放屁。你汪汪狗只知道‘一年清知縣,十萬雪花銀’。只知道蠅營狗茍。你沒有梅花的孤高,你沒有牡丹的雍容,你沒有荷花的高潔,你沒有菊花的孤傲,你是個不懂文墨的白癡……”盧太學越想越氣,越說越急,抓住酒就喝,抓住肉就吃,象發瘋一樣大吃大喝,吆三喝六,猜枚行令,狂笑陣陣。這樣一來,鬧得桌上杯盤狼藉,地上酒瓶亂滾。盧太學喝得酩酊大醉,汗水淋漓,脫去布衫光著脊梁躺在后花園內涼亭里醉得不省人事。
汪知縣由于公務忙脫不開身。日頭偏西啦。忽然想起應盧太學邀請赴會的事。忙叫衙役準備轎樂執事前往。你看吧,縣太爺出動,三聲炮響,鼓樂齊鳴,大鑼大鐃哐哐鳴鑼開道,執事旗幟迎風招展,衙役轎夫前呼后擁耀武揚威,喧鬧非凡。大街小巷交相議論。“還是縣太爺有派頭。還是盧太學有威望,縣太爺還登府拜訪呢。”誰知到了太學府上,冷冷清清沒有一個人迎接。衙役通報進去。盧太學醉臥不起,嘴里還嘟嘟嚷嚷怨三罵四:“汪知縣,狗屁。狗都喂過啦,還來干什么!” 通報人也不敢直說。只含乎其詞說:“讓縣太爺客廳里面坐。”汪知縣到客廳一瞧,一片杯盤狼藉污穢不堪。汪知縣心里老大不高興。這簡直是對本縣的污辱。腳沒站定扭頭回衙。認為盧楠太狂傲啦。本縣屈駕親臨盧府,你盧楠連照面也不打。使本縣在光天化日之下丟人現眼。汪知縣越想越氣,越氣越急。“嗨!你小小盧楠,在我手心里,我有時間懲治你。”汪知縣從此把盧楠記在心里劃上一道。只是尋求下手的時機。
偏巧,第二年夏天暴雨大作。下得房倒屋塌。盧楠家的一道院墻倒塌,砸死了路過墻跟的一個長工。長工的老婆哭鬧連天,哭訴自己的親人死得可憐。消息傳到縣衙,長工的叔伯哥哥在縣衙當差。趕緊報給汪知縣。汪知縣說:“好,時機到啦。”這么長這么短給衙役一說,讓死者妻子遞上狀來。衙役下去又給長工的妻一說。第二天長工的妻子可把狀紙遞上來啦。狀告財主盧楠為富不仁謀害長工致死。汪知縣一看隨時傳令把盧楠收審人獄。盧楠膝下無子,只有三個女兒,女兒們到處求親托友到縣衙說合保釋。但都未能湊效。安葬長工一事花了不少銀錢,賄賂衙役使盧楠在獄中免受皮肉之苦又花不少銀錢。幾年時間盧楠在獄中,家資幾耗盡。盧太學的才氣詩文,沒有人再提啦。
年復一年,一直到汪知縣遷離浚縣。又一個新的縣官陸光祖到浚縣當縣令。新官上任三把火。要清除冤獄施展新政。審理到盧楠一案,提請盧楠申訴,又查訪盧楠鄉鄰。方知長工之死,確是墻塌誤傷砸死,并非盧楠所害。既然賠償長工損失,死已安葬,并撫恤了家小。盧楠已做到仁至義盡。盧案實屬冤案,至此查清無罪釋放。以示當今知縣明鏡高懸。盧太學對縣太爺陸光祖感激涕零,真是黎民父母官再生爹娘,永世不忘陸光祖縣太爺的恩德。
陸光祖在浚縣也有一番作為。吏治廉明清平康盛。也經常會聚文朋詩友吟詩賦詞。又在大伾山腰八丈佛前興建了“藏經閣”。從南京運來五千卷佛經存于樓上。倡導誦詩念經,樂善好施。不久,陸光祖就調遣到南京,任吏部尚書。盧太學又不惜巨資,前往南京看望陸尚書。受到陸光祖的接待。游遍了南京名勝,盧太學每到一處必題詩留壁。墨客文人見了無不贊譽嘆為觀上。陸光祖也贊嘆盧楠是個才子。在陸府的賓客中盧楠才氣橫溢,有才壓江南之美稱。陸光祖想給盧楠安排個職務。怎奈盧楠恃才傲物狂放大羈,大有李白在世之風度。不愿摧眉折腰事權貴。后來江南才子傳遞邀請。盧楠云游江南名山大川。在途中結識了一個盧山道人。盧楠又隨道人上盧山修煉,看破紅塵不入仕途,暮年歸鄉,不久去世。葬于大伾山北麓。
責任編輯:C006文章來源:印象河南網
相關信息
沒有記錄!
著名人物
沒有記錄!
精彩展示
沒有記錄!
評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