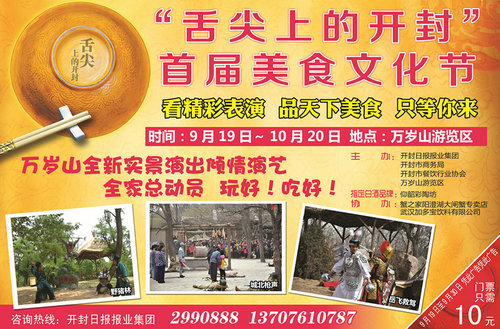-
沒有記錄!
劉子翬:汴京記憶訴興亡
2013/10/24 10:45:14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十多年前,我還在上大學時,每次路過礬樓前總要放慢腳步,街邊有一石碑,鐫刻有劉子翚的一首《汴京紀事》,回憶了年少時夜上礬樓的情景。這首絕句曾無數次引起我的遐想,那些風流歌舞、那些醇厚美酒、那些為賦新詞強說的愁以及欲說還休的青澀,一度占據我青春的思維。劉子翚的名字深深印入我的腦海,他一定很逍遙,他一定很放蕩不羈,他一定見證了汴京的繁華,他一定融入了礬樓的華美夜生活……劉子翚是誰?他的作品為何把東京夢華的記憶和懷念故都的情思以及寄托興亡的歷史融入其中?
一
劉子翚,字彥沖,號屏山,又號病翁,建州崇安人。學者稱其為“屏山先生”,朝廷贈以太師,追封齊國公,謚為“文靖”,《宋史》有其小傳。他見證了北宋末年的政治文化,經歷了大宋南遷的現實歷史。宋代政治昏庸,但是文化卻是走向了頂峰。社會的震蕩深深撞擊著士大夫階層的身心,在家國沉浮、社會變遷的大時代中,當年曾經集聚在北宋汴京的文人也隨王室南渡而心力交瘁。
劉子翚生于1101年,曾祖劉太素師從胡瑗。劉子翚與其兄劉子羽又曾受學于另一位大家胡安國。胡瑗和胡安國都是研究《春秋》的大家。“少負奇材,未冠游太學,聲譽出等夷”,不到弱冠之年的劉子翚就入太學學習了。當時,通過太學入選走上仕途基本上是一條比較穩妥的道路。在太學學習期間,他被“二程”理學深深折服。太學畢業后不久,金兵進犯,劉子翚毅然投筆從戎。他以父蔭授承務郎,被征用為真定府幕僚。1122年,他隨父親抗金,曾親眼見證了金兵入侵之后,百姓流離失所、家園荒廢、滿目瘡痍的慘狀。
1126年,宋金鏖戰進入生死階段,當時劉子翚的父兄都征戰在抗金的戰場上,親人安危、國家危亡、親情與民族情感交織在一起,25歲的劉子翚寫下了《靖康改元四十韻》,詩中充滿了對金國違反海上之盟的痛恨:“肉食開邊釁,天驕負漢恩。陰謀招叛將,喋血犯中原。”同時也流露出對北宋王朝割地求和、軟弱態度的不滿:“橫磨非嗜殺,下策且和番。割地煩專使,要盟脅至尊。”他渴求有志之士慷慨殺敵、報效祖國:“短衣求李廣,長嘯得劉琨。”但是,他有心殺敵卻無力回天。宋軍兵敗如山倒,金人很快就占領了北方廣袤土地,直逼汴京城下。1127年,汴京城陷。時年27歲的劉子翚,不僅經歷了國破之殤,更經歷了失去親人之痛。劉子翚的父親當時作為使者,肩負使命到金營議和,金人對他威逼利誘,遭到他的拒絕:“偷生以事二姓,死不為也。”他給劉子翚等人寫好遺書遣人送回,自己從容更衣沐浴,跪拜南方之后自縊身亡。對于父親的為國殉節,劉子翚十分痛恨金人,他的世界從此沒有了顏色,“丁憂”三年,他“哭墓三年”,憤而寫下了《汴京紀事》組詩20首。
二
《汴京紀事》組詩全部由七絕組成,每首集中寫一件事,以“靖康之變”為敘事中心,以都城汴京為寫作背景,前7首主要寫汴京淪陷后的現實,后13首側重寫汴京往日的繁華舊事。劉子翚用簡練、形象、生動的詩歌語言再現了這段令人痛心疾首的歷史畫面,描寫了汴京淪陷之后的慘狀,字字血、聲聲淚,抨擊了誤國的佞臣和金兵的南侵,表達了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深切憂慮。
劉子翚從小到大一直向往汴京,他的抱負與志向都在這座城市。汴京對于他而言,還是他父親、兄長用生命來守衛的固若金湯的都城,也是他少年時代交游、青年時代求學的繁華勝地。汴京記載了他最美的青春年華,留下了他最純真的情愫和成長足跡。離開后,再也沒有一座城,像汴京那樣叫人魂牽夢縈,叫人想起來就心疼,想起來就黯然神傷、淚流滿面,就算仰天長嘯后仍不解的依舊是濃濃的鄉愁。27年的山河歲月,27年的愛恨情仇都留給了繁華的汴京,都留給了遠去的中原故都。任憑鐵塔風鈴的搖曳,任憑相國霜鐘的凝重,任憑暗夜驚濤的汴水秋聲,任憑如水樣冷冷月光照耀的州橋,劉子翚以一個人的視野,以一個文人的家國情懷書寫了時代的最強音。
汴京是劉子翚心中的痛,從繁榮鼎盛的東京夢華到城春草木深的國破家散,汴京無疑存在劉子翚心中最為軟弱的地方。那時的汴京是“宮娃控馬紫茸袍,笑捻金丸彈翠毛”,如今卻是“鳳輦北游今未返,蓬蓬艮岳內中高”。艮岳曾是北宋豪華的園林,無論當年的皇帝如何奢靡,但是那些城市的地標依舊樹立在人們心中,皇帝被掠到北國了,富麗堂皇的艮岳已經荒蕪一片了。萬千感嘆,凝于一言。“萬炬銀花錦繡圍,景龍門外軟紅飛。”景龍門為汴京著名的城門,每年元宵佳節,宋徽宗就在這里游賞玩樂。景龍門的花燈異常華美,都城市民熙熙攘攘游賞其間,天子與民同樂,日夜沉浸在“錦繡圍”、“軟紅飛”的富貴之鄉,縱酒酣歌,消磨歲月。如今再回首,依舊的當年明月夜,卻不見當年舊時人,昔日繁華已經成為過眼云煙。劉子翚刻意將一段美好的汴京歲月感悟成詩句,讓文字的溫度傳導給我們當年的記憶和往事。
“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時動帝王。”名妓李師師,因與宋徽宗有密切的關系,傳說與水泊梁山的宋江也有關系,于是便成了宣和年間一個人人皆知的風流人物。正史不屑于提到她的名字,但是劉子翚卻在《汴京紀事》組詩中專門寫到了她。李師師色藝雙全,貌若天仙,琴棋書畫無所不通。文人的筆記小說中記載著她與不少文人的交往,張端義的《貴耳錄》、張邦基的《墨莊漫錄》,都記載了她與大詞人周邦彥、晁沖之的來往和詩詞酬答。宋徽宗聽說她的名聲之后,竟微服尋至金線巷,成為座上客。“靖康之變”后,“師師垂老過湖湘”,依舊風華絕代,依舊風韻猶存,縷金檀板與之相比都無顏色。參閱歷代筆記小說,不少說法與劉子翚的記載十分吻合,如《青泥蓮花記》云:“靖康之亂,師師南徙,有人遇之湖湘間,衰老憔悴,無復向時風態。”張邦基《墨莊漫錄》書中稱李師師被籍沒家產以后,流落于江浙一帶,當地的士大夫猶邀請她歌唱,但李師師已“憔悴無復向來之態矣”。 劉子翚的詩歌借歌妓李師師前后遭遇的變化,寄托家國興亡之感慨。
縱觀劉子翚的《汴京紀事》組詩,既有“亡國之音哀以思”之沉痛,又有令乾坤倒轉、江河斷流、勇士拔劍而起的昂揚。這一組詩被當代史學家喻為“南宋流亡三部曲”。
三
劉子翚為父守孝3年之后,在1130年到興化府走馬上任,被任命為“興化軍通判”。當時時局紛亂,外憂金兵,內患戰亂。劉子翚在任3年,最主要的政績是“抗寇”,與盜寇較量了3年。他總結經驗教訓,認為對百姓輕徭薄賦、官員恪守職責才可以國泰民安。
任期一滿,劉子翚就辭歸。因為在父親的喪禮中他操心過度,影響了身心健康。朱熹說他“至是以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因為政績突出,朝廷本想叫他繼續連任,他卻請求任主管武夷山沖佑觀的一個閑官,并且連任四任。正是這樣,在確保衣食無憂的前提下,劉子才有時間摒棄世俗雜務、潛心學問、專事講學,一時間前來學習者很多。《宋史》載:“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
因是閑職,沒有了考核以及政績的壓力,他便搬到故里居住。獨特的家世,造就了劉子翚深厚的文化修養,也形成了劉子翚與眾不同的理學思想。在歸隱期間,劉子翚與胡憲、劉勉之多有交往,人稱“武夷三先生”。他們每次相見都是談論學問。
后來,劉子翚將劉氏家塾改為“屏山書院”。朱熹的父親朱松與劉子翚、胡憲、劉勉之交情很深。1143年,朱松托孤于三人,劉子翚作為朱松臨終前主要的托孤者之一,他盡心盡責地教誨朱熹。那一年,失去父親的朱熹只有14歲,他得到了“武夷三先生”的照料。劉子翚先生格外喜歡朱熹,他為朱熹取表字“元晦”,給他講解圣學。在朱熹的成長和思想體系的形成中,劉子翚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在理學方面,劉子翚直接用“二程”及其門人的著作,并以《圣傳論》作為教學大綱,向朱熹灌輸其糅合儒佛老三道的理學思想。劉子翚的儒家教育、反和主戰的政治態度和獨尊“二程”的理學思想深深影響著朱熹特殊的道學性格,這些為朱熹后來建立集大成的理學體系準備了豐厚的思想土壤。朱熹在《屏山集跋》中評價說:“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于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心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
1147年,劉子翚一次偶染小恙,他預感不祥,立即拜謁家廟,泣別母親,與親朋好友訣別。把家事托付與侄子之后,他選好了墳地,安排好了親戚中孤寡貧弱沒有正常職業之人的生計。劉子翚寫了數百言教誨學子要增強自身修養、追求大道的遺貼,兩天后就去世了。在劉子翚最后臥病不起的日子里,朱熹晝夜待在他的床榻邊端茶喂藥。后來,朱熹在《跋家藏劉病翁遺貼》中寫道:“先生所以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為具道平生問學次第,傾倒亡余。”
作為朱熹的老師,劉子翚不但是知名的理學大師,而且是一位才情橫溢的詩人。當代學者錢鐘書先生稱朱熹是“道學家中間的大詩人”,稱劉子翚是“詩人里的一位道學家”。 錢鐘書在《宋詩選注》中寫道:“假如一位道學家的詩集里,‘講義語錄’的比例還不大,肯容許些‘閑言語’,他就算得道學家中間的大詩人,例如朱熹。劉子翚卻是詩人里的一位道學家,并非只在道學家里充個詩人。他沾染‘講義語錄’的習氣最少,就是講心理學倫理學的時候,也能夠用鮮明的比喻,使抽象的東西有了形象。”
四
劉子翚一生著作甚多,《屏山集》二十卷,其中僅詩歌近十卷715首。劉子翚去世后,他的孩子把劉子翚的著作整理結集,可惜沒有得以刊行。后來,經朱熹整理之后,《屏山集》才得以刊刻成集,流傳于世。劉子翚詩歌造詣頗高,風格比較清爽明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古詩風格高秀,不襲陳因”。尤其是五言古詩,“幽淡卓練”。劉子翚從不同角度反映了世事巨變、家國滄桑的現實,并寄托了深沉的感情。劉克莊稱其詩歌“敘當時事,忠憤悲壯”,足見其愛國之情的忠貞赤誠、深沉厚重。其《汴京紀事》詩20首,堪稱一代興亡史的詩史,在當時廣為流傳。在南宋理宗寶慶年間,有人將劉子翚《汴京紀事》之七中的“夜月池臺王傅宅,春風楊柳太師橋”一句,改為“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風楊柳相公橋”,以譏諷當時奸臣史彌遠,使陳起、劉克莊、敖陶孫、曾極、趙汝迕五人都因此受到牽連和嚴懲,在中國文學史上形成了一場典型、罕見的“詩禍”。可見,劉子翚的詩歌在南宋是很有影響力的。
劉子翚的詩歌特別是《汴京紀事》組詩,展現了汴京淪陷前后眾多歷史事件的風貌,歷來為人矚目。清人翁方綱推崇說:“劉屏山《汴京紀事》諸作,精妙非常。此與鄧拼櫚(鄧肅)《花石綱詩》,皆有關一代事跡,非僅嘲評花月之作也。宋人七絕,自以此種為精詣。”800多年來,他的《汴京紀事》一直廣為流傳。多年之后,我每次閱讀《汴京紀事》組詩之時,常被他追憶的目光引領至歷史上的北宋都城,那是一幅汴京文化的都市長卷,是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圖》,也是歷史長河中兩宋交叉之間的傳奇。(原標題:劉子翬:汴京記憶訴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