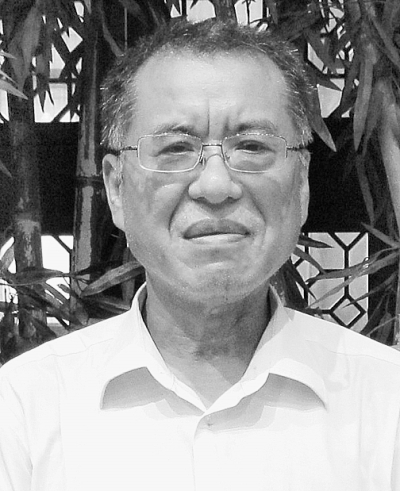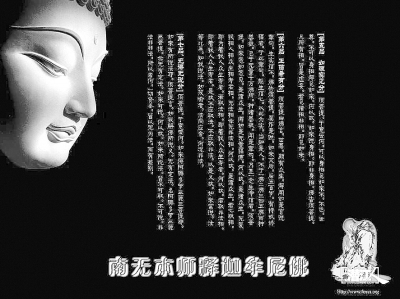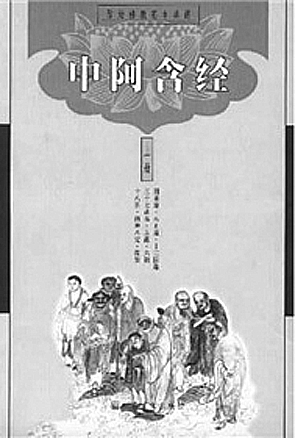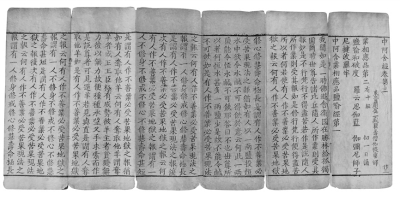主講人:姚衛(wèi)群
時間:2014年3月
地點:北京龍泉寺
我是第一次來龍泉寺,早就有期待來看看北方這家著名寺院,期待有這樣一個機緣與大家交流。
佛教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表現(xiàn)在其思維方式上,而這種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說是一種否定形態(tài)的思維方法,也可以稱之為“遮詮法”。“遮”即否定,“詮”即說明。以此方法來展示或認識事物。
“遮詮法”在佛典中的主要展現(xiàn)
遮詮法所強調(diào)的一種基本思想是:對于事物的本來面目或最高實在不能采用正面表述的方式來展示,而是應采用不斷否定各種有關(guān)名相概念實在性的方式來顯明,即要在否定中體悟事物的真理。這種思維方法在佛教中使用較多,而使用最多或最受重視的是在佛教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形態(tài)——大乘佛教中,特別是在大乘佛教的般若中觀類文獻中有不少典型的表述。
大乘佛典中較早出現(xiàn)的是般若類經(jīng)典。此類經(jīng)典中十分著名的是《金剛經(jīng)》。該經(jīng)中說:“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如來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這里說的“般若波羅蜜”指佛教以最高智慧來度眾生出苦海;“三十二相”是佛教中描述佛及轉(zhuǎn)輪圣王身所具足的三十二種微妙相;“三千大千世界”是佛教關(guān)于宇宙形態(tài)的一種說法;“法相”指事物的相狀或本來面目。在《金剛經(jīng)》看來,佛在解釋這些事物時,所使用的言語本身是不能執(zhí)著的。只有體悟到了這些名相概念不能完全反映事物的本質(zhì),才能明了有關(guān)事物究竟是什么。
《金剛經(jīng)》不長,里面卻有大量上述這種“說……,即非……,是名……”的句式,可見此句式的重要性。這種句式實際上就是一種典型的遮詮法的句式。因為“說……”實際就是使用名相概念的一般表述,而這種表述在大乘佛教思想家看來是不可能展示事物本性的,因而說“即非……”說“即非……”就是一種否定或“遮”,只有這樣才能把握事物的本來面目或?qū)嵪啵床拍苷f“是名……”。這也就是通過不斷地否定達到對事物本來面目的真實展示。
屬般若類經(jīng)典的著名《心經(jīng)》中也說:“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凈,不增,不減。”可以看到,般若類經(jīng)中有大量以“不”或“非”或“無”開頭的文句。經(jīng)的作者是要顯示,只有用這一系列的“不”或“非”或“無”,才能獲得最高的智慧,才能真正認識事物的本來面目。
大乘佛教中除了般若類經(jīng)中有這種表述外,其他一些佛典中也有類似的表述。如《維摩詰經(jīng)》卷上中說:“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有說,離覺觀故”;“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在此經(jīng)看來,事物的本質(zhì)或本來面目用一般言語概念是不能真正認知的。那么,是不是就不能認識了?也不是!只是要采取特殊的認識方法,要在不斷否定描述有關(guān)事物的名相概念中,才能體悟出來。
《維摩詰經(jīng)》中的遮詮意識還體現(xiàn)在解釋“入不二法門”的過程中。如該經(jīng)卷中記述說,維摩詰居士向文殊菩薩等三十二位佛教圣者問什么是“入不二法門”。諸菩薩等圣者作了多種解釋,有的說“生滅不二”,有的說“垢凈不二”,有的說“生死涅槃不二”。文殊菩薩認為:“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為入不二法門。”但這些回答在維摩詰居士看來都不準確。當文殊菩薩反問維摩詰居士“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居士僅僅以“默然”相對。文殊菩薩由此領(lǐng)悟“入不二法門”的真正途徑,他說:“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這里實際也是通過對“入不二法門”各種解釋的否定來說明為達到一種最高境界的正面表述的局限性,說明使用種種名相概念不能絕對地真實反映事物的本來面目。該經(jīng)在這里實際是強調(diào)使用遮詮手法的重要性。它展示的是:只要是正面的表述,都要否定。“默然”則是這種否定的最高形式。因為這些表述都必不可免地要使用名相概念,而名相概念是有局限性的。
早期大乘經(jīng)出現(xiàn)后,許多人對這類經(jīng)典進行解釋,出現(xiàn)了大乘的論。這些論的作者,有不少是解釋大乘經(jīng)較多或較好的佛教論師。這些人形成了佛教中的一個重要派別,即中觀派。中觀派的主要論典中也廣泛運用了遮詮法。如此派最主要的著作《中論》中就大量使用了這種手法。《中論》卷第一中說:“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這里所提出的“八不”實際上就是一種遮詮的表述。通過對生、滅、常、斷、一、異、來、出這些概念的否定,中觀派表明了處于因緣變化中的事物的實相。
中觀派明確認為:事物的本來面目用一般的言語概念是不可說的。《中論》卷第四中說:“諸法不可得,滅一切戲論。無人亦無處,佛亦無所說。”這里表明的是:連如來所說所言也都是“無”,是不能執(zhí)著的,更不要說其他的言語概念了。從絕對真理的標準來看,“佛亦無所說”。因而,只有在“遮”了之后,才有可能悟出諸法的實相,才能真正達到涅槃。
遮詮的方法不僅在般若中觀佛典中有突出的使用,而且在另一大乘佛教的主要派別瑜伽行派中也有不少使用。如瑜伽行派的主要文獻《成唯識論》卷第七中說:“于唯識應深信受:我法非有,空識非無。離有離無,故契中道。……故說一切法,非空非不空。”這里說的中道實際也包含遮詮的成分,即此派強調(diào)非有非無、非空非不空。認為我和法是“非有”的,也就是性空的,而空識是“非無”的。非無似乎是肯定了識,但識之前又有一個“空”字,因而識在實質(zhì)上也是“空”的,也要“遮”。只有都“遮”了,方可達到瑜伽行派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早期和部派佛典中的相關(guān)內(nèi)容
遮詮法雖然在大乘佛典,特別是在般若中觀的佛典中最為流行,但在印度佛教發(fā)展的早期階段和小乘部派階段的文獻中也有這類成分,只是使用的頻率或重視的程度不如大乘般若中觀佛典那樣突出。
佛陀(釋迦牟尼)在世時,印度有許多“外道”(佛教外派別)中的人物,他們常與佛教進行思想交鋒。也有不少人來向佛陀請教,或討論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一些人曾向佛陀提出一些涉及世界及人生的重要哲理性問題。而佛陀對這些問題一般采用一種“不為記說”的態(tài)度,即所謂“無記”(不明確給出答案或判斷)。《雜阿含經(jīng)》卷第三十四中記述了向佛陀提出的十四個問題:“世間常、……世間無常、常無常、非常非無常、有邊、無邊、邊無邊、非邊非無邊、命即是身、命異身異、如來有后死、無后死、有無后死、非有非無后死?”佛陀對這些問題所作出的反應是“默然不答”,或“一切不說”。后來一般稱佛陀對這十四個問題所采取的態(tài)度為“十四無記”,就是對這些問題不回答或不明確表明態(tài)度。佛陀認為:如果作出明確的答復,無論如何也會產(chǎn)生錯誤。這里實際上就包含著一種遮詮的意識。在佛陀看來,無論說世界是常恒的還是不常恒的等,都有局限性,都不能反映事物的本來面目。要想避免產(chǎn)生錯誤,就只能采用“無記”的態(tài)度。即佛陀認為,對這些問題作出明確的回答會產(chǎn)生顛倒見,會受到束縛,產(chǎn)生種種痛苦。只有采取“無記”或“默然不答”的態(tài)度,才能擺脫愚癡,擺脫痛苦。佛陀所要強調(diào)的是:不能進行各種明確的肯定,而不斷的“無記”實際就是不斷的“遮”,通過不斷的“遮”來體悟世界和人生的真理。
佛教中的“中道”思想與“遮詮”意識是密切相關(guān)的。從早期佛教開始,佛教就對一些對立的做法或概念持否定態(tài)度,表露出一種不落兩邊或不走極端的思想觀念。例如,佛陀在世時,對于極端的享受和極端的苦行都是反對的。《中阿含經(jīng)》卷第五十六中說:“有二邊行,諸為道者所不當學:一曰著欲樂賤業(yè),凡人所行;二曰自煩自苦,非賢圣求法,無義相應。五比丘,舍此二邊,有取中道。”這段記述主要是表明了早期佛教的“中道”思想。而這實際上也顯示了佛教中最初的“遮詮”觀念。在佛教產(chǎn)生時,不少人在行為上往往有兩種態(tài)度或傾向:一種是追求極端化的享樂的傾向,另一種是追求極端化的苦行的傾向。前者的主要代表是古印度的一個重要哲學派別順世論,后者的主要代表是印度重要宗教派別耆那教。順世論強調(diào)人在世時應及時行樂,也就是上文中說的“著欲樂賤業(yè)”,屬于極端化的享樂的傾向。耆那教強調(diào)嚴厲的苦行,也就是上文中說的“自煩自苦”,屬于極端化的苦行的傾向。在佛教看來,這是兩個極端,都不能達到覺悟或涅槃。必須“舍此二邊”,才能“有取中道”。這種中道的方法,具體來說就表現(xiàn)為對極端的苦行和極端的享樂這“二邊”都加以否定,因而有一定的“遮”的意識。在佛教看來,要不斷遮除這類極端,才能實現(xiàn)“中道”,達到佛教的最高境界。
部派佛教的一些文獻中也有遮詮方面的表述。例如,部派佛教中的重要派別說一切有部的主要著作《大毗婆沙論》卷第二百中說:“諸外道諸惡見趣無不皆入斷常品中。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對治彼故,宣說中道,謂色心等非斷非常。”這里說到“斷”與“常”這樣對立的概念,認為外道所持的各種錯誤觀點入“斷”,入“常”。而佛教要追求的是“中道”。這里說的“中道”實際上也就是采用遮詮的思想方法,談到物質(zhì)現(xiàn)象(色)和精神現(xiàn)象(心)等時既不能說是“斷”,也不能說是“常”,而只能說“非斷非常”。這樣才能認識事物的本質(zhì)。
部派佛教中實際也有認為某一特定的觀念或概念有局限性的思想,要求離開各種極端。他們意識到,事物或有關(guān)的概念往往有對立的兩邊或兩端。這兩邊或兩端在部派佛教看來都是要否定的。《雜阿毗曇心論》卷第七中說:“圣道離二邊,名為中道。”這里講的“離二邊”或“中道”其實都要采用“遮詮”的方法才能實現(xiàn)。即在部派佛教看來,只有在否定各種對立的偏見過程中才能把握符合佛教中道的正法。
應當說,佛教的遮詮法在早期佛教和部派佛教時期就有一些這方面的思想傾向,但還不十分突出。而在大乘佛教時期,這種思維方式則得到極大地發(fā)展。
遮詮法在古印度的理論源頭
遮詮法雖然在大乘佛教中廣泛使用,并且在早期佛教中就有一些有關(guān)成分,在部派佛教中也有一些表述,但這種思維方法的理論源頭,還是要在佛教產(chǎn)生前的印度古代圣典中去尋找。具體來說,在現(xiàn)存古印度最早的宗教歷史文獻吠陀和奧義書中,就已有這種遮詮法的使用。佛教理論體系中使用遮詮法,應當說是借鑒吸收了吠陀和奧義書中就存在的這種方式。
吠陀是一大批印度遠古時期出現(xiàn)的宗教文獻,其最初的形態(tài)主要是一些印度先民創(chuàng)作的口頭贊歌。主要的吠陀文獻大致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500年之間形成,后來被人們整理成書面文字,流傳至今,是我們了解古代印度早期文化的重要資料。
吠陀中主要是宗教的內(nèi)容,但也有一些哲學性較突出的贊歌。在這些文獻中,已可看出古代印度人對一些對立的概念或觀念同時否定的做法。如《梨俱吠陀》10,129,1-7中說:“那時(泰初),既沒有無,也沒有有。”“既沒有死,也沒有不死。”“有的聯(lián)系在無中被發(fā)現(xiàn)。”“這造作是從哪里出現(xiàn)的?或是他造的,或不是。他是這世界在最高天上的監(jiān)視者,僅他知道,或他也不知道。”這里,作者同時舉出了幾組相互對立的概念——有與無、死與不死、是與不是、知與不知。對這些概念,贊歌的作者顯然已經(jīng)注意到了其中存在的對立。作者在論述中有意識地將這些對立的概念聯(lián)系起來。在其表述中,并不因為否定了一個概念就肯定與此概念完全對立的概念,而是對完全相反的概念同時加以否定。這種做法中顯示了作者的一種意圖,即要通過否定的手法來表明事物的不可言說的或不同一般的狀態(tài)。在這里,已多少可以看出后來在佛教中流行的遮詮的表述方式。但這類成分在吠陀贊歌中還不普遍,而且作者也沒有將這些表述集中安排在某一段落中展示出來。因而,早期吠陀中的這些成分作為一種表述手法還不十分突出或清晰,只能說是印度思想史上遮詮法的早期萌芽形態(tài)。
奧義書從廣義上說也是吠陀文獻的一部分,是吠陀中較晚出現(xiàn)的一批文獻。但從狹義上說,它與早期吠陀贊歌不同。印度古代最初的重要哲學思想產(chǎn)生于奧義書中。較早出現(xiàn)的奧義書在公元前800年左右,還有一些奧義書的形成時間接近于佛教產(chǎn)生的時期,也有奧義書在佛教產(chǎn)生之后形成。奧義書中的一些思想對佛教理論產(chǎn)生了某種影響。遮詮法在奧義書中使用較多,是當時的印度思想家有意識地使用的一種認識方法。
在奧義書中,遮詮法主要出現(xiàn)在哲人們對最高實體“梵”或“我”的表述中。奧義書中的一些思想家認為,世間一切事物的根本或本體是“梵”(大我),而生命現(xiàn)象中的主體是“我”(小我)。“梵”與“我”在本質(zhì)上又是相同的,主張“梵我同一”,即認為宇宙的本體與人生命現(xiàn)象中的主體是同一的或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真正的宇宙本體和人生命現(xiàn)象中的主體只有一個。多數(shù)奧義書思想家在表述“梵”或“我”時采用了遮詮法。例如,較早出現(xiàn)的《廣林奧義書》和《由誰奧義書》中就使用了遮詮的手法來表述作為最高實在的梵或我。
《廣林奧義書》3,8,8中認為,梵是“不粗、不細,不短,不長,……非風,非空……無內(nèi),無外。”顯然,在作者看來,對梵的各種正面表述都不能真正準確地說明它,在各種概念或修飾性的言語前,都要加上“不”、“非”或“無”等否定性的詞,論及梵時只能采取這樣的方式。
奧義書哲人對這一遮詮之法有明確的體悟和相應的歸納,如《廣林奧義書》4,5,15中說:“我(梵)應被描述為‘不是這個,不是這個’。我不被領(lǐng)悟,因為它不能被領(lǐng)悟。”文中說的“不是這個,不是這個”就是不斷地否定。在作者看來,通過正面的陳述,“梵”或“我”是不能被領(lǐng)悟的,只有在不斷的否定中,才能使人體悟出“梵”或“我”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說,最高實體或事物的最高境界只有通過遮詮才能達到。
《由誰奧義書》中也明確認為,“梵”或“我”只能以一種遮詮的方式來展示,而不能正面描述。該奧義書2,3中說:“那些說他們理解了梵或我的人并沒有理解它;那些說他們沒有理解梵或我的人卻理解了它。”這里說“理解了”的人實際是采用了一種正面的表詮,而說“沒有理解”的人則采用了一種遮詮。在奧義書哲人看來,只有遮詮才能真正體悟“梵”或“我”的本質(zhì)。
從吠陀和奧義書的這方面論述中可以看出,早在佛教產(chǎn)生之前,古印度哲人就已大量使用遮詮法。吠陀中已有了遮詮法的一些思想萌芽,它對奧義書中形成明確的遮詮思維方式有一定影響。《廣林奧義書》和《由誰奧義書》等較早的奧義書中明確的遮詮法則對佛教會有直接的影響。奧義書中的主流思想是婆羅門教的觀念,遮詮法主要是在婆羅門教思想家中較早使用的。在古印度,婆羅門教產(chǎn)生在前,佛教產(chǎn)生在后。因而,佛教中的遮詮法主要是受奧義書等婆羅門教圣典中的相關(guān)內(nèi)容影響后產(chǎn)生的。婆羅門教哲學中的遮詮法更多地為大乘佛教思想家所借鑒或吸收。吠陀奧義書等古印度圣典中的一些內(nèi)容是般若中觀佛典中使用的遮詮法的理論源頭。
佛教與古印度婆羅門教中遮詮法的淵源
佛教中的遮詮法與古印度婆羅門教圣典中的遮詮法有重要的淵源關(guān)系,有相同處,也有差別點。
相同處在于:兩教遮詮法所“遮”的都是描述事物的各種概念、名相、范疇,都認為要通過遮除這些概念等的局限性來使人體悟事物的本來面目。
差別點在于:婆羅門教圣典“遮”后要顯示的主要是一個實體或本體。而佛教(特別是大乘佛教)中“遮”后所要顯示的主要是事物的實相。佛教否定有一個不變的實體或本體。
盡管佛教中所使用的遮詮法從產(chǎn)生時間上看要晚于婆羅門教圣典,但在古代印度,以及在中國等佛教傳播的國家,其影響還是很大的。這一方法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主要表現(xiàn)在:
遮詮法的使用者看到了人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使用的概念、名相、范疇等在表明事物時所具有的局限性,實際上也就是看到了人的認識在把握事物本質(zhì)時所具有的局限性。佛教(特別是大乘佛教)的理論向人們展示的是:人在認識事物時無論使用任何言語或名相都會有偏差,正面的直接陳述或詮表最多只能接近事物的本來面目。這種面目絕不可能通過人們附加給事物的各種屬性或性質(zhì)而真正展示出來,人們只能在不斷地否定事物具有種種具體屬性或性質(zhì)的過程中來體悟事物。對這些屬性或性質(zhì)的不斷否定實際也就是人們不斷消除自己認識中不正確成分的過程,這將使認識者逐步接近事物的本來面目。
遮詮法的使用者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事物之中存在著對立面的相互聯(lián)系。他們意識到:否定事物具有一個屬性并不意味著肯定與之對立的屬性,而是應對兩個對立或相反的屬性都加以否定,在這種否定中來展示事物。這種“遮”的過程在客觀上起到了一種糾偏的作用,借助一系列的“遮”,排除各種極端成分,擺脫錯誤的觀念,使人們的認識保持客觀。這是古代印度人追求或探索真理時所采用的一種基本手法。
佛教中廣泛使用的遮詮法,在印度思想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這種方法的理論源頭則在婆羅門教奉為圣典的吠陀奧義書中。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說明:在人類歷史上,不同的甚至一些對立的哲學或宗教派別往往不是處處相互排斥的。在很多場合,他們是相互吸收,相互借鑒的。這種吸收或借鑒有時是明顯的,有時是不明顯的。但這種吸收或借鑒的事實則實際存在。通過歷史上不同哲學或宗教派別的思想交鋒和相互吸收借鑒,人類文明得以健康發(fā)展。(宋曉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