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ö(d©Īng)ėą╦∙│╔ ▒žėą
╚²į┬Ą─Ļ¢(y©óng)╣Ōį┌│Ū╩ąĄ─├┐éĆ(g©©)ĮŪ┬õ└’’@Ą├Ė±═ŌĄ─║═ņŃīÄ?k©┤)oŻ¼╠ż╚ļ..[įö╝Ü(x©¼)]
┴x┼dÅłĄ┌░╦┤·
Åłųą║═Ż¼─ąŻ¼1967─Ļ╔·Ż¼║ė─Ž╩Ī░▓Ļ¢(y©óng)╩ą╗¼┐hĄ└┐┌µé(zh©©n)╚╦Ż¼Ą└┐┌¤²..[įö╝Ü(x©¼)]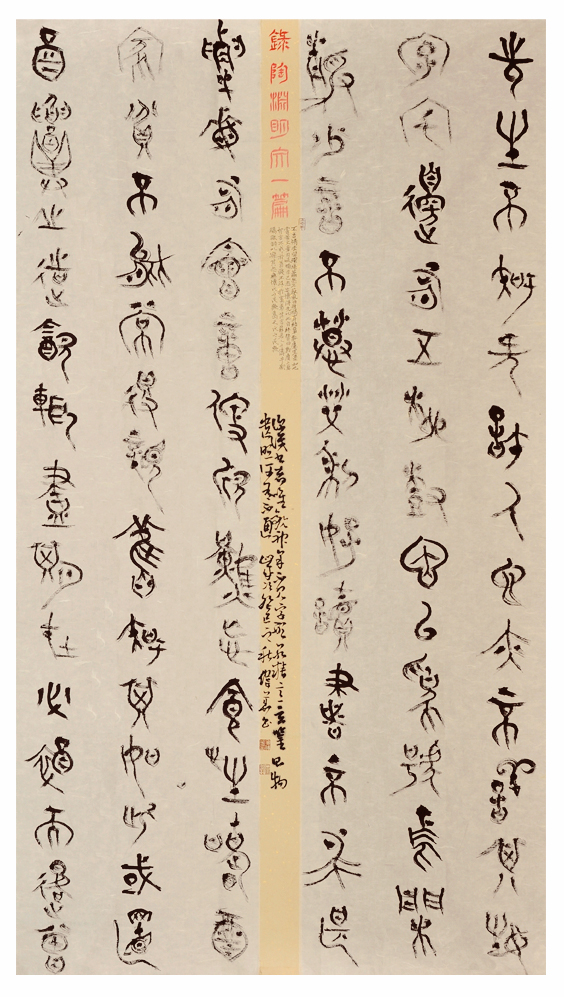
įóŪ╔ė┌ūŠŻ¼ņ`äė(d©░ng)
ĖĄéź╚AūŁ┐╠ū„ŲĘĖĄéź╚AūŁ┐╠ū„ŲĘĖĄéź╚A│÷╔·ė┌ųąų▌╣┼│Ū£Ņ..[įö╝Ü(x©¼)]
- 1Īó┴óČ¼Ī¬╚f(w©żn)╬’╩š▓ž ęÄ(gu©®)▒▄║«Č¼
- 2Īóųąć°(gu©«)┬╔ĤųŲČ╚Ą─Üv╩Ęč▌ūā
- 3ĪóąĪ║«┤¾║« šl(shu©¬)╩Ū╠ņŽ┬Ą┌ę╗║«Ż┐
- 4Īó░┘─ĻŪ░č¾╚╦│įČ╣Ė»ū╠╬Č┘É─╠└ęŻ║╩«Ęų╬Č├└
- 5Īó│■═■═§┘n┴dį┬─Ė┼«ūĪš┬╚A┼_(t©ói)Ż┐║¾Ü¦ė┌Ūž▄Ŗ
- 6Īó╔Ņ╔Į│÷ŲµĖ∙ ╠ņ╚╗╚źĄ±’ŚĪ¬Ī¬ėøĖ∙╦ć├└ąg(sh©┤)
- 7Īó╠Ų┤·┘FūÕ╚ń║╬▀^(gu©░)Č¼Ż┐ė├ōv╦ķĄ─╗©ĮĘ║═─Ó═┐
- 8ĪóÅ─ĪČ┐╣┘┴ėóą█Ų▌└^╣ŌĪĘšf(shu©Ł)ĄĮÜv╩Ę╔ŽĄ─Ų▌└^
-
ø](m©”i)ėąėøõø!
- 1Īóųąć°(gu©«)┬╔ĤųŲČ╚Ą─Üv╩Ęč▌ūā
- 2Īó└ė│÷Š½▓╩╚╦╔·Ī¬Ī¬ėø├±ķg└ė«ŗ(hu©ż)╦ćąg(sh©┤)┤¾Ä¤ČĪ
- 3Īóč®┬õ╝tĮz┤SŻ¼ŽŃäė(d©░ng)Ńy║┴«TĪ¬Ī¬╦╬┤·³c(di©Żn)▓Ķ╣ż
- 4Īó┴óČ¼Ī¬╚f(w©żn)╬’╩š▓ž ęÄ(gu©®)▒▄║«Č¼
- 5Īó┴x┼dÅłĄ┌░╦┤·é„╚╦Åłųą║═
- 6ĪóąĪ║«┤¾║« šl(shu©¬)╩Ū╠ņŽ┬Ą┌ę╗║«Ż┐
- 7Īó░┘─ĻŪ░č¾╚╦│įČ╣Ė»ū╠╬Č┘É─╠└ęŻ║╩«Ęų╬Č├└
- 8Īó│■═■═§┘n┴dį┬─Ė┼«ūĪš┬╚A┼_(t©ói)Ż┐║¾Ü¦ė┌Ūž▄Ŗ
┬įšf(shu©Ł)ĪČšōšZ(y©│)ĪĘĄ─╗∙▒Š╠žš„Ī¬Ī¬ęįĪ░įūėĶĢāīŗĪ▒š┬×ķ└²
2014/9/3 17:49:51 ³c(di©Żn)ō¶öĄ(sh©┤)Ż║ ĪŠūų¾wŻ║┤¾ ųą ąĪĪ┐
▒Š╬─Ą─ų„ų╝Ż¼į┌ė┌ęįĪČ╣½ę▒ķL(zh©Żng)Ų¬ĪĘĄ─“įūėĶĢāīŗ”š┬×ķ└²Ż¼ī”(du©¼)ĪČšōšZ(y©│)ĪĘĄ─╗∙▒Š╠žš„Ż¼ę▓Š═╩Ū╚Õ╝ęĄ─╗∙▒Š╠žš„Ż¼ū„ę╗║å(ji©Żn)ꬥ─ĻU├„ĪŻ▀@ī”(du©¼)īW(xu©”)║├╚Õ╝ęŻ¼īW(xu©”)║├ĪČšōšZ(y©│)ĪĘŻ¼¤o(w©▓)ę╔╩Ūėąųžę¬Ä═ų·Ą─ĪŻ
įŁ╬─Ż║įūėĶĢāīŗĪŻūėį╗Ż║“ąÓ─Š▓╗┐╔Ą±ę▓Ż¼╝S═┴ų«ē”▓╗┐╔¢gę▓Ż╗ė┌ėĶ┼c║╬šDŻ┐”ūėį╗Ż║“╩╝╬ßė┌╚╦ę▓Ż¼┬Ā(t©®ng)ŲõčįČ°ą┼ŲõąąŻ╗Į±╬ßė┌╚╦ę▓Ż¼┬Ā(t©®ng)ŲõčįČ°ė^ŲõąąĪŻė┌ėĶ┼cĖ─╩ŪĪŻ”
Į±ūg╬─Ż║įū╬ę░ū╠ņ╦»ėX(ju©”)ĪŻ┐ūūėšf(shu©Ł)Ż║“Ė»ĀĆĄ──ŠŅ^¤o(w©▓)Ę©Ą±┐╠Ż¼¾a┼KĄ─═┴ēŠ│╔Ą─ē”▒┌¤o(w©▓)Ę©Ę█╦óĪŻī”(du©¼)ė┌įū╬ę╬ę▀Ć─▄ž¤(z©”)éõ╩▓├┤─žŻ┐”┐ūūėėųšf(shu©Ł)Ż║“ęįŪ░╬ęī”(du©¼)ė┌╚╦Ż¼┬Ā(t©®ng)╦¹į§├┤šf(shu©Ł)Ż¼Š═ą┼╦¹į§├┤ū÷ĪŻ¼F(xi©żn)į┌╬ęī”(du©¼)ė┌╚╦Ż¼┬Ā(t©®ng)╦¹į§├┤šf(shu©Ł)Ż¼▀Ćę¬┐┤╦¹į§├┤ū÷ĪŻ╬ę╩ŪÅ─įū╬ęĄ─ąą×ķĖ─š²┴╦▀@éĆ(g©©)Õe(cu©░)š`ĪŻ”
┐ūūėė├╚ń┤╦ć└(y©ón)ģ¢Ą─ĘĮ╩Įž¤(z©”)éõįū╬ęŻ¼ŲõšµīŹ(sh©¬)─┐Ą─╩Ū×ķ┴╦Ė³║├Ąžī”(du©¼)░YŽ┬╦ÄĪŻ╩ņūxĪČšōšZ(y©│)ĪĘĄ─╚╦Įįų¬Ż¼įū╬ę╝╚╩ŪéĆ(g©©)┬ö├„Č°▓╗ē“Ū┌Ŗ^Īóėą▓┼╚AČ°▓╗ųžą▐B(y©Żng)Ą─īW(xu©”)╔·Ż¼ėų╩Ūę╗éĆ(g©©)ėą¬Ü(d©▓)┴óęŖ(ji©żn)ĮŌėųĖęė┌═¼─╦Ĥ╠¦Ė▄ĪóĮą░ÕĄ─īW(xu©”)╔·ĪŻī”(du©¼)▀@śėĄ─īW(xu©”)╔·Ż¼┐ūūė╩Ū▓╗┐╔─▄Śēų├▓╗╣▄Ą─Ż¼ę▓╩Ū▓╗┐╔─▄ų╗ė├“čŁčŁ╔ŲšT”Ą─ĘĮ╩Į╚ź╣▄Ą─ĪŻ╬ę┐éėX(ju©”)Ą├Ż¼┐ūūė▀@└’ė├Ą─ĘĮ╩ĮŻ¼┼cųąć°(gu©«)Üv╩Ę╔ŽČUū┌ūµÄ¤Įė╗»Ą▄ūėĄ─“░¶║╚”ĘĮ╩Įėąą®ŅÉ(l©©i)╦ŲĪŻ“░¶║╚”╚ń═¼ę╗Ę■├═╦ÄŻ¼┐╔ęį╩╣▓Ī╚ļĖÓļ┴ų«╚╦Ą├ęį╦┘ąčŻ¼“░¶║╚”ėų╚ń═¼“▒│║¾ō¶šŲ”ų«Ę©Ż¼┐╔ęį╩╣ł╠(zh©¬)├į▓╗╬“ų«╚╦Ą├ęįŅD╬“ĪŻ
▀\(y©┤n)ė├╚š│Ż╔·╗ŅųąĄ─īŹ(sh©¬)└²Š▀¾w▒Ē╩÷╔Ņ┐╠Ą└└ĒŻ¼╩Ū▒Šš┬Ą─╠ž³c(di©Żn)Ż¼ę▓╩Ūš¹éĆ(g©©)ĪČšōšZ(y©│)ĪĘĄ─╠ž³c(di©Żn)ĪŻ░ū╠ņ╦»ėX(ju©”)Ż¼┤_īŹ(sh©¬)▓╗╩Ū╩▓├┤┤¾Õe(cu©░)Ż¼Ą½╩ŪŻ¼Š═ĪČšōšZ(y©│)ĪĘ╗“┐ūūė╦∙ę¬ėæšōĄ─Ė∙▒Šå¢(w©©n)Ņ}Ż¼╝┤“ų┬┴╝ų¬”üĒ(l©ói)šf(shu©Ł)Ż¼╦³Š═╩Ūę╗éĆ(g©©)ĘŪ│Żųž┤¾Ą─Õe(cu©░)š`┴╦ĪŻ
ĪČšōšZ(y©│)ĪĘ▓╗╩Ū│ŻęÄ(gu©®)ęŌ┴x╔ŽĄ─ŽĄĮy(t©»ng)└ĒšōŻ¼ę▓▓╗╩Ūš▄└ĒĖ±čįŻ¼Ė³▓╗╩ŪāHāHųvéÉ└ĒĄ└Ą┬Ą─Ż¼Č°╩Ū┐ūūėį┌ūį╝║Ą─╔·├³╗Ņäė(d©░ng)ųą“ų┬┴╝ų¬”Ą─ėøõøŻ¼╩Ū┐ūūėī”(du©¼)ūį╝║“ų┬┴╝ų¬”▀^(gu©░)│╠Ą─├Ķ╩÷ĪŻ“┴╝ų¬”╩Ūį┌─│ę╗╝■ūŅŠ▀¾wĄ─╩┬╝■ųąŻ¼ļ[▓žĄ─“╠ņęŌ”“Ą└ą─”┼c“Ęą─”Ż¼ę▓Š═╩Ū“ėŅųµ——╔·├³”ŽĄĮy(t©»ng)╚½ŽóĄ─’@┬ČĪŻĪČęūĪĘį╗Ż║“╠ņąąĮĪŻ¼Š²ūėęįūįÅŖ(qi©óng)▓╗ŽóĪŻ”“╠ņ”ūį╝║╩Ūꬓąą”Ą─ĪŻ“┴╝ų¬”╝┤╩Ū“╠ņąą”Ą─’@┬ČĪŻ▀@ĘN’@┬ČŻ¼¤o(w©▓)╠Ä▓╗į┌Ż¼Ą½ė╔ė┌╚╦├įė┌ūį╝║Ą─ęŌūR(sh©¬)Ż¼▒Ńš┌╔w┴╦“╠ņąą”Ą─š²│Ż’@┬ČĪŻ▀@Š═╩Ū“┴╝ų¬”Ą─▒Š┴xĪŻ“ų┬┴╝ų¬”Š═╩Ūę¬Ģr(sh©¬)Ģr(sh©¬)ąĪą─ūį╝║Ą─Ė„ĘNęŌūR(sh©¬)Ę┴ĄK┴╦─Ńų¬╠ņąąĄ─ÜvöĄ(sh©┤)ĪŻōQŠõįÆšf(shu©Ł)Ż¼“ų┬┴╝ų¬”Š═╩Ū╔Ųė┌“ā╚(n©©i)╩Ī”Ż╗╩╣“┴╝ų¬”▓╗▒╗š┌╔wŻ¼ęį▒Ń└¹▓ČūĮĄĮ“╠ņąąĮĪ”Ą─šµīŹ(sh©¬)ķW╣ŌĪŻ▓╗ę¬ęį×ķ“┴╝ų¬”ų╗╩ŪķW╣ŌĪŻ▀@ķW╣ŌĄ─ę╗äxŻ¼Š═╩Ū“ėŅųµ——╔·├³”ŽĄĮy(t©»ng)Ą─╚½├▓Ż¼ūźūĪ┴╦Ż¼Š═╩ŪšµųŪ╗█ĪŻę╗╝┤ČÓŻ¼ČÓ╝┤ę╗ĪŻ
Č«Ą├┴╦“ų┬┴╝ų¬”Ż¼ę▓Š═Č«Ą├┴╦ĪČšōšZ(y©│)ĪĘĄ─Ė∙▒Š╠ž³c(di©Żn)ĪŻę“?y©żn)ķę╗ĘĮ├µŻ?ldquo;ų┬┴╝ų¬”Ą─“┴╝ų¬”Ż¼╩Ū“╠ņęŌ”“Ą└ą─”║═“Ęą─”Ż¼╩Ū¤o(w©▓)╔·╦└Īó¤o(w©▓)ā¶╣ĖĪó¤o(w©▓)į÷£pĄ─▓╗┐╔ĘųĖŅĄ─š¹¾wŻ¼╩Ūų„┐═Č■ĘųĄ─╦╝ŠSĘĮ╩Įļyęį░č╬šĄ─ĪŻ┴Ēę╗ĘĮ├µŻ¼“ų┬┴╝ų¬”Ą─“ų┬”Ż¼ų„ę¬╩Ūųv╚ń║╬▀_(d©ó)ĄĮ“╠ņęŌ”╝┤“┴╝ų¬”Ą─ĘĮĘ©å¢(w©©n)Ņ}Ż¼▀@éĆ(g©©)å¢(w©©n)Ņ}Ż¼┐╔ęįė├ĪČšōšZ(y©│)·īW(xu©”)Č°ĪĘŲ¬╩ūš┬Ą─Ū░╚²ŠõįÆüĒ(l©ói)šf(shu©Ł)├„ĪŻĄ┌ę╗ŠõŻ║“īW(xu©”)Č°Ģr(sh©¬)┴Ģ(x©¬)ų«Ż¼▓╗ęÓšf(shu©Ł)║§Ż┐”▀@╩ŪųvéĆ(g©©)╚╦▀_(d©ó)ĄĮ┴╝ų¬Ą─╣”Ę“║═▀_(d©ó)ĄĮ┴╝ų¬║¾Ą─ę╗ĘN«a(ch©Żn)╔·ė┌ā╚(n©©i)ą─Ą─ą─ŪķĪŻĄ┌Č■ŠõŻ║“ėą┼¾ūį▀h(yu©Żn)ĘĮüĒ(l©ói)Ż¼▓╗ęÓśĘ(l©©)║§Ż┐”▀@╩Ūųv▀_(d©ó)ĄĮ┴╝ų¬║¾┼c▀h(yu©Żn)ĘĮüĒ(l©ói)Ą─┼¾ėčę╗ŲĮ╗┴„ų┬┴╝ų¬ą─Ą├Ą─ę╗ĘN▒Ē¼F(xi©żn)ė┌═ŌĄ─ą─ŪķĪŻĄ┌╚²ŠõŻ║“╚╦▓╗ų¬Č°▓╗æCŻ¼▓╗ęÓŠ²ūė║§Ż┐”▀@╩ŪųvŪ¾┴╝ų¬ė└▀h(yu©Żn)╩ŪéĆ(g©©)╚╦Ą─╩┬Ż¼ę╗éĆ(g©©)╚╦ę╗éĆ(g©©)śėŻ¼▓╗Ū¾▒╗äe╚╦┐ŽČ©Ż¼äe╚╦▓╗└ĒĮŌūį╝║ų┬┴╝ų¬Ģr(sh©¬)Ą─ā╚(n©©i)ą─Ą─Ž▓ÉéŻ¼ę▓ø](m©”i)ėą╩▓├┤ųĄĄ├▓╗Ė▀┼dĄ─Ż¼Ė³▓╗æ¬(y©®ng)╚źÉ└┼Łäe╚╦ĪŻė┌┤╦Ż¼╬ęéā┐┤ĄĮŻ¼┐ūūė▀_(d©ó)ĄĮ┴╝ų¬Ą─ĘĮĘ©Ż¼╩Ū“ėą×ķĘ©”Ż¼╝┤═©▀^(gu©░)éĆ(g©©)╚╦Ą─“Ģr(sh©¬)┴Ģ(x©¬)ų«”Ą─ą▐B(y©Żng)Ą─╣”Ę“▀_(d©ó)ĄĮ┴╝ų¬Īó░č╬š╠ņęŌĄ─ĪŻ▀@Š═┼cĘĪóĄ└ā╔╝ę▀_(d©ó)ĄĮ┴╝ų¬Ą─ĘĮĘ©▓╗═¼┴╦ĪŻĘĪóĄ└ā╔╝ę╩Ū═©▀^(gu©░)“¤o(w©▓)×ķĘ©”▀_(d©ó)ĄĮ┴╝ų¬Ą─Ż¼Ę╝ęšf(shu©Ł)Ą─“Ę╚ļ▒Ŗ╔·ą─”║═Ą└╝ęšf(shu©Ł)Ą─“╩ź╚╦¤o(w©▓)│Żą─Ż¼ęį░┘ąšų«ą─×ķą─”Ż¼Š═╩ŪųvĄ─“¤o(w©▓)×ķĘ©”ĪŻ
“ų┬┴╝ų¬”×ķ╬ęéāĮę╩Š│÷┴╦┐ūūėų«╦∙ęįć└(y©ón)ž¤(z©”)“įūėĶĢāīŗ”Ą─šµīŹ(sh©¬)įŁę“ĪŻ“ų┬┴╝ų¬”Ą─Ė∙▒Šā╚(n©©i)║ŁŻ¼Š═╩Ūę¬╔Ųė┌║═ūį╝║ęŌūR(sh©¬)ųąĄ─╦Įė¹Īó═²─Ņų▄ą²Ż¼▓╗▒╗╦³╦∙“_Ż¼╦∙šTĪŻįū╬ę╩Ū▀@śėū÷Ą─å߯┐▓╗╩ŪŻĪ╦¹▓╗Ą½ø](m©”i)ėą▀@śėū÷Ż¼ŽÓĘ┤Ą─Ż¼ģs▒╗“╦Įė¹”“═²─Ņ”Ā┐ų°▒Ūūėū▀Ż¼│╔┴╦“╦Įė¹”“═²─Ņ”Ą─┼½ļ`Č°▓╗ūįų¬ĪŻę╗éĆ(g©©)╚╦ėą“╦Įė¹”“═²─Ņ”▓ó▓╗┐╔┼┬Ż¼┐╔┼┬Ą─╩Ūī”(du©¼)┤╦┬ķ─Š▓╗╚╩Ż¼╩¦╚źūįėX(ju©”)Ż¼▓╗ų¬▀@╩Ū“ų┬┴╝ų¬”Ą─┤¾ö│ĪŻ┐ūūėī”(du©¼)įū╬ę░ū╠ņ╦»ėX(ju©”)┤¾░l(f©Ī)ŲóÜŌŻ¼ŲõįŁę“Š═į┌ė┌┤╦ĪŻ▀Ć╩ŪČŁūėų±šf(shu©Ł)Ą├ī”(du©¼)Ż¼įū╬ę╩▄ĄĮ┐ūūė═┤│ŌŻ¼įŁę“Š═į┌╦¹į┌“ų┬┴╝ų¬”╔Ž│÷┴╦╝ä┬®ĪŻ
┐ūūėę└ō■(j©┤)įū╬ę░ū╠ņ╦»ėX(ju©”)▀@ĘNąą×ķŻ¼Ė─š²┴╦╦¹▀^(gu©░)╚źī”(du©¼)čį┼cąąĻP(gu©Īn)ŽĄĄ─┐┤Ę©ĪŻ▀^(gu©░)╚źŻ¼╦¹┬Ā(t©®ng)┴╦čįŠ═ą┼┴╦ąąŻ¼░ččį┼cąą┐┤│╔╩Ūę╗¾wĄ─Īó▒Šę╗Ą─Ż¼¼F(xi©żn)į┌Ż¼╦¹šJ(r©©n)×ķ▀@śė┐┤╩ŪÕe(cu©░)š`Ą─Ż¼æ¬(y©®ng)«ö(d©Īng)╩Ū┬Ā(t©®ng)Ųõčį▀Ćę¬ė^ŲõąąŻ¼ę“?y©żn)ķū„×ķéĆ(g©©)¾w╔·├³Ż¼Ųõ“ų¬”“čį”┼cŲõ“ąą”Ż¼▓ó▓╗╩Ūę╗¾wĄ─Īó▒Šę╗Ą─ĪŻČŁūėų±į┌ĪČšōšZ(y©│)š²▓├ĪĘĄ─“šZ(y©│)čįŻ¼╩ŪéĆ(g©©)Ž▌┌Õ”ųąšf(shu©Ł)Ż║“‘ėŅųµ——╔·├³’ŽĄĮy(t©»ng)╩Ūę╗éĆ(g©©)ė└║ŃĄ─š¹¾wŻ¼┼c▀@éĆ(g©©)š¹¾w▀\(y©┤n)äė(d©░ng)ŽÓĮy(t©»ng)ę╗Ą─╩Ū‘├„’Ż¼╚╬║╬‘├„’ģsėųų╗─▄╩ŪéĆ(g©©)¾wĄ─Īó┼żŪ·Ą─Īóš█╣ŌĄ─ĪŻ▀@╩ŪėŅųµųąĄ─Ė∙▒Š├¼Č▄ĪŻ▀@éĆ(g©©)├¼Č▄ø](m©”i)ėą┴╦Ż¼‘ėŅųµ——╔·├³’ę▓Š═╦└═÷┴╦Ż¼╩▓├┤ę▓ø](m©”i)ėą┴╦Ż¼¤o(w©▓)įÆ┐╔šf(shu©Ł)┴╦ĪŻę▓Š═╩Ūšf(shu©Ł)Ż¼éĆ(g©©)¾węŌūR(sh©¬)Ą─┼żŪ·ąį╩Ū▓╗┐╔┐╦Ę■Ą─Ż¼Č°╚╦ŅÉ(l©©i)Ą─šZ(y©│)čįꬎļ═Ļ╚½£╩(zh©│n)┤_▒Ē¼F(xi©żn)╚╦Ą─╚½▓┐ęŌūR(sh©¬)Ż¼─╦ų┴═Ļš¹├Ķ╩÷╩┬╬’Äū║§╩Ū▓╗┐╔─▄Ą─Ż¼šZ(y©│)čį▒Š╔Ē¤o(w©▓)īŹ(sh©¬)┴xĪŻ‘šZ(y©│)čį’╩Ūę╗ĘN‘ėŅųµ——╔·├³’ŽĄĮy(t©»ng)ųąĄ─▀\(y©┤n)äė(d©░ng)Ż¼Ūę╩Ūę╗ĘN╬ó║§Ųõ╬óĄ──▄┴┐▀\(y©┤n)äė(d©░ng)Ż¼ūŅČÓ▓╗▀^(gu©░)╩Ūę╗Ą└Ą└┴„ąŪėĻŻ¼╗“╩ŪķWļŖŻ¼Žļ┐┐╦³═Ļš¹Ę┤ė│‘ėŅųµ——╔·├³’ŽĄĮy(t©»ng)Ą─╚½▓┐Ą─š¹¾wĄ─▀\(y©┤n)äė(d©░ng)ĀŅørŻ¼Äū║§╩Ū▓╗┐╔─▄Ą─ĪŻ”▀@╩ŪĖµįV╬ęéāŻ¼éĆ(g©©)¾w╔·├³Ą─“ų¬”┼c“čį”═¼“ėŅųµ——╔·├³”ŽĄĮy(t©»ng)Ą─š¹¾wĄ─▀\(y©┤n)äė(d©░ng)Ż©“ąą”Ż®╩Ūę╗ī”(du©¼)Ė∙▒Š├¼Č▄Ż¼Č■š▀▓╗ę╗ų┬Ż¼╩Ūš²│ŻĄ─Ż¼Ųõ▒Š╔Ēø](m©”i)ėą╩▓├┤ī”(du©¼)Õe(cu©░)┐╔čįĪŻĻP(gu©Īn)µI╩Ū╚ń║╬ī”(du©¼)┤²▀@ę╗ī”(du©¼)├¼Č▄Ż║╩Ū“╠ņąąĮĪŻ¼Š²ūėęįūįÅŖ(qi©óng)▓╗Žó”─žŻ┐▀Ć╩ŪŽ±įū╬ę─ŪśėŻ¼▓╔╚Ī░ū╠ņ╦»┤¾ėX(ju©”)Ą─æB(t©żi)Č╚─žŻ┐║▄├„’@Ż¼š²┤_Ą─ū÷Ę©Ż¼æ¬(y©®ng)«ö(d©Īng)╩ŪŪ░š▀Ż¼Č°▓╗╩Ū║¾š▀ĪŻ┐ūūėų«╦∙ęįć└(y©ón)ģ¢Ąžž¤(z©”)éõįū╬ęŻ¼Ųõ─┐Ą─Š═╩ŪŽŻ═¹╦¹─▄ųąöÓūį╝║Ą─ę╗Ūą“═²─Ņ”Ż¼ęį“ūįÅŖ(qi©óng)▓╗Žó”Ą─æB(t©żi)Č╚ī”(du©¼)┤²“╠ņąą”ĪŻĻ░║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