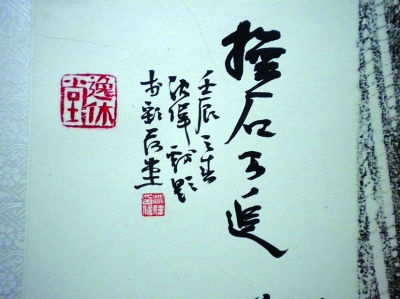-
沒有記錄!
論元好問以傳奇為詞現象
2014/12/29 11:38:30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作者簡介:趙維江,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發表過專著《金元詞論稿》等;夏令偉,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后,發表過論文《王惲秋澗詞研究》等。
內容提要:元好問在東坡“以詩為詞”和稼軒“以文為詞”的道路上繼續開拓,以傳奇為詞,在詞里不避險怪,述奇事,記奇人,寫奇景。這一現象是唐宋以來詞體形式及其觀念不斷演化的結果。詞序功能的進一步擴展,轉踏、鼓子詞等民間通俗文藝的說唱形式,稼軒以文為詞的創作范式,為傳奇體詞的創作提供了可操作的平臺和取材、結構、語言等方面的啟發與借鑒。遺山以傳奇為詞有著廣泛的背景和深厚的土壤。仙道思想及好奇尚異的審美觀,小說的志怪傳奇傳統及詩歌的好奇風尚,以詞存史的詞學觀念,對于以傳奇為詞現象的形成都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
關 鍵 詞:遺山樂府/詞體革新/傳奇/敘事
引言
在古代文學諸體裁中,詞體相對后起,所以對于其他體裁的借鑒也往往成了詞體變革的重要手段。宋詞發展過程中,曾出現過柳永引賦法入詞、蘇軾以詩為詞、辛棄疾以文為詞等重要的詞體革新實踐,傳統體制不斷解放,創作路子逐漸拓寬。但詞體的演化并未就此止步。自宋始,文學體裁的價值序列開始發生逆轉。伴隨著文學通俗化的進程,敘事文體迅速崛起,小說、戲曲的創作一片繁榮,逐漸取得了與詩、賦、詞等抒情文體同樣重要的地位。這種文體生態格局對于詞體自身的嬗變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隨著文體間的交集、互化,敘事因素向詞體悄然滲入,催化著其體制的新變革,由此而出現了以遺山詞為典范的以傳奇為詞的現象。
所謂傳奇,本為小說、戲曲等敘事文體的一個門類,后世又以之泛稱情節離奇或人物行為非常的故事。謂元好問以傳奇為詞并非說他以詞的形式寫傳奇故事,而是指這類詞作有著傳奇的某些要素和特色,具有更強的敘事性和故事性。陳廷焯后期不滿意遺山詞的一個主要理由是背離詞體“正聲”①,“刻意爭奇求勝”②,陳氏實際上指出了元詞的一個重要的藝術創新點。通觀遺山詞,我們會發現其“刻意爭奇”不僅表現在語言風格上,還表現在詞的選材、作法等方面。元好問的許多詞作不避險怪,述奇志異,呈現出一種明顯的“傳奇”特征,不妨稱其為“傳奇體”。其中典型的作品,大致呈現為一種詞序敘述故事而正文詠嘆故事的結構形式。但這種傳奇體并未改變詞體的抒情特質,只是改變了傳統詞體表達方式上的比重和抒情效應,即使那些直接以正文述奇的作品,其著力點仍是在對故事的驚嘆感慨之上。
以傳奇為詞可以說是元好問在蘇、辛的詞體革新基礎上最富于創造意義的開拓。東坡“以詩為詞”和稼軒“以文為詞”的典型作品并不多,但其詞體革新的意義和詞學史意義則十分重大;就遺山詞整體而言,雖然取材、造意上“刻意爭奇”的傾向普遍存在,但其中典型的傳奇體作品數量也只是一小部分,不過,它們卻往往是遺山最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佳作,如《摸魚兒·雁丘詞》、《摸魚兒·雙蕖怨》、《水調歌頭·賦三門津》等。遺山詞中奇人、奇事及奇景的敘寫,拉近了詞與自然和社會的距離,大大增強了詞體文學的敘事功能,擴大了詞的表現范圍,提高了詞的藝術表現力和可讀性。同時進一步密切了敘事文學與抒情文學的關系,為二者的有機結合提供了一條富于啟發性的思路,客觀上促進了后世戲曲、小說中詩文結合形式的形成和成熟。以傳奇為詞的作用和意義尚可討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已開始邊緣化了的詞體由此被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遺山樂府以傳奇為詞現象述略
關于遺山樂府的傳奇現象,大致可從如下三方面來考察:
(一)述奇事
這一類作品當以兩首著名的《摸魚兒》(雁丘詞、雙蕖怨)為代表。兩首詞前分別以序文形式敘述了兩件奇事,一為親歷,一為耳聞;一為人事,一為物情,然皆行事罕異,情節離奇,又皆旨歸情愛,感泣人神。遺山樂府中還有一篇同類題材的《梅花引》,小序所述故事情節更為復雜和詳盡:
泰和中,西州士人家女阿金,姿色絕妙。其家欲得佳婿,使女自擇。同郡某郎獨華腴,且以文彩風流自名,女欲得之。嘗見郎墻頭,數語而去。他日又約于城南,郎以事不果來。其后從兄官陜右。女家不能待,乃許他姓。女郁郁不自聊,竟用是得疾,去大歸二三日而死。又數年,郎仕,馳驛過家。先通殷勤者持冥錢告女墓云:“郎今年歸,女知之耶?”聞者悲之。此州有元魏離宮,在河中潬。士人月夜踏歌和云:“魏拔來,野花開。”故予作《金娘怨》,用楊白花故事。詞云:“含情出戶嬌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春去秋來雙燕子,愿銜楊花入窠里。”郎,中朝貴游,不欲斥其名,借古語道之。讀者當以意曉云。“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托清塵”,是崔娘書詞,事見元相國《傳奇》。長達二百五十余字的序文寫得一波三折,首尾相應,引人入勝,其本身可以說就是一篇傳奇小說。
此類愛情傳奇也出現在《太常引》一詞中,其序云:“予年廿許,時自秦州侍下還太原,路出絳陽。適郡人為觀察判官,祖道道傍。少年有與紅袖泣別者。少焉,車馬相及,知其為觀察之孫振之也。所別即琴姬阿蓮。予嘗以詩道其事。今二十五年。歲辛巳,振之因過予,語及舊游,恍如隔世。感念今昔,殆無以為懷,因為賦此。”詞文接著對此深情地歌詠道:
渚蓮寂寞倚秋煙,發幽思,入哀弦。高樹記離筵,似昨日、郵亭道邊。白頭青鬢,舊游新夢,相對兩凄然。驕馬弄金鞭,也曾是、長安少年。大家公子流連青樓鮮有付之真情者,而振之竟如此癡情,也實屬奇聞。此事為遺山親見并深為感動,當年他賦詩以紀,二十五年后又詠之以詞。
遺山樂府中所述奇聞多為凄艷情事,但也不乏其他方面的奇聞異事,如《水調歌頭》(云山有宮闕)就是一篇題材特異的詞體“傳奇”。其序交代,作者與友人同訪嵩山少姨廟,于殘壁間發現了一段字跡模糊的古辭,便“磴木石而上,拂拭淬滌,迫視者久之,始可完讀”,之后又推測辭文所屬年代,并將壁文加以整理而題為《仙人詞》。這樣,一次意外的發現,一個撲朔迷離的懸案,引發出遺山一段奇思妙詞:
云山有宮闕,浩蕩玉華秋。何年鸑鷟同侶,清夢入真游?細看詩中元鼎,似道區區東井,冠帶事昆丘。壞壁沈風雨,醉墨失蛟虬。問詩仙,緣底事,愧幽州?知音定在何許,此語為誰留?世外青天明月,世上紅塵白日,我亦厭囂湫。一笑拂衣去,崧頂坐垂鉤。遺山所記奇事,多采自民間傳聞,并不深究虛實,而是“實錄”于筆下,以為詩料談資,并借之抒寫懷抱。如《摸魚兒》(笑青山)一詞,記述了一件十分怪誕的“正月龍起”故事。據詞序,作者與友人同游龍母潭,相傳當年韓愈垂釣于此“遇雷事,見天封題名”,夜里果然“雷雨大作,望潭中火光燭天。明日,旁近言龍起大槐中”。于是,詞人在一片神異幻誕的語境中開始了他隱逸淡泊情懷的歌唱。再如《江城子》(纖條裊裊雪蔥蘢)一詞詠酴醾花,詞序先引入一段艷麗而怪誕的傳說:“內鄉縣廟芳菊堂前,大酴醾架芳香絕異。常年開時,人有見素衣美婦。迫視之,無有也。或者以為花神。”借此神異事,作者在詞文中想象天上花神于“月明中,下瑤宮”,種下了千百畝蘭蕙,由此引發出詞人“只恐行云、歸去卷花空”的憂思和“剩著瓊杯斟曉露,留少住,莫匆匆”的癡舉。
詞人皆愛寫夢,遺山也不例外,不同的是遺山筆下的夢境有時被演繹成一個荒誕不經的故事。夢境是遺山詞傳奇述異的一個重要途徑。如《永遇樂》(絕壁孤云)即寫了一個幻生于真,真通于幻的怪夢。據詞序,詞人“夢中有以王正之樂府相示者”,并記住了末尾數句,但夢魂始定之后,恍然省悟“正之未曾有此作”。及至次日,在友人的鼓勵下“作《永遇樂》補成之”,續完了這段夢緣。又如《品令》一詞,寫的是他“清明夜,夢酒間唱田不伐《映竹園啼鳥》樂府”之事,詞中寫道:“夢中行處,數枝臨水,幽花相照。把酒長歌,猶記竹間啼鳥。”夢中唱詞,令人稱絕。
(二)記奇人
元遺山編《中州集》以詩系人,以小傳記人,有意識地保留下百年以來詩壇上眾多“苦心之士”的身影,集中特設“異人”一目,專為特立獨行之士立傳寫真。其實遺山詞中也多有此類奇士異人的形象。
元好問在志怪小說《續夷堅志》中曾寫過許多身手不凡的僧道,而其詞作《滿庭芳》也描述了這樣一位奇人,其序云:
遇仙樓酒家楊廣道、趙君瑞皆山后人,其鄉僧號李菩薩者,人頗以為狂。嘗就二人借宿。每夜客散,乃從外來,臥具有閑剩則就之,不然赤地亦寢。一日天寒,楊生與之酒,僧若愧無以報主人者。晨起持酒碗出,同宿者聞噀酒聲。少之,僧來說云:“增明亭前花開矣,公等往觀之。”人熟其狂,不信也。已而視庭中牡丹,果開兩花。是后僧不復至。京師來觀者車馬闐咽,醉客相枕藉,酒壚為之一空。趙禮部為雷御史希顏所請,即席同予賦之。時正大四年之十月也。牡丹花開寒冬,可謂一大奇觀,而此奇觀竟由奇人點化而成,又是奇中之奇。作者在序文中側面點染,懸念巧設,著重描寫李菩薩的狂怪個性和神奇道術,寫得活靈活現,如睹其人,如聞其聲。
遺山樂府涉及各色各樣的人物,但直接寫人的篇目并不多,不過除一般壽詞外,所紀者多為特異非常之人。如《水龍吟》(少年射虎名豪)寫商州守帥斜列(又作:色埒默)的傳奇生平,《滿江紅》(畫戟清香)述戰功赫然的武將郝仲純“風流有文詞”的儒雅風度。遺山樂府中也記載了一些下層人物的傳奇故事,如前面提到的“大名民家小兒女”(《摸魚兒》)、“西州士人家女阿金”(《梅花引》)等,此外還有一篇為一對樂人夫婦立傳的《木蘭花慢》:
要新聲陶寫,奈聲外有聲何?愴銀字安清,珠繩瑩滑,怨感相和。風流故家人物,記諸郎、吹管念奴歌。落日邯鄲老樹,秋風太液淪波。十年燕市重經過。鞍馬宴鳴珂。趁饑鳳微吟,嬌鶯巧囀,紅卷鈿螺。纏頭斷腸詩句,似鄰舟、一聽惜蹉跎。休唱貞元舊曲,向來朝士無多。據詞序和詞文,這位被稱作“張嘴兒”的樂人長于吹觱篥,其婦田氏為歌者。他們在貞元年間曾走紅京師的樂壇歌臺,也屬當時特異之人。十年后,詞人又與他們邂逅于“燕京”,聽到他們演唱當年的歌曲,然而“向來朝士無多”,張氏夫婦也歷盡了磨難,“斷腸詩句”令作者不勝感慨。短短一首小詞,畫出了一幅梨園“風流故家人物”圖。
實際上,人與事難以截然分開,人以事傳,事以人明,遺山樂府所記奇事、奇人常常是交織在一起的,在具體描寫中只是有所側重而已。
(三)寫奇景
雄壯的北方山水、奇特的中州物象,相對于宋詞所寫的小橋流水而言,本身就具有一種陌生感,遺山以之入詞,或為歌詠對象,或為人事背景,顯得奇特異樣,有時,作者還有意地選擇一些怪異景象入詞,或者以志怪手法寫景,從而使許多詞中景觀物態蒙上了一層異光奇彩。
有學者根據計算機統計數據指出,在兩萬余首宋詞中,真正以山水為主要描寫對象的作品并不多,特別是寫北方奇山異水的詞作更為罕見。即使寫山水,也多是清秀婉麗之景,少有雄奇壯闊的境界。東坡筆下“大江東去”的壯偉景觀,罕有繼響。辛稼軒以豪杰之氣縱橫詞壇,但限于經歷,筆下也少有險峻雄奇的北方山川景象③。這一論斷是符合詞史實際的。真正以詞寫出北方山水奇觀的是元好問。元氏以其得天獨厚的條件,挾幽并豪俠之氣,遨游于北國名山大川之中,將一幅幅雄麗的山水畫圖攝入詞中。如《水調歌頭·賦三門津》所寫黃河三門峽景象雄奇險峻,被認為“崎嶇排奡,坡公之所不可及”④。又如《念奴嬌》(欽叔、欽用避兵太華絕頂,有書見招,因為賦此)一詞上片對華山神奇景象的描寫:
云間太華,笑蒼然塵世,真成何物。玉井蓮開花十丈,獨立蒼龍絕壁。九點齊州,一杯滄海,半落天山雪。中原逐鹿,定知誰是雄杰。本詞為步韻東坡《念奴嬌·赤壁懷古》之作,所寫華山壯奇之景和險峻之勢,酷肖東坡,其宏闊境界或有過之。
遺山詞所寫奇景也包括一些奇特的人文物象,如《清平樂》(丹書碧字)一詞曾寫到他所目睹的“天壇石室”所藏《金華丹經》,其詞序云:
夜宿奉先,與宗入明道談天壇勝游,因賦此詞。司馬子微開元十七年中元日,藏《金華丹經》于天壇石室。中興亂后,人得之,字畫如《洛神賦》,縑素亦不爛壞。予于山陽一相識家嘗見之。遺山將所見珍奇文物,紀之以詞,表達他的驚嘆之情。再如一首《八聲甘州》,似寫秦漢故宮風物,極具夢幻感:
玉京巖、龍香海南來。霓裳月中傳。有六朝圖畫,朝朝瓊樹,步步金蓮。明滅重簾畫燭,幾處鎖嬋娟。塵暗秦王女,秋扇年年。一枕繁華夢覺,問故家桃李,何許爭妍?便牛羊丘隴,百草動蒼煙。更誰知、昭陽舊事,似天教、通德見伶玄。春風老、擁鬟顰黛,寂寞燈前。詞人透過眼前的“丘隴”“蒼煙”,居然看到一片如真如幻的仙苑神殿,正若作者另一首《沁園春》中所寫:“腐朽神奇,夢幻吞侵,朝昏變遷。”無疑,作者已將對現實中華屋丘墟的巨大悲慨投入到了這幻化如夢的奇異景觀之中。
二詞體傳奇性敘事的內在動因及傳統
由上可見,元好問以傳奇為詞的作品,較之于抒情言志的傳統詞體形態,明顯地增強了敘事成分,語言風格更為通俗化,而且有意追求一種戲劇化的藝術效果。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種向當時流行的小說、戲曲等通俗敘事文體靠攏的跡象。它作為一種創作方法和詞體形態,并非純由元好問個人興趣所致,實為東坡“以詩為詞”和稼軒“以文為詞”的詞體革新進程的繼續,是唐宋以來詞體形式及其觀念不斷演化的結果,有著深刻的內在動因和歷史淵源。
(一)詞序篇幅與功能的擴張
從詞體結構形式看,遺山詞中傳奇故事的主要載體是作品的序文。詞序作為詞體的衍展部分,主要作用是交代寫作緣起及背景,而以之述奇志異,當是伴隨著詞體表現領域的不斷擴大和詞序功能進一步擴展,篇幅相應增長,并由此獲得相對獨立的結果。就表達特性而言,詩、詞皆長于抒情而拙于敘事,然古體詩中也不乏《孔雀東南飛》、《長恨歌》這樣的長篇敘事之作,一個重要原因是古體沒有篇幅的限制;相反,格律嚴格且篇幅短小的近體中敘事就難以展開。在這一點上,詞體頗類似,格律和篇幅的限制注定了它缺少敘事功能。然而,隨著創作中主體意識和寫實性的增強,作品所言之情的個性化愈加突出,產生其情意的事由便需要作必要的交代,于是作者借用詩歌題序的形式來突破詞體有限的空間。從唐以來文人創作來看,詞序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短到長,從詞文補敘到獨立成章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詞體敘事功能和傳奇色彩不斷增強的過程。
蘇軾對于詞序功用的擴展具有標志性意義。他不僅大量寫作長序,而且通過序文記載了一些富有傳奇色彩的人與事。如《水龍吟》(古來云海茫茫)述謝自然求仙奇遇,《戚氏》(玉龜山)“言周穆王賓于西王母事”,《洞仙歌》(冰肌玉骨)以近百字長序述花蕊夫人作詞的傳說。至南宋,詞有題序已成常例,小序在作品中具有了獨立的審美價值,敘事傳奇因而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間。如稼軒詞題序數量在兩宋詞中最多,有些詞序的內容明顯有傳奇性敘事的性質,如《蘭陵王》(恨之極)即以篇幅長于本詞的序文記述了一個情節完整而奇異的夢境。在共時異域的金詞中,詞序的運用同樣十分普遍,如曾為辛棄疾業師的蔡松年,其詞序動輒數百言,最長的近六百字,清張金吾《金文最》收其詞序十二篇,足見其獨立的文體學價值。詞序篇幅的擴張和相對獨立,使較為完整的敘事成為可能,如蔡松年《水調歌頭》(云間貴公子)一詞表達對曹浩然人品的欽敬和志趣的投合。詞前以約二百字長序,介紹曹浩然“人品高秀”,卻“流離頓挫”的遭際和流連詩酒,“悠然得意”的獨特個性。無疑,這樣的詞序,等于在詞的正文之外又搭建了一個供詞人騰挪跌宕顯露才情的平臺,這時序文的作用已經不僅限于揭示主旨,或簡單地交代寫作背景及緣起了,實際上它已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表現空間,凡是與詞情相關且不適合或無法在正文中表現的人、事、物、理等內容都可展示于此。與正文以抒情為主不同,序文最重要的功能是敘事,奇聞逸事的敘述便由此在詞作中得到更為完整、更為具體地展開。
(二)詞體傳奇性敘事傳統的嬗變
以詞序為主要載體的傳奇體,經過東坡、稼軒等詞人的不斷實踐,到元好問時已形成規模并構成了一種新型的詞體范式。雖然詞序內容十分豐富,并非一定要傳奇述異,但傳奇性敘事始終是詞體的一個基本因子和傳統,元好問作傳奇體只不過是這一因子發育成熟和這種傳統發揚光大的結果。我們可以從曲子詞與民間通俗文藝的關系上來探求這一發展的線索。
作為燕樂歌詞的曲子詞,除了其基本形式的只曲小唱外,在民間還有“轉踏”、“纏達”、“鼓子詞”等歌舞劇形式。如“轉踏”多用《調笑》曲,故又稱“調笑轉踏”,它由一個曲調連續歌唱以表演一個或多個故事,其文本多為一組聯章體詞。所敘故事,多為奇人異聞。今存文人作品如北宋鄭僅的《調笑轉踏》分詠羅敷、莫愁、卓文君、桃花源等十二事;秦觀的《調笑轉踏》十首分詠王昭君、崔鶯鶯等十位古代美女的傳奇艷情。這類詞一般在詞文前有一段獨白和七言詩。詩、詞相配,吟唱結合,共同演繹故事,如秦觀寫崔鶯鶯的一首:
崔家有女名鶯鶯。未識春光先有情。河橋兵亂依蕭寺,紅愁綠慘見張生。
張生一見春情重。明月拂墻花樹動。夜半紅娘擁抱來,脈脈驚魂若春夢。
春夢。神仙洞。冉冉拂墻花樹動。西廂待月知誰共。更覺玉人情重。紅娘深夜行云送。困亸釵橫金鳳。由本首作品看,詩歌部分主要用來敘事,曲詞部分雖然也有敘事成分,但側重于抒情詠嘆,這在調笑轉踏詞中有一定普遍性。蘇、辛、元等以傳奇為詞的作品,在內容的尚奇傾向和敘事性等特點上,可以說與這類調笑轉踏詞一脈相承;此外,在敘事結構上二者也很有些類似,只是傳奇體詞以序文代替了詩歌。又因為序為散文形式,故敘事也更為完整具體。
在敘事內容和結構上,宋代流行的說唱性質的聯章鼓子詞可能與傳奇體詞關系更為密切。如歐陽修《采桑子》十一首,詠西湖勝景,前有短序,作為開場。又如趙令疇的《商調蝶戀花》,用十二首曲子演唱元稹傳奇小說《鶯鶯傳》故事,他采用一段散文一首歌詞的形式,以散文講述情節,以歌詞詠嘆故事。這種說唱結合的形式對于中國傳統文藝有著兩個極向的啟示:在表演藝術方面,它的導向是更大規模且采用套曲形式的諸宮調;在詞體演化方面,其結構形式和題材特點為單篇傳奇體的形成提供了參照系。在這個意義上,傳奇體詞可謂聯章體說唱詞的簡約化。
轉踏、鼓子詞等演唱文本與傳奇體詞在體制、受眾和傳播方式等方面都有明顯的不同,然而在傳奇性敘事和序詞結合的結構形式上,二者則明顯地呈現出某種趨同性。雖然不能說后者是在前者影響下形成的,但這種情況至少可以說明,自唐宋以來詞壇上一直存在著以傳奇性敘事的傳統,詞體傳奇性敘事的因子在社會文化消費需求的推動下,不斷強化和擴張,最終形成以遺山詞為典范的傳奇體。可見,以傳奇為詞現象的產生實有其體制內的必然性。
(三)以文為詞的延展與深化
從詞體革新角度看,以傳奇為詞實質上是稼軒以文為詞的延展和深化。以文為詞必然導致詞體敘事功能的增強。詞體語言和手法的散文化,可使其擺脫詩化語言整飭、沉凝、雅奧、套路化等因素的束縛,大大增加表達的豐富性和靈活性,從而使故事的敘寫更具有可操作性。事實上,在稼軒以文為詞的篇章里已有許多述奇志異之作,如《摸魚兒》(問何年)寫一塊“驚倒世間兒女”的“狀怪甚”的石頭,為了突出詞中怪異的描寫,作者索性將調名改為《山鬼謠》,但這首詞的序文卻很短,故事主要通過詞文散體化的描述展開。遺山的以傳奇為詞繼承了稼軒以文為詞的傳統并積極開拓,它將“文”的外延由一般的傳統古文擴展到小說、俗曲、戲劇等通俗文學形式,其語言、結構及其表現手法由一般的散文化傾向進一步向傳奇性敘事凝聚。因而,在傳奇體詞作中,傳奇精神并非僅僅體現在詞序里,而是彌散在作品的各個層面。
如前所述,遺山詞的傳奇性敘事一般放在詞序中,而詞文重在詠嘆,詫怪驚奇,旨歸于感懷。如元氏《摸魚兒·雙葉怨》詞序詳敘故事,詞文則著意于贊嘆“小兒女”那種“海枯石爛情緣在”的情愛。不過,即使這一類作品,其詞文仍然有一定的敘事性質。如寫阿金故事的《梅花引》,其詞云:
墻頭紅杏粉光勻,宋東鄰,見郎頻。腸斷城南,消息未全真。拾得楊花雙淚落,江水闊,年年燕語新。見說金娘埋恨處,蒺藜沙,草不盡。離魂一只鴛鴦去,寂寞誰親。惟有因風,委露托清塵。月下哀歌宮殿古,暮云合,遙山入翠顰。詞中敘述雖簡,但梗概清晰,從墻頭相見到城南爽約,從阿金相思而歿到郎歸月下哀歌,人物、時地、經過等主要的敘事因素都披文可見,事明而情真。遺山詞語言并不像稼軒詞那樣有明顯的古文之風,其散體化敘事因素主要體現在作品的內在結構上。
在遺山詞中,傳奇性描述有時也主要靠詞文來承擔,這種情況多出現在寫景之作中,這些詞作一般為短序或無序,作者在詞文中以描寫性語言渲染氣氛,形容景象,營造氣勢,如《水調歌頭·賦三門津》等。不過,遺山專以詞文傳奇敘事寫人的作品很少,偶爾為之,則風調令人耳目一新,如《眼兒媚》寫其子叔儀兒時之事:
阿儀丑筆學雷家,繞口墨糊涂。今年解道,疏籬凍雀,遠樹昏鴉。乃公行坐文書里,面皺鬢生華。兒郎又待,吟詩寫字,甚是生涯。詞中所寫內容并無甚奇特,但作者將兒子學字吟詩的天真樣子與自己老而無用仍“行坐文書里”的處境相比照,便頓然生出一種強烈的戲劇性傳奇效果,揭示出一個難解的人生悖論。詞的行文也有異于元詞常態,寫得俗白流利,猶若話本曲詞。
三元好問以傳奇為詞的文化與文學背景
元好問以傳奇為詞現象是詞體演化的結果,但這種演化不是孤立進行的,它實質上是一種文學、文化現象,有著廣泛的背景和深厚的土壤,下面從三個方面分述之。
(一)仙道思想及好奇尚異的審美觀
元好問以傳奇為詞現象的產生,與他所處時代的詞學觀念、文學思潮有密切的關系,但這些關系之于作者創作的效應,歸根結蒂還是取決于作者的世界觀和價值信仰,特別是審美觀。具體而言,以傳奇為詞是遺山好奇尚異審美觀的產物,而仙道思想則是元氏以奇異為美觀念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礎。
詹石窗先生曾著文闡述元好問的仙道思想,他指出:“殘酷的現實使他遁入老莊的思想幽宮之中。在長期的生涯里,他又與許多道門中人來往。盡管他在個別場合表白‘神仙非所期’,但在許多情況下卻又借仙境的想象或道門典故以抒寫情懷。”從元好問的相關詩詞作品中“不僅可以看出他對道門圣跡之諳熟,而且也可追蹤他試圖通過仙家勝境之神游而排遣煩惱之心跡”⑤。金元之際,全真道教十分流行,元好問在《通仙觀記》中談到他的神仙觀:
予嘗究于神仙之說。蓋人稟天地之氣,氣之清者為賢;至于仙,則又人之賢而清者也。黃、老、莊、列而上不必置論,如抱樸子、陶貞白、司馬煉師之屬,其事可考,其書故在,其人可想而見。不謂之踔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其可乎?使仙果不可成,彼稱材智絕出,事物變故皆了然于胸中,寧若世之昧者蔽于一曲之論,僥幸萬一,徒以耗壯心而老歲月乎?由此可見,元好問對于仙的存在深信無疑,只是認為仙是“人之賢而清者”。盡管這種認識一定程度上把仙俗世化了,但是他并不否認這些仙人的神奇法力。這一點在他描述仙道者流的詩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如《普照范煉師寫真三首》其三贊美范煉師的法力:“鶴骨松姿又一奇,化身千億更無疑。人間只說乘風了,覿面相呈卻是誰。”《通玄大師李君墓碑》記通玄大師李君的神奇本領:“莘公鎮平陽,以歲旱請君致禱,車轍未旋而澍雨沾足,時人以神人許之。”《華巖寂大士墓銘》寫到“叢竹”不死長生的神奇:“龕前叢竹,既枯而華,隨采隨生,人以為道念堅固之感。在專述異聞的《續夷堅志》中此類例子更多。作品所記奇人異事多是作者耳聞目見并有意識地記錄積累下來的,這些材料的時間跨度幾乎覆蓋了他一生,可見元好問對于奇聞異事的廣泛而持久的興趣。他曾在《紫虛大師于公墓碑》一文中解釋離峰子苦行得道說:“夫事與理偕,有是理則有是事,三尺童子以為然。然而無是理而有是事,載于書、接見于耳目,往往有之,是三尺童子不以為然,而老師宿學有不敢不以為然者。”元氏認為,這些怪異現象雖然無法用目前已知的事理解釋,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認它們真實地發生過。
道人法力和仙家勝境在元遺山心目中不僅真實存在,而且心向往之。仙道所具有的超自然能力可以讓人擺脫俗世的惡濁和殘酷,這對于在現實生活中由于家破國亡和人生抱負破滅而備受靈魂煎熬的元好問而言,無疑是一個極大的誘惑。在這里,奇異成了自由的語符,神怪成了人性的寄托。由此,神奇怪異被賦予了美好的品質。正是這樣的審美理想,引導著元遺山去關注、尋找并傳述奇人異事。由是觀之,遺山詞中出現諸如大雁殉情、花開并蒂的千古奇觀和可令牡丹花開寒冬的李菩薩等神異之人也就不足為怪了。需要指出的是,元好問所秉持的仙道信仰及其好奇審美觀并不完全出于他個人的喜好,南宋金元時期是仙道文化的黃金時代,特別是全真道教在北方蓬勃的發展,以奇異為美是當時文人的普遍好尚,作為文壇領袖的元好問,其思想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和代表性。
(二)小說志怪傳統及詩歌好奇風尚
金元時代普遍的仙道信仰與尚奇審美觀直接影響著人們的文學價值認知和創作趣向,無論是作為主流文體的詩歌,還是方興未艾的小說、劇曲等通俗敘事文學,都呈現出一種喜寫奇異險怪的創作傾向。處于這樣一種文學環境中,以傳奇為詞現象的出現當是順理成章之事。
志怪傳奇小說,可以說是詞壇傳奇體最近的親戚。從遺山以傳奇為詞的作品中,可明顯地看到此類詞作與傳奇類小說之間的密切聯系。如《梅花引》在序文中講完故事后,特別引用了元稹的小說《鶯鶯傳》中的鶯鶯詩句,并特別注明“崔娘書詞,事見元相國《傳奇》”,由此可窺傳奇小說影響之一斑。小說一體經志怪、傳奇和話本等不同形式的演變,至金、元時代已呈勃興之勢。元好問本人曾著筆記小說《續夷堅志》,多記荒誕怪異之事,稱由此可“惡善懲勸”,“知風俗而見人心”⑥。這種道德功利說突破了儒家“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的正統觀念,從而讓作者放手去志怪述異。以言情見長的詞不同于小說,遺山以之傳奇述異,實際上是將小說的功能部分地轉移到了詞里。如《摸魚兒》(恨人間)寫大雁殉情,奇事奇情,感人至深。有趣的是,《續夷堅志·貞雞》也是一則動物殉情的故事:
房皞希白宰盧氏時,客至,烹一雞。其雌繞舍悲鳴,三日不飲啄而死。文士多為詩文。予號之為“貞雞”。二作雖體裁不同,情節卻驚人相似。不同的只是小說文字簡略平淡,盡管也以“貞”字表明了贊賞之情,但限于體裁,主觀情感并不明顯;而《摸魚兒》則序、詞配合,表達了詞人十分強烈的愛憎態度,“綿至之思,一往而深,讀之令人低回欲絕”⑦。同樣體現了“知風俗而見人心”的意義。
與筆記小說性質十分接近的“本事”詞話與傳奇體詞的關系可能更親近一些。詞體因短于敘事而致所敘事物簡略模糊,這卻給詞的內容造成了更大的解讀空間。詞本為娛賓遣興的通俗歌詞,多寫麗情艷事,不僅歌詞本身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歌詞背后的“本事”也撩撥著人們的好奇心。于是,揭秘“本事”的詞話便隨之而生。今見的幾部早期詞話,內容多為詞人風流韻事的記載,而“奇”則是編者選材的一個主要標準。《本事曲子》是宋代第一部紀“本事”的詞話,蘇軾贊賞說它“足廣奇聞”⑧,并且還把“其人甚奇偉”的陳慥等人的事及詞提供給楊繪以作該書增補。這些“本事”許多為小說家言,實際上是一些借詞作和詞人之名而“炒作”的傳奇故事。不過,這類詞話與作品密切相關,對于作品的解讀和傳播有著超越文本自身的意義。這類“本事”詞話與傳奇體的詞序在內容取向上極類似,又皆用散文形式,而且對于詞作都有著“助讀”、“促銷”的功用;不同的是詞序為文本的有機部分,而詞話游離于詞作之外,屬于體制外的附加物。宋人中柳永、蘇軾的“本事”詞話最多,但蘇詞中凡有詞序詳細交代寫作緣起背景的作品,則少有所謂“本事”流傳。是否可以詞序的傳奇性敘事看作是逸聞類“本事”詞話的體制內轉移呢?
此外,詩體作為詞體之同宗,其好奇尚異的風氣對于以傳奇為詞現象的產生當有更大更直接的影響。中晚唐以來,受通俗敘事文學影響,詩歌的敘事功能不斷強化,其中不乏述奇志怪之作。如白居易《長恨歌》兼傳奇與志怪于一體,李賀詩風險怪,杜牧稱其“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⑨。宋詩中也有許多如蘇軾《游金山寺》中“江中似有炬火明”,“非鬼非人竟何物”一類的怪異描寫。金代詩壇南渡后由趙秉文和李純甫主導,曾形成了一種好奇風尚,李純甫尤甚。對此,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之十六借對孟郊、李賀詩的批評說:“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鑒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元氏雖然更欣賞李白明朗清新的寫法,但對于李賀詩雖寫鬼怪但真情感人的特點也給予了明確的肯定。
實際上遺山詩也多有紀詠離奇故事和怪異景象的內容。如《水簾記異》所寫情景:
神明自足還舊觀,涌浪爭敢徼靈通。何因狡獪出變化,勝概轉盼增清雄。天孫機絲拂夜月,佛界珠網搖秋風。東坡拊掌應大笑,不見蟄窟鞭魚龍。而比這首詩晚一天所作的《谼谷圣燈》,所紀景象更為怪異:
山空月黑無人聲,林間宿鳥時一鳴。游人燒香仰天立,不覺紫煙峰頭一燈出。一燈一燈續一燈,山僧失喜見未曾。金繩脫串珠散進,玉丸走樣光不定。飛行起伏誰控摶,華麗清圓自殊勝。北荒燭龍開晦冥,南極入地多異星。這兩首詩分別記載了作者游黃華、谼谷的奇遇異聞,多用靈怪意象寫奇特之境。元好問向來主張詩詞一理,因此在詩里紀寫奇異的做法也順理成章地移到了詞里。如遺山樂府中《摸魚兒》(笑青山)和《水調歌頭·賦三門津》等詞,與上述兩首詩在取材取法上都十分接近。
(三)以詞存史觀念與詞中的奇聞實錄
從詞學觀念角度看,以詞存史的“詞史”意識當是以傳奇為詞現象形成的最終的有力推手。南宋后,隨著“尊體”意識的興起,詞史意識也逐漸凸現出來。至元好問,一種自覺的詞史意識已形成,并成為他詞學活動的一個重要動因。所謂詞史意識有三層意義,一是“詞亦有史”之意,即詞有其自身的發展史;二是將詞作為歷史文獻保存;三是以詞體負載史實內容。直接影響元氏以傳奇為詞的主要是后兩個方面所體現的以詞存史觀念。
詞史意識是元好問以其史學觀觀照詞學的產物。需要指出的是,元好問的史學觀并不囿于正統的正史中心意識,他治史的目的在于“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聞”⑩,所以他所關注的不僅有帝王社稷的廢立興亡,更包涵了廣泛的社會文明發展歷史。因而野史逸聞,三教九流,凡被認為屬“一代之美”者皆被采摭入囊。在這種開放的“野史”視野中,民間流傳的離奇怪異之事自然也具有了“史”的價值而引起作者極大的興趣。他以“野史亭”名其書齋正說明這一點。這種繼承于司馬遷以傳奇為史的“野史”觀,導致了作者在以詞存史時不避險陘,樂述奇異。
作為一代名臣和文宗,元好問“存史”的使命感十分強烈,他不僅自撰史志,還廣泛輯錄整理各類文獻以存金源百余年史料。《中州集》是他以詩存史的舉措。《中州集》的一部分為金詞總集《中州樂府》,元好問將金詞作為與金詩有同樣價值的歷史文獻和文體自身發展資料加以搜集、選編,其目的同樣是存史。在體例上,《中州樂府》同于《中州集》,每位作者名下均列小傳,敘其生平,論其文學。值得注意的是,小傳所記的人、事也多有奇特怪異的性質。就提供傳奇敘事空間這一點來看,小傳與詞序確有著類似的功用。
此外,元好問還有意識地利用各類文體的創作來紀乘存史。《續夷堅志》是以小說存史,紀時事之詩是以詩存史,所撰碑志銘記是以文存史,同樣,元好問也將詞視為“史”之載體。這種觀念促使他在創作中自覺地以詞來記錄他耳聞目睹的有意義的人和事,與其“野史”觀一致,這些記載往往呈現出濃重的傳奇色彩。元好問以傳奇為詞的存史性質還可從這類作品的寫作特征上得到證明。我們注意到,詞序中的這類傳奇故事多以史傳筆法出之。凡所涉之人,皆寫明姓什名誰、里籍家世等;凡所錄之事,皆記下事發地點,甲子月日等。人或怪異非常,事或荒誕不經,然在作者筆下皆寫得信而有征,言之不虛。這一點與魏晉以來的志怪傳奇小說如出一轍。如那首寫情侶殉情化荷的《摸魚兒·雙蕖怨》,其序曰:
泰和中,大名民家小兒女,有以私情不如意赴水者,官為蹤跡之,無見也。其后踏藕者得二尸水中,衣服仍可驗,其事乃白。是歲,此陂荷花開無不并蒂者。沁水梁國用時為錄事判官,為李用章內翰言如此。此曲以樂府雙蕖怨命篇,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清之瑞露,春動七情,韓偓《香奩集中》自敘語。故事時地清楚,人物名姓官職皆具,可謂言之鑿鑿,一派史家“實錄”風格。這種史筆為詞的作法清楚地表明了以詞存史觀念對于傳奇體詞創作的推動作用。
注釋:
①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三,《詞話叢編》,第3822頁。
② 元好問著,姚奠中主編,李正民增訂《元好問全集》(增訂本),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3頁。本文所引元好問作品皆出此書,不另加注。
③ 王兆鵬《神通之筆繪神奇之景——元好問〈水調歌頭·賦三門津〉》,《古典文學知識》1998年第2期。
④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三,《詞話叢編》,第4464
⑤ 詹石窗《論元好問詩詞的仙家情思》,《廈門教育學院學報》1999年第4期。
⑥ 宋無《續夷堅志跋》,《元好問全集》(增訂本),第1115頁。
⑦ 許昂霄《詞綜偶評》,《詞話叢編》,第1574頁。
⑧ 《東坡文集》卷五五,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652頁。
⑨ 杜牧《李賀集序》,吳在慶《杜牧集系年校注》,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774頁。
⑩ 郝經《陵川集》卷三五,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