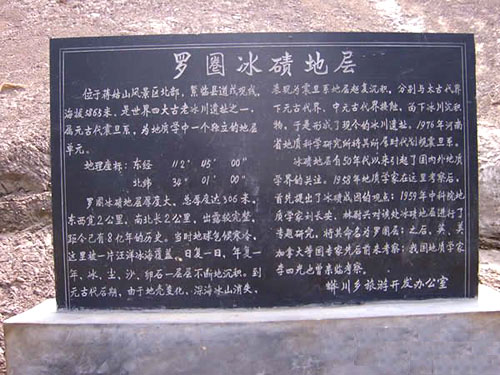-
沒有記錄!
水經注:三水匯流七里河(三)
2013/11/9 17:10:46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2008年5月21日,筆者和倉頭鄉水利站的溫金貴站長一起看禹王河。
正當油菜黃熟季節,山坡上和溝谷里,時見收割油菜的人忙碌著。出齊穗的麥子案板一樣平展展鋪向溝岔深處。這里是城市的后院,是我們衣食所出的最本初的地方。近期以來,這地方的山形地貌,一直處在迅速變幻之中。正如一個管水利的領導干部說的那樣:“我不關心水資源,今天看過,可能沒過幾天就沒有了。”
可是如果有一天小河溝都干涸了,大河還會存在嗎?
村村通公路纏著河道走,所幸坡上的植被多在恢復中。倉頭鄉地偏山遠,是一個省級貧困鄉。1970年代剃光山頭造梯田,植被遭到了毀滅性的損壞。一遇暴雨,泥沙俱下,河水哧溜就下去了。稍有旱情,塘干溝枯,吃水都困難。人們在大自然嚴酷的教訓中變得明智起來。退耕還田,植樹固坡。這個鄉莊園型果林成規模的已近萬畝。但上游植被還是很稀薄,沿岸山頭裸巖磊磊,村莊一貧如洗。
循著起伏不定的山路蜿蜒而上,直達高高聳起的嶺頭。山脊狹長,西北通往泛著紫藍的藥皇頂、五垛山。這是一道分水嶺,分開了北汝河與沙河流域。西南一路,山勢低淺,坡上有不連貫的小片樹林。這道南北走向的嶺脈,西邊滾坡水入禹王河,東邊歸大浪河。陽光明亮,空氣干燥。只有近水的地方,草木才青茂有顏色。幾年前,人們在寶豐與魯山交界的地方發現了鋁礦石,就有人開始放炮剝山,那些被挖開的地方,林木不保,黃金一樣的土層被掘成一二十米深的大坑,裸露出森森巖架。
在紅椿樹溝自然村,筆者采訪了57歲的村民高金泉。他說這道溝中住有110多口人,再往里去,自從山那邊開礦采煤,不下大雨溝里再也沒有水了。過村向下200米,左邊有條500米長的黑溝,山根出大泉,兩個三寸泵都抽不干。砌有十平方米泉池,供村里人吃用。
2009年4月10日,黃楝樹村的支部書記王杰在電話里告訴筆者,由于天旱數月,紅椿樹溝上下三四里七八個吃水井都干了,村民吃水跑4公里去鷹咀石西北坡和鐵山根兒,排隊接細小巖泉。從鷹咀石到豹子溝,這段河連陰天才有明水,雨過即干。瓦房莊自然村西500米,坡根有搟面杖粗一股山泉,修成2畝大的水塘,天旱這么狠,溢水仍不停往下流,引渠澆灌20畝菜園。到溝口,供瓦房莊自然村30多口人吃用,余水在村下沒入紅椿樹溝。河在后莊自然村折向左岸海拔278米的蜘蛛山。山根有常年泉溪,沿溝打四五個透水井,供150多口人吃用,下來800米,并入紅椿樹溝。河道躬起一個大灣,繞到黃楝樹自然村。村下有半畝大的攔河壩,剛建成時水深十多米,眼前淤剩一米多。后莊組200多口人沿河打井,吃溝里的潛水。河走S型折而南下,左岸上郭窯自然村有水濺溝注入。溪溝源于鋸齒嶺陽坡,水量與瓦房莊溪流不相上下。濺水大時,溝中都是稻田,村莊就叫稻田溝。現在上郭窯組的400多口人仍然吃這溝水。一半人家埋管接到屋,一半人家沿溝打井。去年冬天旱到現在,全村也就水濺溝澆了六七十畝麥地。
與水濺溝隔嶺并流的,還有一道山泉。泉源在稻田溝自然村后坡巖根處,是一股指頭粗的常年泉,供四五家喬姓村民飲用,到劉河自然村,匯入紅椿樹溝。紅椿樹溝自后莊自然村下明水動流,至劉河行政村,流幅已有兩米寬,無棧石過不到對岸。前些年河灘里種的都是楊樹,這兩年賣不上價,改種了桐樹。河水漸行漸小,到李窯行政村,瘦到一米多寬,腳脖深。村北有東溝來匯,溝中建有5畝大、3米深的三岔口小水庫。壩下百余米,又有6畝大、2米深的西溝小水庫。水自壩上溢流而下,行800米在禹王冢處歸入紅椿溝來水,始稱禹王河。過禹王冢不遠,左岸有井溝注入。水量是東溝的一半兒,上源在黑頭山。村民沿溝打井,澆種木耳。
大禹治水的腳蹤遍布黃河兩岸大江南北,已成神話。世間凡順天利民之人之事,漁樵閑話里都是美談。也無論地下考古,地上留痕,一代英雄美人總是等著下一代、下下一代的英雄美人來相知相認。唯有志存高遠情意浩蕩者,方可接過這歷史深處的大好意思,播火傳薪,成就新一代鮮亮亮的人情物意。大地上的一切文明,都是人心的流露。勞動不只是生存的手段,科技也不只是創造經濟效益的工具。有了美好的創意在里面,有了與大自然相諧的智性在里面,它才會有音樂舞蹈的姿彩。去年5月的禹王冢前,熱熱鬧鬧好幾里,是廟會,也是民間物資交流會。紅男綠女你來我往,喜盈盈地彌漫著現代生活氣息。堆積萬年的歷史傳說與人類往事,無論如何轟轟烈烈,都付與了斜陽流水。眉清目揚的今人和后人,才是文明發展的旨歸。愛護山川河流,立足于人類的長遠發展,讓千行百業都與自然與民心相和諧,開拓和發展都在大自然容與回環的序列里,興利于明艷鮮潔的民間,才不至于辱沒了自己的生命和子孫后代的承望吧。(曲令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