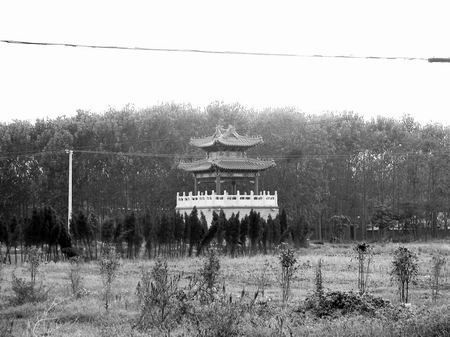龍?zhí)洞髰{谷躋
近日,本網(wǎng)從河南省旅游局網(wǎng)站獲悉,..[詳細]
濟源天壇峰構(gòu)
濟源天壇峰構(gòu)造地貌景觀 天壇峰位于..[詳細]
林州太行大峽
炎熱夏季,越來越多追求生活質(zhì)量的都..[詳細]
-
沒有記錄!
“風土吉壤三陵臺”系列之二 “梁孝繁華想廢臺”
2013/7/31 16:33:23 點擊數(shù): 【字體:大 中 小】
梁園與三陵臺的關(guān)系,被清代詩人賈開宗一句“梁孝繁華想廢臺”點破。而以往的考古發(fā)掘,也屢次見證了這一點。
1987年,原商丘縣文化館對三陵臺調(diào)查勘探,發(fā)現(xiàn)夯土,并采集到漢代板瓦等建筑構(gòu)件殘片。到了1994年,商丘文物工作者再次調(diào)查三陵臺,確認為古代陵墓。“到了1995年,中美聯(lián)合考古隊來時,他們帶了很多先進的儀器,本是為調(diào)查先商文化而來,在我們的強烈要求下,對三陵臺進行勘探,再次發(fā)現(xiàn)夯土層和漢代建筑構(gòu)件。”商丘市文物局副局長劉昭允先生道。2000年,河南省古建研究所副所長牛寧先生也曾到此調(diào)研,確認陵上瓦片是漢代東西。
2008年10月16日,三陵臺管委會主任黎德亮先生拿繩紋瓦給記者看:“這東西多,我原來撿到過一堆,有的在三個陵上隨意丟棄著,有的動手扒一扒就有。”
三陵臺既有漢代遺存,那么它真是“梁孝廢臺”嗎?
河南省科學院地理研究所遙感考古工作站,曾拍攝一組商丘古城和梁園遺跡的遙感照片,顯示出商丘古城1200平方公里范圍內(nèi)地表、地下的影像,其中有三條鋸齒狀遺跡較為突出,長約140公里。鋸齒狀遺跡每段折線約為八十米,寬數(shù)米。遺跡附近,還發(fā)現(xiàn)有七八處較大的村落遺址。“這種規(guī)模宏偉的遺跡,專家們認為很可能與西漢梁園遺跡有關(guān)系。”商丘資深文物專家閻根齊先生分析道。
梁園,《辭海》中釋道:“即菟園,漢代梁孝王劉武所造,也叫梁苑。故址在今商丘市東。梁孝王好賓客,司馬相如、枚乘等辭賦家皆曾延居園中,因而有名。杜甫《寄李十二白》詩:‘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李白《贈王判官詩》:‘荊門倒屈宋,梁園傾鄒枚。’”
梁園名氣很大,不僅是作為園囿的實體存在,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分量,以至于成為千年以來重要文學符號。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綱要》中稱:“天下文學之盛,當時蓋未有如梁者也。”這是漢代。到了唐宋,李白、杜甫、高適、岑參、蘇軾、蘇轍等,都來過此處,它成了文學家筆下夢幻之地。法國美學家丹納認為:“藝術(shù)家本身連同他產(chǎn)生的全部作品,不是孤立的,有一個包括藝術(shù)家在內(nèi)的整體,比藝術(shù)家更廣大,就是他所隸屬的同時同地的藝術(shù)流派或藝術(shù)家家族。”梁園文化即是孕育了一個文學流派、一個藝術(shù)家家族的夢幻家園。
《中國文學史》上又稱,“給予漢初文學發(fā)展以巨大推動力的人,首推梁園的建造者梁孝王劉武。”
梁園到底是何等所在,以致千年后仍享大名?它因何而建?三陵臺又如何成為梁孝“廢臺”的呢?
“自我膨脹”建梁園
“漢代睢陽城是疊加于宋國都城之上的,城門名字還沿用了宋國都城之名。城之長寬史書記載不一,有城方13里、12里、27里、70里之說。能夠肯定的是,它作為梁國都城,是當時的名城大邑。梁孝王劉武治梁之時,是梁國最盛時期。”商丘市梁園區(qū)文物辦主任楊亞民先生說。
劉武是漢高祖劉邦之孫、漢文帝之子、漢景帝的親弟弟,他和景帝都是竇太后所生。他初為淮陽王,改封梁王,當時梁國疆界南起今安徽太和北,北至古黃河與趙國為鄰,西到高陽(今杞縣西南),東與泰山郡、魯國接壤。“四十余城,皆多大縣,居天下膏腴之地”,地位巨重要。梁國可以“扦齊趙拒吳楚”,也就是說,劉武作為皇帝嫡系,是要威懾漢代九個同姓王國中“有想法者”。
梁國經(jīng)濟極發(fā)達,全國有名。絲絹是皇室貢品,冶鐵技術(shù)發(fā)展也很快。當時全國邊遠地區(qū)每平方公里不足一人,梁國每平方公里則100余人,是全國人口最密集區(qū)域,總?cè)丝谟?50萬人,“天下戶口最盛”。
劉武治梁,是要威懾別的王國。到了“七國之亂”時,劉武和梁國地位果然突出,“如果打下梁國,一過洛陽,叛軍就直接打到西安。但梁國滅叛軍的人數(shù),與中央軍隊半對半。撼梁國難,漢室才無恙。這功勞可就大了。”劉昭允先生說。
立此大功,劉武出入“得賜天子旌旗,出入千乘萬騎”,與皇帝一樣,出殿言“蹈”,入宮稱“警”。到了京城,“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與游獵”。睢陽城內(nèi),珠寶玉器比京城還多。
哥哥寵老媽縱,劉武本身又有能力,這種“銜著金湯勺出生”的幸運兒,沒法不自我膨脹。他在睢陽城筑梁園,搞到“方三百余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冶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于平臺三十余里”。規(guī)模與哥哥的上林苑不相上下。在當時,除帝王外,大貴族擁有私人園林的極少見。劉武把園林建于郊野之地,其實還帶有擴張地盤、開拓生產(chǎn)的目的。
這園子,具體是何模樣呢?
它集離宮、亭臺、山水、奇花異草、珍禽異獸、陵園為一體,是游獵、出獵、娛樂等多功能園囿。晉葛洪《西京雜記》中說:“作耀華之宮,筑菟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起龍囿,又有雁池,池間有鶴州,鳧渚。其諸宮觀相連,綿延數(shù)十里。奇果異樹,珍禽怪獸畢備。”《太平御覽》云:“梁孝王有修竹園,園中竹木天下之選集。諸方游士各為賦,故館有鄒枚之號……又有雁鶩池,周回四里,亦梁王所鑿。又有清冷池,有鉤臺,謂之清冷臺。”梁園模樣,約略可見。
當時它已很有名氣,估計夠得上“國家五A級景區(qū)”。枚乘寫《梁王菟園賦》中說:“于是晚春早夏,邯鄲、襄國,易、涿容麗人及燕汾之游子,相予雜還而往焉。”人氣這么盛,如果賣門票收入也不少。
梁園中的臺、觀、山、巖、囿、池,是空間的疊加,梁園主人劉武從一處走向另一處,穿越了不同體量與風格的空間。這是組合型空間之魅力,它制造了跨越時空的幻覺。為銜接這些龐大的組合空間,“復道”——一種亭式長廊被打造成梁園迷宮的結(jié)構(gòu)基線,復道的無限延展,反復重現(xiàn)著梁園迷宮的特性。
梁園中臺觀建得很多,這不是梁王首創(chuàng)。“筑臺風氣自文王的靈臺、衛(wèi)宣公的新臺、秦始皇的瑯笽臺以來,歷代不絕。”平地起臺,構(gòu)筑三維空間,以滿足古人與上天“溝通”的愿望。梁園臺觀遺存至今的還有清涼臺、三陵臺、平臺等。劉武在地處平原的豫東,在梁園內(nèi)多處筑臺,也是大工程,為省事起見,他一定會選取地勢高的地方。漢代三陵臺臺基已存,借助原有臺基,于其上筑臺成景,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不知是不是梁園遺風,商丘自茲以后盛行“七臺八景”之說,直至清代,包括商丘所屬各縣,都有一套自己的說詞。
商丘“七臺八景”之臺,往往是指臺基固堆而言,大多是古人類留下的文化遺跡,人類為生存擇高而居,吃剩食物、用過東西鋪在地上,地面逐年加高,便成臺地。春秋后貴族墓地大規(guī)模封土,墓上封土稱“墳”,大的固堆稱“冢”,都經(jīng)層層夯打。到了漢代,臺地上往往成為家族墓地,東漢之后,佛教傳入中國,寺院往往建在這些高岡臺地上。“所以至今所能見到的豫東一帶的土固堆,凡稱臺,不是古代文化遺址,就是古代寺廟基址,或是春秋戰(zhàn)國墓葬所在。”劉昭允先生認為。而土固堆稍平坦一些的就稱為岡、丘了。商丘是天下五名丘之一,這些丘,最早是古人類居住地,明代以后,變成了人們追根懷舊的古跡。
具體到三陵臺的演變,它最初是豫東人擇高而居之所,到了春秋戰(zhàn)國,變成宋國貴族墓地。到了漢代,被劉武圈進自己園囿內(nèi),因地制宜,于其上筑成臺觀(現(xiàn)在依然能找到板瓦等漢代建筑構(gòu)件殘片)。這是一個合理演變過程。
“天下文學它最盛”
劉武愛才,喜風雅,延攬?zhí)煜氯瞬牛?ldquo;豪俊之士靡集”。許多人辭去朝廷及其他諸侯國官職,到梁園“從梁王游”。其中最有名氣的,當數(shù)司馬相如、枚乘、鄒陽、莊忌等。
枚乘、鄒陽、莊忌原為吳王劉濞門下,力勸吳王不要謀反,吳王不聽,遂奔梁國。吳王發(fā)動“七國之亂”,枚乘又寫信諫吳王,力阻謀反,枚乘因此名震天下。“七國之亂”平定后,枚乘托病辭了漢景帝的官,仍回梁國做梁孝王文學侍從。
“枚乘為辭賦大家,以《諫吳王書》、《七發(fā)》、《梁王菟園賦》等成為梁園及整個西漢文壇的領(lǐng)袖。他寫于梁園的《七發(fā)》,更是漢賦由楚辭演變而來至成熟期的代表之作,標志著漢代散體大賦體制的最后形成。”劉昭允先生說。
司馬相如,先在朝中任漢景帝武騎常侍,景帝不喜辭賦,司馬相如頗不如意,到梁國追隨劉武。他客居梁國數(shù)年,給梁園留下了文辭華麗、結(jié)構(gòu)雄偉的《子虛賦》,這是漢賦代表作。據(jù)說劉武還把一張傳世古琴“綠綺”贈給了他。劉武死后,相如又歸蜀,估計就是彈著這張琴,唱著《鳳求凰》,拐走了卓文君。
正因為有枚乘、司馬相如等人加盟,一時間形成了蔚為大觀的梁園作家群,梁園辭賦開了漢代大賦先聲,梁園也為西漢文壇輸送了大批人才。
《西京雜記》中記錄梁園作家們聚會場面:“梁孝王游于忘憂之館,集諸游士,各使為賦。枚乘作《柳賦》,路喬如作《鶴賦》,公孫詭為《文鹿賦》,鄒陽為《酒賦》,公孫乘為《月賦》,羊勝為《屏風賦》。韓安國作《幾賦》不成,鄒陽代之。韓罰酒三升。枚乘、路喬如各得賜絹五匹。”可以想見當時諸作家PK,互動甚強,因而佳作迭出。因此,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綱要》中稱:“天下文學之盛,當時蓋未有如梁者也。”
梁園作家群共同打造的梁園文化奇異浪漫,既有中原大國的弘闊氣度,又兼具東方齊文化“奇譎多氣”與南方楚文化“浪漫瑰麗”,這自然和作家們來自全國各地有關(guān)系。
劉武此舉,一是本身憐才好士,二是有效仿“孟嘗君養(yǎng)士”之意。這是文壇盛事,也是劉武政治上的敗筆。他最終還是因“養(yǎng)士、求嗣、謀反”幾件事為景帝猜忌,暴病身亡,史稱“中熱疾而卒”。死得詭異,連他母親竇太后都懷疑他被景帝所害,傷心得吃不下飯。
梁園文化成就一時無二,因此后世文人每逢至此,都感慨不已。
唐代大詩人李白在梁園留住10年不忍離去。李白有《梁園吟》一詩:“我浮黃河去京闕,掛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仿古始及平臺間。平臺為客憂思多,對酒遂作《梁園歌》。梁王宮闕今安在?枚馬先歸不相待。舞影歌聲散綠池,空余汴水東流海。”他所見梁園已敗落,宮闕都沒了。
到了北宋,蘇轍再次見識了梁園的蕭條,他給蘇軾寫信:“梁園久蕪沒,何以奉君游。故城已耕稼,臺觀皆荒丘……”成了荒丘的臺觀中,應有三陵臺。
到了清代賈開宗寫的《三陵臺》一詩中,“宋襄統(tǒng)系思遺冢,梁孝繁華想廢臺。”一個“廢”字,“啥都別說了,眼淚嘩嘩的”。
與那些朝代更迭之中一火焚之的曠世名園不同,梁園是慢慢耗散的一個過程,它的殘與頹緩慢出現(xiàn)。實體梁園消失了,梁園建筑的碎片——臺、觀、山、巖、囿、池,仍像夢境一樣浮現(xiàn)在此后的文學史上,后世文人對它有著“失樂園”的想象。很少有一座花園像它這樣,承載如此豐厚的文化寓意。它生前是劉武私人享樂的喜劇,死后轉(zhuǎn)向無盡的文化正劇。它遺落的灰燼,比時間更長久。而文化,比歲月更長久。
曾為梁園一景的三陵臺,也因梁園而不朽。
當年梁孝王劉武自我膨脹,在睢陽城建造集離宮、亭臺、山水、奇花異草、珍禽異獸、陵園為一體的梁園,規(guī)模堪與哥哥漢景帝的上林苑媲美。三陵臺作為梁園一景,也因梁園而不朽。圖為今三陵臺一景。(盛夏)【原標題:“風土吉壤三陵臺”系列之二 “梁孝繁華想廢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