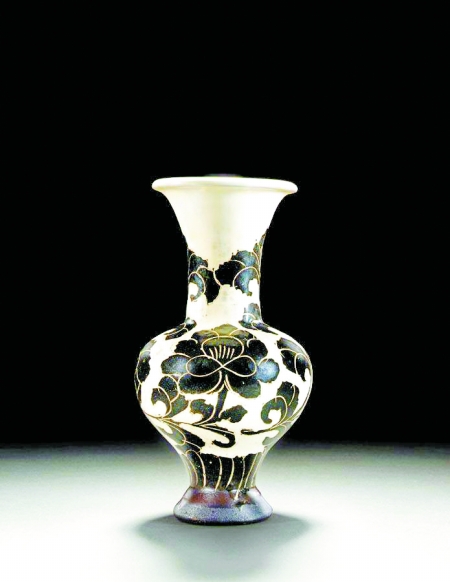-
沒有記錄!
鄧淑蘋:從清宮舊藏看子岡種種謎(2)
2013/11/6 10:51:45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蘇周刊:要研究陸子岡,必然研究明清時期我國玉雕的發(fā)展史。您對這段歷史是怎樣劃分的?
鄧淑蘋:我覺得,明清的500多年(1368-1911年)時間里,我國的玉雕至少分四個發(fā)展階段:
一是明早中期,約1560年之前,這是接續(xù)元代玉雕傳統(tǒng)的時期。13世紀元代蒙古兵西征,帶回了中亞地區(qū)的玉工,將他們安置在大都(今北京)的城南,成為元、明時期的官匠戶,北方的“京作”玉器也由此逐漸形成;
二是明中晚期至清早期。隨著江南經濟的發(fā)展,書畫及各類工藝美術蓬勃發(fā)展。在文人、富商的扶持下,我國的玉雕更加精雅細致,以蘇州為中心的“Suzhou school”玉雕形成。“Suzhou school”是西方人的稱法,我是1981年在美國底特律開會時第一次聽到的。從字面看,它是“蘇州學校”的意思,實際內涵就是“蘇幫”、“蘇作”;
三是清中期。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起,清朝政府直接控制昆侖山玉料的開采,玉雕空前繁榮;對西南的開發(fā)也導致緬甸翠玉的輸入;
四是清朝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口通商后。由于鴉片戰(zhàn)爭等因素,清朝國力大衰,宮中造辦處玉雕業(yè)務萎縮,但民間交易卻更見繁榮,特別是興起了所謂“洋莊”生意,通過上海,將蘇州、揚州的玉器大量外銷歐美。這一時期,翡翠、寶石、金工都加入玉雕制作,各種吉祥圖案如蝙蝠(福)、壽桃(壽)、靈芝(如意)、竹(高風亮節(jié))紛紛運用;還出現了玉雕“翠玉白菜”,以白菜與螽斯象征清清白白、多子多孫……都促成了玉雕行業(yè)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持續(xù)繁榮。
蘇周刊:您上面提到,玉雕有“京作”和“蘇作”之分。這兩種制作技藝,有什么不同點?
鄧淑蘋:“京作”就是北方工,以北京為中心,大氣、質樸為其特征;“蘇作”是南方工,以蘇州為中心,以靈空、飄逸、精細著稱。
蘇周刊:業(yè)界對蘇作玉雕有著怎樣的評價?
鄧淑蘋:一般都認為蘇作玉雕以“精巧雅致”為特征,老少咸宜,雅俗共賞。上面已提到,在二十世紀后半葉,西方藝術史界以“Suzhou school”一詞專指明代晚期在江南形成的講究文人清雅品味的藝術風尚。這一名詞不只指玉雕,也泛稱當時各類以文人書房用品為主的工藝。
藝術史界通常稱明晚期以蘇州(當時又稱“吳門”或“吳中”)為核心的書畫傳統(tǒng)為“吳派(Wu school)”,工藝傳統(tǒng)為“蘇派(Suzhou school)”。前者是文人畫派,后者是合乎文人品位的工藝流派。
陸子岡謎團越滾越大
蘇周刊:根據您掌握的資料,陸子岡是怎樣一個人?
鄧淑蘋:他又寫作“陸子剛”,生卒年份不詳,是明代中后期蘇州府太倉州的玉工,活躍于十六世紀后半葉。晚明的多位江南文人都曾在著作中記錄有關陸子岡雕玉的事跡。另外,明代崇禎十五年(1642年)出版的《太倉州志》也記載。再后來記載越來越多,各種說法層出不窮。
蘇周刊:能否按時間順序具體說說有關陸子岡的記載?
鄧淑蘋:我覺得可以分五個時間段。
第一個時間段是16世紀晚期,主要是與陸子岡同時代的文人的著述。
如王世貞(1526-1590年)的《觚不觚錄》:“今吾吳中陸子剛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銀,皆比常價再倍,而其人有與縉紳坐者。近聞此好流入宮掖(即宮廷),其勢尚未己也”;
高廉(生卒年不詳)《遵生八箋》(刊印于萬歷十九年,即1591年)中的《燕閑清賞箋》:“水注,又見吳中陸子岡制白玉辟邪,中空貯水,上嵌青綠石片,法古舊形,滑熱可愛。有玉蟾蜍注,擬寶晉齋舊式者。水中丞:近有陸琢玉水中丞,其碾獸面錦地,與古尊罍同,亦佳器也。印色池,有陸子岡做周身連蓋滾螭白玉印池,工致侔古,今多效制”;
徐渭(1521—1593年)《詠水仙》:“略有風情陳妙常,絕無煙火杜蘭香。昆吾鋒盡終難似,愁殺蘇州陸子剛”;
陳繼儒(1558—1639年)《妮古錄》記錄了1595年的事:“乙未十月四日,于吳伯度家,見百乳白玉觶,觶蓋有環(huán)貫于把手上,凡十三連環(huán),吳門陸子(指陸子岡)所制”。
蘇周刊:分析16世紀晚期與陸子岡同時代文人的著述,有哪些特點?
鄧淑蘋:第一是陸氏的名字有兩種寫法,多處都記載為“陸子剛”,高廉則寫作“陸子岡”。
二,陸子岡制作的玉器有辟邪形水注、蟾蜍形水注、獸面錦地水中丞(也就是“水盛”)、周身連蓋滾螭白玉印池、百乳白玉觶。除了這五件被具體描述器形、紋飾的器類外,還有詩夸稱陸子岡雕玉擅于掌握水仙花的神韻。
高廉形容陸氏制作的“獸面錦地水中丞”時用了“碾”字,流露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陸子岡雕玉主要還是用砣具配合各種解玉砂、磨玉砂完成的。
徐渭的詩句“昆吾鋒盡終難似”,意思似乎是指陸氏用“昆吾刀”刻玉。“昆吾刀”一詞早期僅出現于漢末《海內十洲記》之類傳說色彩濃厚的史料中,明末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認為“昆吾石”可能是金剛石。徐渭的詩可能暗示,當時已有人認為陸氏雕玉的過程中,用了某種特別鋒利的刀子直接刻玉。
蘇周刊:第二、第三個時間段對陸子岡是如何記載的?
鄧淑蘋:第二個時間段是17世紀中期的崇禎十五年(1642年)。《太倉州志卷五·物產》紀錄了陸子岡的用刀:“雕玉器,凡玉器類砂碾,五十年前州人有陸子剛者,用刀雕刻,遂擅絕今。所遺玉簪,價一枝值五六十金。子剛死,技亦不傳。”
第三個時間段是民國初期的1915年。李狷厓的《中國藝術家征略》稱:“陸子剛碾玉妙手,造水仙簪,玲瓏奇巧,花莖細如毫發(fā)。”這里將徐渭《詠水仙》的絕句,訛寫成“詠水仙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