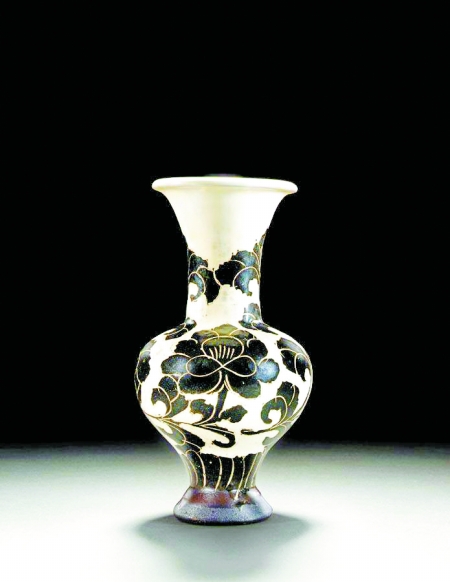-
沒有記錄!
鄧淑蘋:從清宮舊藏看子岡種種謎(3)
2013/11/6 10:51:45 點擊數(shù): 【字體:大 中 小】
蘇周刊:第四個時間段是什么時候?又是怎樣記載的?
鄧淑蘋:這是1942年,趙汝珍的《古玩指南》記載:“陸子剛,明時吳中人也。選玉作器迥異恒流,與士大夫抗禮,非尋常玉工所可比擬。凡所作器,必先選玉,無論有微瑕者,概置不用,即稍帶玉性者,亦棄而不治。所用之料,或白或青,必純潔無疵,通體皆混然一色。其所作之畫,片布皆近情理。即他人不經(jīng)意處,亦經(jīng)營慘淡以為之。比如刻一新月,則必上弦而偏右。刻一曉月,則必下弦而偏左。其詳人所略有如此者。故凡系出自子剛手之畫片,雖吹毛求之,亦無一疵可指也。其所制器,皆均平如一,無或深或淺之處。而所刻之字均系陽文。從來玉上刻文,陰文者多,陽文者少,以陽文難刻也。子剛則取其難。足見長于術(shù)也,且筆意圓轉(zhuǎn)與寫于紙上者,絲毫不爽,蓋子剛書畫作工,皆出己手。子剛不惟善于治玉,亦且以書畫名家也。”
這段話對陸子岡選玉、雕玉進(jìn)行了細(xì)致的介紹,而且還夸獎他是個書畫好手。
蘇周刊:第五個時間段是什么時候?記載了什么?
鄧淑蘋:應(yīng)該從1997年之前就開始了,直到現(xiàn)在。主要是大陸的出版品進(jìn)行的記載。如葉寅生的《陸子剛和子剛玉》(《珠寶科技》1997年第2期)稱:“皇帝叫子岡雕玉茶壺,交代他不許刻自己的名款。子岡將自己的名字偷刻得很淺,后來被皇帝發(fā)現(xiàn)而被斬首”;
后來在網(wǎng)絡(luò)上神奇?zhèn)髡f越來越多,相互傳抄轉(zhuǎn)載,有的也出現(xiàn)在當(dāng)下某些出版品上。如:“清代宮中的如意館雕琢很多帶有‘子岡’款的玉墜,是為了紀(jì)念他”;
“明穆宗命陸子剛在玉扳指上雕百駿圖。他僅用幾天時間完成了,在小小的玉扳指上刻出高山疊巒的氣氛和一個大開的城門,而馬只雕了三匹,一匹馳騁城內(nèi),一匹正向城門飛奔,一匹剛從山谷間露出馬頭。僅僅如此卻給人以藏有馬匹無數(shù)奔騰欲出之感,他以虛擬的手法表達(dá)了百駿之意,妙不可言。自此,他的玉雕便成了皇室的專利品,世間幾乎絕技。”
蘇周刊:縱觀這五個時間段的記載,您有什么看法?
鄧淑蘋:我覺得,十六世紀(jì)晚期至今,400多年來人們對陸子岡的記載越來越細(xì),陸子岡故事一步步發(fā)展,陸氏本人被越傳越玄,謎團(tuán)越滾越大。
運(yùn)用立體顯微鏡帶來的新發(fā)現(xiàn)
蘇周刊:為什么說陸子岡被越傳越玄呢?
鄧淑蘋:你看,第三個時間段贊美陸子岡所雕的水仙簪花莖細(xì)如毫發(fā);第四個時間段說陸子岡也是書畫家,他一定只選白玉,只雕陽文,構(gòu)圖非常用心,作品器表非常平整,但反而沒有提到用刀刻玉;最后被塑造成不畏皇權(quán)、因為堅持理念而被殺的悲劇英雄,所以連清代宮中都為紀(jì)念他而制作了許多子岡牌;再變成虛擬的雕琢手法的發(fā)明者,以三匹馬表現(xiàn)奔騰欲出的百駿。
這些說法中,除了與他同時的文人所記是真相外,其他的可能都不是真的。
蘇周刊:直到今天,圍繞陸子岡的謎團(tuán)仍然還有許多,核心謎團(tuán)有哪些?
鄧淑蘋:我認(rèn)為,核心謎團(tuán)包括:他到底是不是直接用刀刻玉?目前傳世大量刻有“子岡款”的玉器中,到底哪些是陸子岡親自雕琢的作品?
蘇周刊:您前面提到,1981年曾發(fā)表過有關(guān)的中文和英文論文,里面有沒有涉及這些謎團(tuán)?
鄧淑蘋:涉及了一部分。論文里主要提出了三個觀點:一,陸子岡的作品主要是明朝中晚期江南地區(qū)文人書齋所用各色文具,以及發(fā)簪、小佩等;二,在雕琢器形、紋飾以及今草體(草書的一種、也稱“小草”)陽文詩句時,用傳統(tǒng)的砣具配合解玉砂完成;三,在雕琢篆體名款時,直接用刀具刻成。
蘇周刊:聽說您最近又有新的觀點?
鄧淑蘋:是的。這是因為,近年我們博物院增添了立體顯微鏡。有了這一先進(jìn)“武器”,我對部分“子剛”款玉器進(jìn)行了仔細(xì)的觀察,同時也跟熟悉篆刻、雕玉工藝的同事討論,結(jié)果有了意外的發(fā)現(xiàn)。
蘇周刊:目前子岡款玉器大約有多少件?
鄧淑蘋:我在2011年12月的《故宮文物月刊》發(fā)表專文《探索“子剛”——晚明江南玉雕謎團(tuán)的再思》,將兩岸故宮已披露子岡款玉器列表統(tǒng)計過,共約有44件,其中八九成屬清宮舊藏。民間收藏以曾屬香港北山堂所藏、后來捐贈給香港中文大學(xué)的一件圓盒最著名,它上面刻有“嘉靖辛酉陸子剛制”八個字,被公認(rèn)是陸子岡的真跡。
目前考古出土的唯一一件“子剛”款玉器是北京市海淀區(qū)清代黑舍里氏墓出土的明代“子剛”款玉樽,它高10.5厘米,口徑5.8厘米,這也是公認(rèn)的陸子岡的真跡。
2002年,北京市政府頗為用心地出版了一套《北京文物精粹大系》,公布了這件玉樽的局部刻款,提供我們作對比研究。
蘇周刊:通過立體顯微鏡觀測,您對陸子岡在作品上刻下自己的名款,以及他用刀來刻玉的說法,有什么結(jié)論?
鄧淑蘋:陸子岡其實也是用傳統(tǒng)的砣具進(jìn)行雕琢,但是因為十六世紀(jì)的江南地區(qū),在文彭、何震等人的倡導(dǎo)下,開創(chuàng)了特殊的篆刻風(fēng)氣,而一般被文人用作印材的,都是摩氏硬度約二三度,以葉臘石為主要成分的壽山、田黃、青田等玉石,所以可以用雕刀在上面留下錯落有致、神采風(fēng)骨俱佳的書體。聰明的陸子岡卻用砣具模仿出以刀治印的“刀味兒”。當(dāng)時的文人不知道這個秘密,陸子岡也不說穿,于是就傳出他用刀刻玉的說法了。到后來他去世了,沒有徒弟,這技藝也就失傳了。在陸子岡去世后約五十年,修地方志的官吏將此說法正式記載在《太倉州志》,自此就迷惑了愛玉族四個世紀(jì)。
“子岡雕不如今天的玉雕”
蘇周刊:您用立體顯微鏡觀察了幾件藏品?您認(rèn)為它們都是陸子岡的作品嗎?
鄧淑蘋:我觀察了七件。今年六月我曾赴北京演講,就向首都博物館申請入庫房檢視黑舍里墓出土的玉樽,很受啟發(fā)。綜合我2011年時的考慮,我的初步結(jié)論是:七件中有六件可能是陸子岡在不同年齡時的作品。它們都是明代晚期江南風(fēng)格文房用品,如水盛、香爐、印泥盒等,所刻的篆體名款的筆畫都留著銼刀痕,另外一件臂擱雖然玉質(zhì)好,雕工也美,但篆體名款的筆畫上沒有銼刀痕,目前暫時將它排除在子岡真跡的范疇之外。
蘇周刊:陸子岡被傳得如此沸沸揚(yáng)揚(yáng),他的玉雕水平是否超過今人?
鄧淑蘋:應(yīng)該這么說,子岡雕不如“乾隆工”,“乾隆工”又不如今天的玉雕。
蘇周刊:“乾隆工”是怎樣的一種風(fēng)格的玉雕?
鄧淑蘋:字面上講,“乾隆工”應(yīng)該是指乾隆時期,也就是十八世紀(jì)中后期,由皇家所提倡與主導(dǎo)的玉雕風(fēng)格,這應(yīng)該是“乾隆工”的正確定義。
乾隆皇帝并不喜歡“層次多、琢工細(xì)、精而薄”的玉雕,他常嚴(yán)厲批評當(dāng)時蘇州玉工創(chuàng)造的這種“新樣”非常“纖俗、華囂、弄奇、繁縟”,還全力設(shè)法引導(dǎo)雕琢敦厚純樸、有文化內(nèi)涵的“仿古風(fēng)格”。
蘇周刊:為什么會出現(xiàn)子岡玉不如乾隆工、乾隆工又不如今天玉雕的現(xiàn)象?
鄧淑蘋:因為時間越晚,工具越先進(jìn),可以雕出更好的玉器。另外,一位雕玉大師的養(yǎng)成,必然有其一定的職業(yè)生涯,所以世上應(yīng)該存在陸子岡比較早期的、還不夠成熟的作品,這類作品跟現(xiàn)在最高端的玉雕大師的作品就更不好比了。
也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現(xiàn)在的玉雕從業(yè)人員是幸福的,想雕什么就雕什么,自由度很大,可以借助先進(jìn)的機(jī)器創(chuàng)作,很好地發(fā)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成就自己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