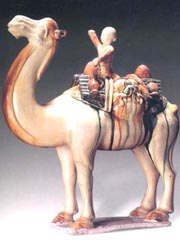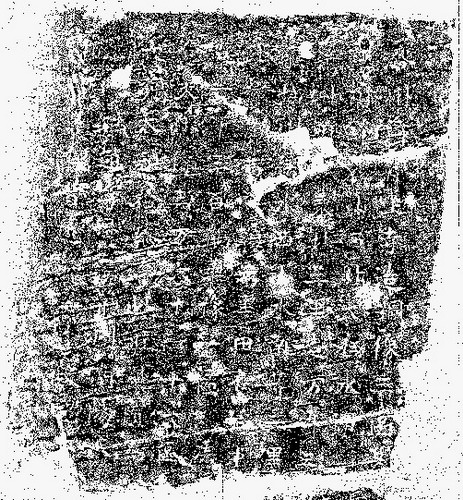- 1、洛陽水席八中件
- 2、洛陽水席四大件
- 3、洛陽水席四掃尾菜
- 4、三彩工藝流程
- 5、洛陽水席前八品制作
- 6、【洛陽非遺】河洛大鼓
- 7、洛陽水席招牌菜的制作
- 8、洛陽宮燈
-
沒有記錄!
- 1、河洛大鼓的傳承方式
- 2、洛陽水席八中件
- 3、洛陽水席四大件
- 4、洛陽水席四掃尾菜
- 5、三彩工藝流程
- 6、洛陽水席前八品制作
- 7、【洛陽非遺】河洛大鼓
- 8、洛陽水席招牌菜的制作
洛陽水泉石窟的摩崖碑記
2014/1/6 10:26:52 點擊數(shù): 【字體:大 中 小】
水泉石窟是洛陽地區(qū)石窟群中較為重要的北魏佛教洞窟。位于該洞窟外南側(cè)崖壁上方的摩崖碑記,是唯一記載北魏洛陽地區(qū)造像情況的碑記,內(nèi)容豐富,堪稱“洛陽造像記”。然而由于該碑漫漶殘泐,一些關(guān)鍵字難以辨認(rèn),致使其珍貴的價值未得到充分認(rèn)識。
摩崖碑記為通體碑,共有20行文字,推測有805字。因巖體滑動,已殘為兩段,上段連同雙龍碑首移向左邊,使得碑文上下段錯行。此前一些學(xué)者付出了許多努力,能辨認(rèn)的字?jǐn)?shù)也逐漸增多。目前注錄較為完整的是劉景龍、趙會軍的《偃師水泉石窟·碑刻題記》,共計432字。筆者對照原碑、拓片并參考有關(guān)學(xué)者的著述、歷史典籍等,經(jīng)過認(rèn)真辨析,使能夠明確辨認(rèn)的字?jǐn)?shù)增加到537個。由于對碑記注錄有較大的進(jìn)展,原先一些似是而非的字得以確認(rèn),使整篇文字遂能連貫地加以分析理解,進(jìn)而解決了一些重要問題:
一是確定了石窟主曇覆的身世。此前,很多研究者對碑記中極為重要的第九行開頭幾句,僅注錄出“□□□趙□□□□州南陽人”,所以無法完整理解這一段文字。雖有學(xué)者指出碑記中的“趙”是石窟主比丘曇覆的俗姓,但只是推測。通過此次努力,將其辨認(rèn)為:“曇覆,姓趙,字得覆。荊州南陽人。□趙靈王之苗胄焉。其太曾始祖,寶廟神區(qū),龍云自蔭,于是連和重疊,封襲數(shù)人,百官諸方。”這樣,基本弄清了曇覆的身世:俗姓趙,字得覆。他的太曾祖就熱衷于建廟造像,因而福被后代,以至“封襲數(shù)人,百官諸方”。曇覆在北魏太和十三年就曾在洛陽一帶造過佛像并主持或建造過佛寺,發(fā)愿讓五道受苦者“普同受樂”。
二是基本確定了洞窟造像年代。此前,碑記只辨認(rèn)出“大魏太和拾□年比丘曇覆為□□并□□廟”。學(xué)術(shù)界據(jù)此對水泉石窟開鑿年代爭議頗多。一說石窟開鑿于孝文帝十幾年,進(jìn)而推斷石窟正壁兩尊主佛也為曇覆所造。另一說根據(jù)洞窟第八龕題記及造像藝術(shù)風(fēng)格,認(rèn)為洞窟開鑿于北魏晚期,正壁兩尊主佛是曇覆之后的他人所建造。水泉石窟最早開鑿的佛龕是“石窟主曇覆敬念造”的第八龕。筆者通過辨認(rèn),可以肯定碑文為:“大魏太和拾叅年比丘曇覆為□□并□□廟”。聯(lián)系上下文理解,可知這段碑文是曇覆追憶他造像和造廟的時間,而非此洞窟開鑿的時間。曇覆造像是在“皇運(yùn)徙居,爵倫更迭”的社會背景下,對現(xiàn)實感到絕望,“歸山自靜”期間開鑿的。據(jù)此可推斷,曇覆造像當(dāng)在孝武帝至孝明帝期間。
三是記錄了當(dāng)時洛陽地區(qū)各種題材的造像。碑記較為詳細(xì)地記載了分布在石窟、佛堂、浮屠塔、露天摩崖等處的銅像、鍍金像、石像等各類造像,更為關(guān)鍵的是,記載的各種題材造像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流行于當(dāng)時洛陽地區(qū)的各種宗派信仰。比如萬佛與千佛造像,這是石窟造像中較為普遍的內(nèi)容,邑社造像對此更為熱衷。一千五百龍華像則源于彌勒下生信仰,據(jù)記載彌勒菩薩將于佛陀入滅后五十七億六千萬年,下生于人間,在龍華樹下成道、說法度眾。千佛天宮這類造像敘述了彌勒上生此天時之情景,這是往生彌陀凈土之外的另一種往生思想。五百華勝佛的造像取材于《佛說佛名經(jīng)》,五百華勝佛信仰流行于當(dāng)時社會上流階層。十六王子像是佛教造像中少見的一種題材,是佛出家時,在好城有十六位王子,皆隨佛一起出家為沙彌,以后十六王子宣講《法華經(jīng)》,皆成佛道。這些記載從側(cè)面反映出北魏洛陽地區(qū)佛教造像種類繁多,佛教發(fā)展空前繁盛的史實,對我們?nèi)媪私夥鸾淘谥性貐^(qū)的發(fā)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證據(jù)。
四是記載了佛輦輿與行像。碑記說:“洛州阿育王寺造銅像三區(qū),各長三尺,金度色,并佛輦輿。”佛輦輿是一種至高的宗教禮儀,制造并使用佛輦輿足以證明阿育王寺在當(dāng)時眾多寺院中的顯赫地位。佛輦輿是用來承載移動的佛像的,這種可移動的佛像(也叫行像)一般用旃檀香木和紫銅制成,是一種珍貴的造像。阿育王寺里造高大且鍍金的銅佛像,這說明它可能和皇室間有密切的關(guān)系。
五是印證了洛陽阿育王寺的存在。由于漫漶,對題記開頭幾句的辨認(rèn)歧義頗多。劉景龍、趙會軍《偃師水泉石窟·碑刻題記》認(rèn)為是:“洛州□□上寺造銅像三區(qū)□□長三尺金度色并佛□輿。造石窟一區(qū)中置一萬佛造□千五百龍華像一區(qū)。”張總《十六王子像小記》著錄為:“洛州河南王寺造銅像三區(qū)各長三尺金嚴(yán)色并佛囗庫造石窟一區(qū)中置一萬佛造一千五百龍華像一區(qū)。”這段話總共四十一個字,就出現(xiàn)了四處不同,其中最關(guān)鍵的是把阿育王寺誤認(rèn)為其他寺廟。
最早記載洛陽阿育王寺的是北齊魏收的《魏書·釋老志》:“于后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于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阿育王寺,蓋成其遺跡焉。”然而自此以后,有關(guān)洛陽阿育王寺的史料闕如。唐代京兆釋道宣《廣弘明集》卷十五載:“洛州故都西白馬寺東一里育王塔。”有學(xué)者認(rèn)為,這個育王塔即為阿育王寺。實際上,《廣弘明集》把洛陽與洛州混為一談。因為北魏洛陽與洛州是兩個不同的地理概念,北魏時期,將司州改名為洛州,治所在洛陽縣,就是現(xiàn)在洛陽市東北,不久就復(fù)名為司州。東魏時又改洛州,到隋朝時廢除。造像題記對洛陽周邊五縣佛像進(jìn)行記述時,只說數(shù)量、方位、造像題材而不提及寺院,唯對阿育王寺作了詳細(xì)描述,足以證明其地位之高。這一史料有力佐證了《魏書》關(guān)于洛陽阿育王寺的記載,且進(jìn)一步明確了地點,彌足珍貴。作者:賀玉萍 【原標(biāo)題:洛陽水泉石窟摩崖碑刻的新發(fā)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