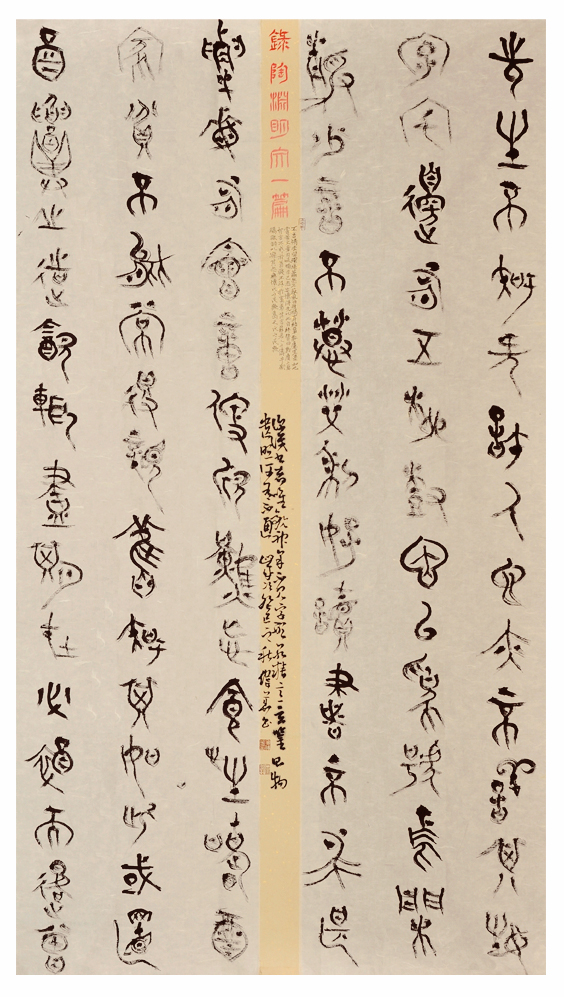-
沒有記錄!
隔岸是否有蘇軾
2015/3/6 11:51:20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張瑜娟
世間無非男子、女子,然而相互看過去,瞬間卻如同隔岸煙火,滋滋向上,美,卻仿佛不在實處。或許這便是人與人的距離,距離生隙,卻亦生成美麗。
女子欣賞男子的豪情、俠義、才情以及強大的內里,還有他們的英雄夢。男子大抵都有英雄夢吧?起碼,少年時曾有。女子所愛的極致無非英雄性,可見男女在某處是相通的,即便隔岸煙火。
相愛的最終多是件冷酷的事,只因所有事物總要走向消亡。當那個愛轉化為親情,原本的情感已成為另一種事物;當它轉化為仇敵,那個愛已變質,生成相反方向的力;當它化作青煙,愛便升騰了,卻逃不脫走向涼荒,或更廣闊的涼荒。
愛情可能比較符合一首詩的意義,不是它本身太脆弱,而是它不在三維的維度里,維度正好是我們最大的局限。
蘇軾的一句“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蕩氣回腸間卻又千回百轉,氣吞山河時亦去向了更深邃的悲憫,滲透于字里行間,讓人激昂卻又潸然。那里頭正是情感,男子的、無底的,一個滄桑才子蒼涼、豪邁而又深邃悲憫的絕唱。他一定是有大情感的,凝結在世人的所感之外,想要冷眼看世界,卻在蒼茫處潤濕了雙眼。世間寥闊,能置放我們的肉身,卻不見得能夠安妥所有的感知與才情。那些無中生有的感知,寂寞還有靈性,回蕩在身體與內心時才是雙重的充盈。感知是人與天地與內心的瞬間相通,生成靈性。寂寞類于孤獨,卻不是孤單,孤單是想要去到某處,孤獨卻是更深遠的抵達。
蘇軾那個彼時的男子還好嗎?歲月的盡頭定然存在著許多無法逝去的影像,他的華發是否在神游中依然生長?那番如夢人生,還有多情、還有江月。
那個筑了蘇堤、料理出東坡肉的男子,那個寫出“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的男子,那個感懷“十年生死兩茫茫……”的男子,他真的曾經存在過嗎?還有他《赤壁賦》中的人物和潛在人物們,那個曲有誤、周郎顧的周公瑾,那個氣勢磅礴、建安文學的領袖者曹氏們……他們密集地出現,讓人簡直以為英雄無處不在。
或者,說起英雄,恐怕無法不提秦始皇,他有著絕對的決絕和凜冽,隔了太久遠的時空看過去,他更像個行為藝術家,他造出太多唯一,他帶領出所向披靡的軍隊,他設計出強大的謎樣的箭陣,還有他的長城、他的陵墓……他留給世人太多難解之謎,他無法超越,他擁有山的力量。那個山是秦嶺嗎?
我可能沒法回避那顆愛惜才情的心,于是繞不過李白,那個游俠,那個仿佛總在殘陽或暮雪背景下的詩者,那個男子,以及那些個舊夢。他那日的散發結了嗎?他壓了五花馬、壓了千金裘的豪情可曾消得了萬古愁?他仍在凝視那個令他放歌和黯傷的長安嗎?或者,他的凝視與放歌與黯傷無關。他風塵仆仆,他仗劍天涯,對了,還有他詩中的蜀僧,那個我畫了無數次的蜀僧,那個抱著綠綺的蜀僧,仿佛隔了千年仍能聽到那曲令碧山暮、秋云暗的古老琴聲。
其實,我此時不想說古人,然而古人站在歲月之外,安妥、清晰;其實我想說當世的男子,可是我們同在此時的空間時卻竟然如在謎中,無法看得清晰。然而盡管如此,我卻清晰地欣賞并羨慕著男子間的情感,那份天然的豪情,即便兩個普通的男子,于世間相遇、相交并相知時,談吐恣肆,霍霍而來,或對酒當歌,或靜默相對,其間四目遼遠,許是知己。此時男女間的那點情顯然有點無力,去不到某個更遙遠的深邃處,闊不出胸懷來承擔那份單純的人境,雖有知己、紅顏這樣的詞,卻軟了些。兩個引為知己的男子更有力量,氣場相合時鐵錚錚的盡是力,俠肝義膽、豪氣豪情,那亦是英雄性!讓人想起夕陽與遠山,想起大碗大碗的老酒、大塊大塊的馬肉;長亭向晚、孤舟、渡口……
或者,每個男子都是英雄。
或者,那隔了岸的煙火在夜色中方能顯現絕美。
世界是個迷宮嗎?我們交錯在變幻的空間與維度里,我們甚至找不到入口與出口,我們可能會向往莫奈唯美的庭院,我們可能更會想起博爾赫斯那座交叉小徑的花園,我們在其間行走,我們隔岸相望,對視間便是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