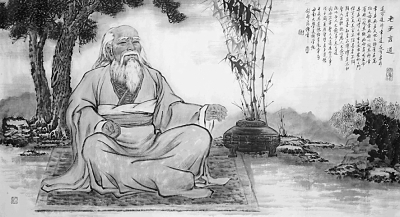┴x┼dÅłĄ┌░╦┤·
Åłųą║═Ż¼─ąŻ¼1967─Ļ╔·Ż¼║ė─Ž╩Ī░▓Ļ¢(y©óng)╩ą╗¼┐hĄ└┐┌µé(zh©©n)╚╦Ż¼Ą└┐┌¤²..[įö╝Ü(x©¼)]
└ė│÷Š½▓╩╚╦╔·
└ė«ŗ(hu©ż)ėųĘQĀC«ŗ(hu©ż)Ż¼╗╣P«ŗ(hu©ż)Ż¼╩Ūė├╗¤²¤ß└ėĶFį┌╬’¾w╔Žņ┘│÷└ė║█..[įö╝Ü(x©¼)]
«ö(d©Īng)ėą╦∙│╔ ▒žėą
╚²į┬Ą─Ļ¢(y©óng)╣Ōį┌│Ū╩ąĄ─├┐éĆ(g©©)ĮŪ┬õ└’’@Ą├Ė±═ŌĄ─║═ņŃīÄ?k©┤)oŻ¼╠ż╚ļ..[įö╝Ü(x©¼)]
-
ø](m©”i)ėąėøõø!
Į©śŗ(g©░u)ą┬Ą└╝ęĄ─Ī░ūį╚╗╩└ĮńĪ▒
2017/7/3 11:17:28 ³c(di©Żn)ō¶öĄ(sh©┤)Ż║ ĪŠūų¾wŻ║┤¾ ųą ąĪĪ┐
ĪĪĪĪ╬ęéā│Ż│Żęį╚╦ŅÉ(l©©i)×ķ║╦ą─Īó┴óūŃė┌╬ęéā┘ćęį╔·┤µĄ─ĄžŪ“┐┤┤²▀@éĆ(g©©)╩└ĮńŻ¼░č╚╦ŅÉ(l©©i)ų«═ŌĄ─┤µį┌ĘQ×ķŁh(hu©ón)Š│Ż¼ė┌╩Ūėą╦∙ų^═Ō╠½┐šŁh(hu©ón)Š│Īó╠½┐šŁh(hu©ón)Š│Īóūį╚╗Łh(hu©ón)Š│Ą╚šf(shu©Ł)Ę©ĪŻ╬ę╦∙ų^Ą─ūį╚╗╩└Įń╩ŪŠ═š¹éĆ(g©©)ėŅųµČ°čįĄ─Ż¼ėŅųµŠ═Ųõ▒Š┘|(zh©¼)ęŌ┴x╔ŽŠ═╩Ūūį╚╗╩└ĮńŻ¼─╦╩Ūūį╚╗Ą─┤µį┌ĪŻ
ĪĪĪĪūį╚╗╩└ĮńĄ─ė^─Ņ╩ŪÅ─ėŅųµĄ─ęĢĮŪī”(du©¼)ėŅųµĄ─šJ(r©©n)ų¬┼c└ĒĮŌŻ¼╩ŪÅ─ūį╚╗Ą─ęĢĮŪī”(du©¼)ūį╚╗Ą─šJ(r©©n)ų¬┼c└ĒĮŌŻ¼┼c╚╦ŅÉ(l©©i)ęĢė“ųąĄ─ūį╚╗Łh(hu©ón)Š│¤o(w©▓)ĻP(gu©Īn)ĪŻę“?y©żn)ķūį╚╗Łh(hu©ón)Š│╩ŪŽÓī”(du©¼)ė┌╚╦ŅÉ(l©©i)Č°čįĄ─Ż¼╩Ūęį╚╦ŅÉ(l©©i)×ķųąą─Č°░č╚╦ŅÉ(l©©i)ų▄?ch©ź)·Ą─╩└ĮńĘQū„ūį╚╗Łh(hu©ón)Š│Ż¼▓óŪęūį╚╗Łh(hu©ón)Š│═©│ŻųĖ╚╦ŅÉ(l©©i)┐╔ęįė|╝░╗“š▀┐╔ęįų▒Įė╗“ķgĮėė░Ēæ╚╦ŅÉ(l©©i)╔·┤µ┼c░l(f©Ī)š╣Ą─╚╦ŅÉ(l©©i)ų▄?ch©ź)·Ą─═Ō▓┐╩└ĮńĪŻ▀@ĘNūį╚╗Łh(hu©ón)Š│ų„ę¬ųĖĄžŪ“╔Žė░Ēæ╚╦ŅÉ(l©©i)╔·┤µĄ─Ė„ĘNę“╦žĄ─┐é║═ęį╝░░³╣³ĄžŪ“Ą─┤¾ÜŌīėŻ¼░³└©┤¾ÜŌĪóÜŌ║“ĪóĻ¢(y©óng)╣ŌĪó’L(f©źng)ėĻĪó║Żč¾Īó║ė┴„Īó╔Į├}Īó▓▌─ŠĪóŪ▌½FĄ╚Ą╚Ż╗▀@ĘNūį╚╗Łh(hu©ón)Š│╩ŪėąŽ▐Ą─Ż¼═©│Żę▓╩Ū┐╔ęįšJ(r©©n)ų¬Ą─ĪŻ
ĪĪĪĪūį╚╗╩└Įńļm╚╗╩Ū¤o(w©▓)Ž▐Ą─Ż¼║Ł╔wš¹éĆ(g©©)ėŅųµŻ¼Ą½╩ŪŻ¼ęį╚╦ŅÉ(l©©i)Ą─ųŪ┴”▓╗╠½┐╔─▄─▄ē“ĖF▒M▀@¤o(w©▓)Ž▐Ą─ūį╚╗╩└ĮńĪó¤o(w©▓)Ž▐Ą─ėŅųµĪŻ▓╗Ą├ęčŻ¼╬ęéā░čūį╚╗╩└ĮńäØĘų×ķ╦─éĆ(g©©)īė├µŻ║ė╔¤o(w©▓)öĄ(sh©┤)Ą─ąŪŪ“┼cąŪļH┐šķgęį╝░╔·┤µė┌ŲõķgĄ─ūį╚╗╬’Ą╚╦∙ĮM│╔Ą─ūį╚╗╩└ĮńŻ¼ė╔═Ō╠½┐šĪó╠½┐šĪó┤¾ÜŌīėĪóĄžŪ“ęį╝░╔·┤µė┌ŲõķgĄ─ūį╚╗╬’Ą╚╦∙ĮM│╔Ą─ūį╚╗╩└ĮńŻ¼ė╔╠½┐šĪó┤¾ÜŌīėĪóĄžŪ“ęį╝░╔·┤µė┌ŲõķgĄ─ūį╚╗╬’Ą╚╦∙ĮM│╔Ą─ūį╚╗╩└ĮńŻ¼ė╔┤¾ÜŌīėĪóĄžŪ“ęį╝░╔·┤µė┌ŲõķgĄ─ūį╚╗╬’Ą╚╦∙ĮM│╔Ą─ūį╚╗╩└ĮńĪŻī”(du©¼)ė┌╚╦ŅÉ(l©©i)Č°čįŻ¼╦∙ų^ūį╚╗╩└Įńų„ę¬ųĖ║¾Č■š▀Ż¼Č°║¾Č■š▀ī”(du©¼)ė┌╚╦ŅÉ(l©©i)ėąų°ų▒Įė╗“ķgĮėĄ─ė░ĒæŻ¼Å──┐Ū░üĒ(l©ói)┐┤ę▓╩Ū╚╦ŅÉ(l©©i)┐╔ęįšJ(r©©n)ų¬Ą─ŅI(l©½ng)ė“ĪŻ
Č■
ĪĪĪĪūį╚╗╩└ĮńĄ─▒ŠįŁ╩ŪĄ└Ż¼Ą└╩Ūūį╚╗╩└ĮńĪóūį╚╗╚f(w©żn)╬’Ą─äō(chu©żng)╔·š▀ĪŻŠ═Ą└äō(chu©żng)╔·ūį╚╗╩└ĮńĪóūį╚╗╚f(w©żn)╬’Č°čįŻ¼Ą└╩ūŽ╚äō(chu©żng)įņ│÷ę╗į¬ų«ÜŌ——╗ņŃńę╗¾wĄ─ĪóįŁ╩╝Ą─“╬’”Ż¼ė╔Ųõśŗ(g©░u)│╔įŁ│§Ą─ūį╚╗╩└ĮńŻ¼╚╗║¾╩╣ę╗į¬ų«ÜŌĘų╗»×ķĻÄĻ¢(y©óng)Č■ÜŌŻ¼═©▀^(gu©░)ĻÄĻ¢(y©óng)Č■ÜŌĄ─Ė„ūį─²ĮY(ji©”)Č°╔·│÷╠ņĄžŻ¼į┘═©▀^(gu©░)ĻÄĻ¢(y©óng)Č■ÜŌĄ─Į╗═©ĪóģR║Ž╔·│÷╠ņĄžķgĄ─ūį╚╗╚f(w©żn)╬’Ż╗Ą└¤o(w©▓)╠Ä▓╗į┌Ż¼į┌╔·│÷ūį╚╗╩└ĮńĪóūį╚╗╚f(w©żn)╬’ų«║¾┤µį┌ė┌ūį╚╗╩└ĮńĪóūį╚╗╚f(w©żn)╬’ų«ųąŻ¼┼cūį╚╗╚f(w©żn)╬’“ėH├▄¤o(w©▓)ķg”Ż¼╚┌×ķę╗¾wŻ╗╠ņĄž▓╗╦└Ż¼ūį╚╗╚f(w©żn)╬’į┌╔·├³ĮKĮY(ji©”)║¾ėųĢ■(hu©¼)╗žÜwė┌Ą└Ż¼Ž¹╚┌ė┌Ą└ų«ųąŻ╗ūį╚╗╚f(w©żn)╬’ļm╚╗ėąŲõ╔·╦└Ż¼Ą½╩ŪŻ¼ūį╚╗╚f(w©żn)╬’╦∙śŗ(g©░u)│╔Ą─ūį╚╗╩└Įńģs╩Ūėą╩╝¤o(w©▓)ĮKĄ─┤µį┌ĪŻ
ĪĪĪĪūį╚╗╩└Įńė╔╠ņĪóĄžĪó╠ņĄ─śŗ(g©░u)│╔š▀ĪóĄž╔ŽĄ─ūį╚╗╬’ęį╝░╠ņĄžų«ķgĄ─ūį╚╗╬’Ą╚╦∙śŗ(g©░u)│╔Ż¼Č°╠ņätė╔╚šį┬ĪóąŪ│ĮĪó╦─Ģr(sh©¬)ĪóĢāę╣Ą╚╦∙śŗ(g©░u)│╔Ż¼Ąž╔ŽĄ─ūį╚╗╬’ätėą╔Į┤©║ė┴„Īó▓▌─ŠŪ▌½FĪó’w°B(ni©Żo)Īó¶~(y©▓)„MĪó└źŽx(ch©«ng)Ą╚Ż¼╠ņĄžų«ķgĄ─ūį╚╗╬’ätėąĻÄĻ¢(y©óng)Č■ÜŌĪó’L(f©źng)ėĻ└ū÷¬ĪóįŲ▓╩Ą╚Ż╗į┌ūį╚╗╩└ĮńųąŻ¼╠ņĄžūŅ×ķųžę¬Ż¼╠ņĄžęį╝░╠ņĄžų«ķgĄ─┐šķgūŅ×ķÅV┤¾Ż╗▓╗āH╠ņĄžęį╝░╠ņĄžų«ķgĄ─┐šķgūŅ×ķÅV┤¾Ż¼Č°Ūę╠ņĄž─▄ē“╔·Č°▓╗╦└Ż¼▀@╩Ū╠ņĄž─▄ē“│╔×ķ╠ņĄžų«═ŌĄ─ūį╚╗╚f(w©żn)╬’Ą─╔·┤µ╝ęł@Ą─ųžę¬įŁę“ĪŻ
ĪĪĪĪūį╚╗╩└ĮńųąĄ─ūį╚╗╚f(w©żn)╬’ļm╚╗Ū¦▓Ņ╚f(w©żn)äeČ°Ūę┐┤ŲüĒ(l©ói)▓ŅŠÓŠ▐┤¾Ż¼ŲõīŹ(sh©¬)Ż¼ūį╚╗╚f(w©żn)╬’Ą─▓Ņäe╩ŪŽÓī”(du©¼)Ą─Ż¼┼c┤╦ŽÓæ¬(y©®ng)Ż¼ūį╚╗╚f(w©żn)╬’ļm╚╗ėąÅŖ(qi©óng)ėą╚§Č°Ūę┐┤ŲüĒ(l©ói)ÅŖ(qi©óng)╚§Ęų├„Ż¼Ą½ūį╚╗╚f(w©żn)╬’Ą─ÅŖ(qi©óng)╚§ę▓╩ŪŽÓī”(du©¼)Ą─Ż¼╦∙ęįŻ¼Ūfūėį╗Ż║“Ę▓ėą├▓Ž¾┬Ģ╔½š▀Ż¼Įį╬’ę▓Ż¼╬’┼c╬’║╬ęįŽÓ▀h(yu©Żn)Ż┐”Ż©ĪČŪfūė·▀_(d©ó)╔·ĪĘŻ®Å─ūį╚╗╚f(w©żn)╬’Ą─▒ŠįŁĪóśŗ(g©░u)│╔ęį╝░ūį╚╗╚f(w©żn)╬’▓Ņäe║═ÅŖ(qi©óng)╚§Ą─ŽÓī”(du©¼)ąįüĒ(l©ói)┐┤Ż¼ūį╚╗╚f(w©żn)╬’╩ŪŲĮĄ╚Ą─Ż¼═¼Ģr(sh©¬)Ż¼ūį╚╗╩└ĮńųąĄ─ūį╚╗╚f(w©żn)╬’╝┤▒Ńėą╦∙ų^ūŅÅŖ(qi©óng)š▀Ż¼ę▓ąĶę¬ŲĮĄ╚Ąžī”(du©¼)┤²╦¹╬’ĪŻŲĮĄ╚Ż¼ī”(du©¼)ė┌ūį╚╗╚f(w©żn)╬’üĒ(l©ói)šf(shu©Ł)╩Ū┼c╔·ŠŃüĒ(l©ói)Ą─ĪŻ
╚²
ĪĪĪĪūį╚╗╚f(w©żn)╬’Ą─šJ(r©©n)ų¬░³└©ūį╚╗╚f(w©żn)╬’ī”(du©¼)ė┌ūį╔ĒĄ─šJ(r©©n)ų¬ęį╝░ūį╚╗╚f(w©żn)╬’ī”(du©¼)ė┌ūį╚╗╩└ĮńĄ─šJ(r©©n)ų¬Ż¼ę▓Š═╩Ūšf(shu©Ł)Ż¼░³└©ūį╚╗╚f(w©żn)╬’Ą─ūį╬ęšJ(r©©n)ų¬ęį╝░ūį╚╗╚f(w©żn)╬’ī”(du©¼)ė┌“╦¹š▀”Ą─šJ(r©©n)ų¬ĪŻ▀@ā╔ĘNšJ(r©©n)ų¬į┌Ģr(sh©¬)ķgīė├µ╩Ū═¼Ģr(sh©¬)Ą─Ż¼į┌▀ē▌ŗīė├µę▓╩Ūø](m©”i)ėą╦∙ų^Ž╚║¾┤╬ą“Ą─ĪŻūį╚╗╩└ĮńųąĄ─╚╬║╬ūį╚╗╬’Č╝╩Ū═©▀^(gu©░)ī”(du©¼)ūį╬ęĄ─šJ(r©©n)ų¬šJ(r©©n)ŪÕūį╝║Ż¼═©▀^(gu©░)ī”(du©¼)“╦¹š▀”Ą─šJ(r©©n)ų¬šJ(r©©n)ŪÕūį╚╗╩└ĮńŻ¼▓ó═©▀^(gu©░)ī”(du©¼)ė┌ūį╬ę┼c“╦¹š▀”Ą─šJ(r©©n)ų¬ģ^(q©▒)Ęųūį╬ę┼cūį╚╗╩└ĮńŻ¼æ¬(y©®ng)ī”(du©¼)Īó╠Ä└Ēūį╬ę┼cūį╚╗╩└ĮńĄ─ĻP(gu©Īn)ŽĄĪŻūį╚╗╚f(w©żn)╬’Ą─ūį╬ęšJ(r©©n)ų¬Š═╩Ūūį╚╗╚f(w©żn)╬’ī”(du©¼)ė┌ūį╝║Ą─Č┤▓ņĪó└ĒĮŌ║═įu(p©¬ng)ār(ji©ż)Ż¼╔µ╝░ūį╚╗╚f(w©żn)╬’ī”(du©¼)ė┌Ųõš¹éĆ(g©©)╔·├³▀^(gu©░)│╠Īó╔·╗Ņ┴Ģ(x©¬)ąįĪó╔·┤µ└¦Š│Ą╚Ą─šJ(r©©n)ų¬Ż¼╔µ╝░ūį╚╗╚f(w©żn)╬’ī”(du©¼)ė┌Ųõį┌ūį╚╗╩└ĮńųąĄ─╬╗ų├Īóī”(du©¼)ė┌Ųõ─▄┴”Ą─šJ(r©©n)ų¬ĪŻ
ĪĪĪĪūį╚╗╚f(w©żn)╬’╔·┤µė┌ūį╚╗╩└Įńų«ųąŻ¼═©▀^(gu©░)ī”(du©¼)ė┌ūį╚╗╩└ĮńĄ─šJ(r©©n)ų¬Č°┼cūį╚╗╩└ĮńĪóūį╚╗╩└ĮńųąĄ─╦¹╬’ŽÓĮėė|Ż¼▀M(j©¼n)Č°┼cūį╚╗╩└ĮńĪóūį╚╗╩└ĮńųąĄ─╦¹╬’░l(f©Ī)╔·┬ō(li©ón)ŽĄĪŻūį╚╗╚f(w©żn)╬’ī”(du©¼)ūį╚╗╩└ĮńĄ─šJ(r©©n)ų¬Ą─ĀŅørų▒ĮėøQČ©Ųõī”(du©¼)ė┌ūį╚╗╩└ĮńĪóī”(du©¼)ė┌ūį╚╗╩└ĮńųąĄ─╦¹╬’Ą─æB(t©żi)Č╚Ż¼ų▒ĮėøQČ©Ųõūį╔ĒĄ─╔·┤µĀŅørĪŻūį╚╗╚f(w©żn)╬’ī”(du©¼)ė┌ūį╚╗╩└ĮńĄ─šJ(r©©n)ų¬Ż¼Š═šJ(r©©n)ų¬ī”(du©¼)Ž¾üĒ(l©ói)šf(shu©Ł)Ż¼╔µ╝░Ųõī”(du©¼)ė┌ūį╚╗╩└ĮńĄ─üĒ(l©ói)į┤Īóūį╚╗╩└ĮńĄ─š¹¾węį╝░ūį╚╗╩└ĮńųąĄ─╦¹╬’Ą─šJ(r©©n)ų¬Ż╗Š═šJ(r©©n)ų¬Ą─ęĢĮŪüĒ(l©ói)šf(shu©Ł)Ż¼╔µ╝░Ą└Ą─ęĢĮŪ┼c╬’Ą─ęĢĮŪĄ╚Ż╗Š═šJ(r©©n)ų¬ų„¾wüĒ(l©ói)šf(shu©Ł)Ż¼╔µ╝░╚╦┼c╚╦ų«═ŌĄ─╦¹╬’Ż¼╗“š▀šf(shu©Ł)Ż¼╔µ╝░╦∙ėąĄ─ūį╚╗╬’ĪŻ
ĪĪĪĪśŗ(g©░u)│╔ūį╚╗╩└ĮńĄ─ūį╚╗╚f(w©żn)╬’▒M╣▄éĆ(g©©)ąįĖ„«ÉĪóą╬æB(t©żi)Ė„«ÉĪó╔·┤µŁh(hu©ón)Š│Ė„«ÉŻ¼Ą½╩ŪŻ¼Č╝╩Ūī”(du©¼)ĘĮą──┐ųą═Ļ├└Ą─┤µį┌Ż¼ūį╚╗╚f(w©żn)╬’ų«ķg▒ŠüĒ(l©ói)Š═╩Ū▒╦┤╦║═ųC║═─└Ą─Ż¼ę“┤╦Ż¼ūį╚╗╚f(w©żn)╬’╩Ū▓╗ąĶę¬Ė─ūāĄ─ĪŻ▀@ęŌ╬Čų°ūį╚╗╚f(w©żn)╬’Ą─ŽÓ╠Äų«Ą└▒ž╚╗╩Ū¤o(w©▓)×ķČ°Ēśæ¬(y©®ng)╦¹╬’ų«ūį╚╗ĪŻų╗ėąū÷ĄĮ¤o(w©▓)×ķČ°Ēśæ¬(y©®ng)╦¹╬’ų«ūį╚╗Ż¼▓┼─▄īŹ(sh©¬)¼F(xi©żn)“ĻÄĻ¢(y©óng)║═ņoŻ¼╣Ē╔±▓╗ö_Ż¼╦─Ģr(sh©¬)Ą├╣Ø(ji©”)Ż¼╚f(w©żn)╬’▓╗é¹Ż¼╚║╔·▓╗ž▓Ż¼╚╦ļmėąų¬Ż¼¤o(w©▓)╦∙ė├ų«”Ż©ĪČŪfūė·┐śąįĪĘŻ®Ą─├└║├Šų├µŻ╗ūį╚╗╚f(w©żn)╬’ę▓▓┼─▄╝╚▒Żūo(h©┤)║├ūį╝║Ż¼ėų▒Żūo(h©┤)║├╦¹╬’Ż¼▓óŪęėHĮ³ĪóĻP(gu©Īn)É█(©żi)╦¹╬’ĪŻ
╦─
ĪĪĪĪūį╚╗╚f(w©żn)╬’ū„×ķ╔·┤µŁh(hu©ón)Š│Īó╔·┤µ┘Yį┤Ą─ąĶ꬚▀Ż¼ąĶę¬└¹ė├╗“į╗╩╣ė├╦¹╬’Ż¼Č°└¹ė├╗“į╗╩╣ė├╦¹╬’ęŌ╬Čų°ī”(du©¼)╦¹╬’Ą─┐╔─▄Ą─é¹║”Ż¼▀@Š═ę¬Ū¾ūį╚╗╚f(w©żn)╬’į┌└¹ė├╗“į╗╩╣ė├╦¹╬’Ģr(sh©¬)─▄ē“ū÷ĄĮ“ė├┤¾”Ż╗ūį╚╗╚f(w©żn)╬’ū„×ķ╦¹╬’Ą─╔·┤µŁh(hu©ón)Š│Īó╔·┤µ┘Yį┤Ż¼Š═╩Ū▒╗ąĶ꬚▀Ż¼▓╗Ą├▓╗▒╗╦¹╬’╦∙└¹ė├╗“į╗╩╣ė├Ż¼×ķ┴╦▓╗▒╗╦¹╬’╦∙é¹║”Ż¼ėųę¬Ū¾ūį╚╗╚f(w©żn)╬’į┌╦¹╬’└¹ė├╗“į╗╩╣ė├ūį╝║Ģr(sh©¬)─▄ē“ū÷ĄĮ“¤o(w©▓)ė├”ĪŻ«ö(d©Īng)ūį╚╗╚f(w©żn)╬’▓╗─▄┤_▒Żūį╝║ę╗Č©─▄ē“ū÷ĄĮ“¤o(w©▓)ė├”Ż¼═¼Ģr(sh©¬)ę▓▓╗─▄ē“┤_▒Ż└¹ė├╗“į╗╩╣ė├ūį╝║Ą─╦¹╬’ę╗Č©─▄ē“ū÷ĄĮ“ė├┤¾”ų«Ģr(sh©¬)Ż¼ūį╚╗╚f(w©żn)╬’ūįŠ╚Ą─ĘĮĘ©ų╗ėąā╔ĘNŻ¼─ŪŠ═╩Ūę¬├┤┼cūį╝║Ą─═¼ŅÉ(l©©i)ČĘųŪČĘė┬Ż¼ę¬├┤ūīūį╝║ėą“╚▒Ž▌”ĪŻļm╚╗▀@ā╔ĘNĘĮĘ©▓ó▓╗Ą└Ą┬Ż¼ę▓▓╗╩«Ęų┐╔┐┐ĪŻ▀ĆėąŻ¼ūį╚╗╚f(w©żn)╬’┼cūį╝║Ą─═¼ŅÉ(l©©i)ČĘųŪČĘė┬Ż¼ūīūį╝║ėą“╚▒Ž▌”Ż¼▀@į┌Ūfūė┐┤üĒ(l©ói)ī┘ė┌ėąęŌ×ķų«Ż¼Č°ĘŪ│÷ė┌╠ņąįĪŻ▀@ĘN┐┤Ę©¤o(w©▓)ę╔╩ŪÕe(cu©░)š`Ą─Ż¼ę▓┼cŪfūė│ń╔ąūį╚╗ĪóĘ┤ī”(du©¼)“╚╦×ķ”Ą─┴ół÷(ch©Żng)ŽÓū¾ĪŻį┌╬ę┐┤üĒ(l©ói)Ż¼æ¬(y©®ng)įō╩Ūūį╚╗╚f(w©żn)╬’▒ŠėąŲõ▀@ĘĮ├µĄ─╠ņąįŻ¼╚╗║¾┐┤╦ŲėąęŌ×ķų«Ż¼īŹ(sh©¬)ät│÷ė┌╠ņąįŻ¼▓╗ų¬▓╗ėX(ju©”)ųąĒśæ¬(y©®ng)┤╦╠ņąįČ°š╣┬Čų«Č°ęčĪŻ╝┤╩Ūšf(shu©Ł)Ż¼╦∙ų^ėąęŌ×ķų«Ż¼─╦╩ŪŪfūėĪó╦¹╬’Ą─Õe(cu©░)ėX(ju©”)Ż╗│÷ė┌╠ņąįŻ¼▓┼╩Ūš²┤_Ą─┐┤Ę©ĪŻ
ĪĪĪĪū„×ķūį╚╗╚f(w©żn)╬’Ą─╔·┤µŁh(hu©ón)Š│┼c╔·┤µ┘Yį┤Ą─╦¹╬’Č╝╩Ū═Ļ├└Ą─Ż¼╩Ū▓╗ąĶę¬ę▓▓╗┐╔ęįĖ─ūāĄ─Ż¼╦∙ų^╦¹╬’Ą─▓╗═Ļ├└─╦╩Ū│¼įĮ┴╦╦¹╬’Ą─▒ŠąįĪó─▄┴”Č°ī”(du©¼)ė┌╦¹╬’Ą─▀^(gu©░)Ė▀Ą─Īó¤o(w©▓)└ĒĄ─ę¬Ū¾ĪŻ├µī”(du©¼)╦¹╬’Ą─╦∙ų^╚▒Ž▌Īó╦∙ų^▓╗═Ļ├└╔§ų┴ėą║”ąįęį╝░Øōį┌Ą─╬Ż║”ąįŻ¼ūį╚╗╚f(w©żn)╬’╦∙─▄ē“ū÷Ą─Š═╩ŪšJ(r©©n)ūR(sh©¬)╦¹╬’Ą─ī┘ąįĪó╠ž³c(di©Żn)Č°▓╗ė|╝░Ųõėą║”ąįĪóØōį┌Ą─╬Ż║”ąįŻ¼▓╗Ė─ūā╦¹╬’Č°▀mæ¬(y©®ng)╦¹╬’Ż¼▓╗Ė─ūā╦¹╬’Č°æ(zh©żn)ä┘Īó│¼įĮ╦¹╬’ĪŻūį╚╗╚f(w©żn)╬’“ų╗╩Ū│÷ė┌▓╗┐╔▒▄├ŌĄ─▒ž╚╗ąį▓┼é¹║”║═ܦ£ń╔·├³”Ż©░óĀ¢žÉ╠ž·╩®ĒfØ╔šZ(y©│)Ż®Ż¼į┌Ųõ×ķ┴╦╔·┤µČ°▓╗Ą├▓╗é¹║”ū„×ķ╔·«a(ch©Żn)╗“╔·╗Ņ┘Y┴ŽĄ─╦¹╬’ų«Ģr(sh©¬)Ż¼ę¬ī”(du©¼)╦¹╬’│õØMĖąČ„Īó└óŠ╬ų«ą─Ż¼į┌é¹║”ų«Ū░Īóé¹║”ų«Ģr(sh©¬)ę¬╔Ų┤²╦¹╬’Ż¼▒M┴┐£p╔┘Ųõ═┤┐Ó┼c┐ųæųŻ¼═¼Ģr(sh©¬)Ż¼▒M┴┐?j©®)Ć╩Īūį╝║Ą─ąĶŪ¾Ż¼Å─Č°£p╔┘ī”(du©¼)ė┌╦¹╬’Ą─öĄ(sh©┤)┴┐┼cĘNŅÉ(l©©i)Ą─ąĶŪ¾ĪŻČ°ę¬ū÷ĄĮ▀@ą®Ż¼ąĶę¬ūį╚╗╚f(w©żn)╬’Č«Ą├ų¬ūŃĪŻ
ĪĪĪĪūį╚╗╚f(w©żn)╬’▒ŠėąĄ─╔·┤µŁh(hu©ón)Š│╩Ūūį╚╗╚f(w©żn)╬’╔·Č°Š═ėąĄ─╔·┤µŁh(hu©ón)Š│Ż¼ļm╚╗┐┤╦Ųīż│ŻĪóęūĄ├Ż¼ŲõīŹ(sh©¬)įŁ▒ŠŠ═╩Ūūį╚╗╚f(w©żn)╬’└ĒŽļĄ─╔·┤µŁh(hu©ón)Š│ĪŻ▀@śėĄ─╔·┤µŁh(hu©ón)Š│▓╗āHĮoėĶ┴╦ūį╚╗╚f(w©żn)╬’╔·┤µ╦∙▒žąĶĄ─ę╗ŪąŁh(hu©ón)Š│ę“╦žŻ¼ūīūį╚╗╚f(w©żn)╬’Ą├ęį¤o(w©▓)æn¤o(w©▓)æ]Ą─╔·╗ŅŻ¼Ą├ęįį┌▀@ĘN¤o(w©▓)æn¤o(w©▓)æ]Ą─╔·╗ŅųąĖą╩▄┐ņśĘ(l©©)Ż¼═¼Ģr(sh©¬)Ż¼▀ĆĄųė∙┴╦╦¹╬’Ą─╣źō¶Ż¼║Ūūo(h©┤)┴╦ūį╚╗╚f(w©żn)╬’Ą─╔·├³░▓╚½ĪŻę“┤╦Ż¼▒MŪķŽĒ╩▄▀@śėĄ─╔·┤µŁh(hu©ón)Š│Ż¼ė├ą─╩žūo(h©┤)▀@śėĄ─╔·┤µŁh(hu©ón)Š│Ż¼æčų°ĖąČ„Ą─ą─├µī”(du©¼)▀@śėĄ─╔·┤µŁh(hu©ón)Š│Ż¼▓┼╩Ūūį╚╗╚f(w©żn)╬’æ¬(y©®ng)įōū÷Ą─Ż╗į┌╚╬║╬Ūķą╬ų«Ž┬▓╗▒╗╚╬║╬ę“╦ž╦∙šT╗¾Ż¼▓╗ģÆŠļĪó▓╗ļxķ_(k©Īi)ūį╝║Ą─╔·┤µŁh(hu©ón)Š│Ż¼▓┼╩Ū├„ųŪĄ─▀xō±ĪŻūį╚╗╚f(w©żn)╬’░▓ė┌ūį╔ĒĄ─¼F(xi©żn)ĀŅĪó┐ŽČ©ūį╔ĒĄ─╠ž┘|(zh©¼)Ż¼ęįūį╔ĒĄ─¼F(xi©żn)ĀŅĪóūį╔ĒĄ─╠ž┘|(zh©¼)×ķūŅ×ķ═Ļ├└Ą─¼F(xi©żn)ĀŅĪóūŅ×ķ═Ļ├└Ą─╠ž┘|(zh©¼)Ż¼╩ŪūŅ║├ę▓╩Ū╬©ę╗š²┤_Ą─Š±ō±Ż¼ų╗ėąį┌┤╦Ū░╠ߎ┬▓┼┐╔½@Ą├╔·┤µ░▓╚½Īó½@Ą├╔·├³ųąĄ─┐ņśĘ(l©©)ĪŻ▓╗░▓ė┌ūį╔ĒĄ─¼F(xi©żn)ĀŅŻ¼ėų¤o(w©▓)┴”Ė─ūāūį╔ĒĄ─¼F(xi©żn)ĀŅŻ¼į┌┤╦ĀŅørŽ┬×ķĖ─ūāūį╔ĒĄ─¼F(xi©żn)ĀŅČ°Ū¾ų·ė┌╦¹╬’Ż¼Š═ęŌ╬Č░č├³▀\(y©┤n)Į╗Įo╦¹╬’Ż¼░čā┤ļU(xi©Żn)┴¶Įoūį╝║Ż╗▓╗┐ŽČ©ūį╔ĒĄ─╠ž┘|(zh©¼)Ż¼ėų▓╗┐╔─▄Ė─ūāūį╔ĒĄ─╠ž┘|(zh©¼)Ż¼į┌┤╦ĀŅørŽ┬▀Ć┴w─Į╦¹╬’Ż¼Ę±Č©ūį╝║Ż¼Š═ęŌ╬ČĘ┼Śēūį╝║Ą─┐ņśĘ(l©©)Ż¼Č°╚źūįīż¤®É└——īżšę▒ŠüĒ(l©ói)Š═▓╗æ¬(y©®ng)įōėąĄ─═┤┐Ó┼c¤®É└ĪŻūį╚╗╚f(w©żn)╬’š²┤_įu(p©¬ng)╣└ūį╝║Ż¼ĒśÅ─▒╚ūį╝║ŽÓī”(du©¼)ÅŖ(qi©óng)┤¾Ą─╦¹╬’Ż¼▓╗┼c╦¹╬’ĀÄ(zh©źng)ÅŖ(qi©óng)ČĘ║▌Ż¼▓╗šą╚Ū╦¹╬’╠žäe╩Ū▓╗šą╚Ū┼c╝║▓ó¤o(w©▓)ų▒ĮėĻP(gu©Īn)ŽĄĄ─╦¹╬’Ż¼▓┼╩ŪŅŻųŪĄ─ĪŻę“?y©żn)ķų╗ėą▀@śė▓┼▓╗ų┴ė┌ų„äė(d©░ng)šąüĒ(l©ói)Üó╔Ēų«Ą£Ż¼▓┼┐╔▒Ż╚½ūį╝║ĪŻūį╚╗╚f(w©żn)╬’╔·┤µ└¦Š│Ą─╗»ĮŌĪó│¼įĮų╗─▄╩ŪŠ½╔±īė├µĄ─╗»ĮŌĪó│¼įĮĪŻ«ö(d©Īng)ā╚(n©©i)ą─ļyęįīŹ(sh©¬)¼F(xi©żn)▀@ĘN╗»ĮŌĪó│¼įĮų«Ģr(sh©¬)Ż¼“ē¶(m©©ng)”▒ŃĄŪł÷(ch©Żng)┴╦ĪŻ▓╗▀^(gu©░)Ż¼▒ŠüĒ(l©ói)¤o(w©▓)ęŌūR(sh©¬)Ą─ūį╚╗ų«“ē¶(m©©ng)”į┌Ųõūā│╔ėąęŌūR(sh©¬)Ą─│¼įĮų«“ē¶(m©©ng)”ų«Ģr(sh©¬)Ż¼“ē¶(m©©ng)”▒Ń▓╗į┘╩Ū“ē¶(m©©ng)”Ż¼Č°│╔┴╦┴Ēę╗ĘNŠ½╔±│¼įĮĄ─┬ĘÅĮĪŻ
ĪĪĪĪų«╦∙ęįę¬Į©śŗ(g©░u)ą┬Ą└╝ęĄ─“ūį╚╗╩└Įń”Ż¼ėæšōūį╚╗╩└Įń┼cūį╚╗╩└ĮńųąĄ─ūį╚╗╚f(w©żn)╬’Ż¼▓óė╔┤╦Č°ėæšōūį╚╗╩└ĮńĄ─ą╬│╔┼cśŗ(g©░u)│╔Īóūį╚╗╚f(w©żn)╬’Ą─ŲĮĄ╚┼cŽÓ╠Äų«Ą└Īóūį╚╗╚f(w©żn)╬’Ą─ūį╬ęšJ(r©©n)ų¬┼cī”(du©¼)“╦¹╬’”Ą─šJ(r©©n)ų¬Īóūį╚╗╚f(w©żn)╬’Ą─╔·┤µųŪ╗█┼c╗»ĮŌ└¦Š│Ą──▄┴”Ż¼ų╗╩ŪŽļ░č╚╦ŅÉ(l©©i)āHāH┐┤ū„ūį╚╗╚f(w©żn)╬’ųąŲš═©Ą─ę╗åTŻ¼╚ź│²╚╦ŅÉ(l©©i)▓╗æ¬(y©®ng)ėąĄ─ā×(y©Łu)įĮĖąŻ¼╚ź│²╚╦ŅÉ(l©©i)▓╗æ¬(y©®ng)ėąĄ─Õe(cu©░)ėX(ju©”)ĪŻī”(du©¼)ė┌┐═ė^╔ŽŽÓī”(du©¼)ÅŖ(qi©óng)┤¾Ą─╚╦ŅÉ(l©©i)üĒ(l©ói)šf(shu©Ł)Ż¼╝╚╚╗ūį╚╗╩└ĮńĄ─╣ĒĖ½╔±╣ż┘xėĶŲõÅŖ(qi©óng)┤¾Ą─┴”┴┐Ż¼Š═ęŌ╬ČŲõæ¬(y©®ng)Š▀ėąĖ³×ķīÆÅVČ°┤╚▒»Ą─ąžæčŻ¼æ¬(y©®ng)╝ńžō(f©┤)Ė³ČÓĄ─╩╣├³Īó│ąō·(d©Īn)Ė³ČÓĄ─ž¤(z©”)╚╬Ż¼æ¬(y©®ng)ŠSūo(h©┤)ūį╚╗╩└Įń╠ņ╚╗Ą─š²┴xŻ¼╚ź▒Żūo(h©┤)ŽÓī”(du©¼)╚§ąĪĄ─┤µį┌Ż¼Č°▓╗╩ŪŽÓĘ┤ĪŻ
ĪĪĪĪŻ©ū„š▀Ż║ĻæĮ©╚AŻ¼ŽĄ░▓╗š┤¾īW(xu©”)š▄īW(xu©”)ŽĄĮ╠╩┌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