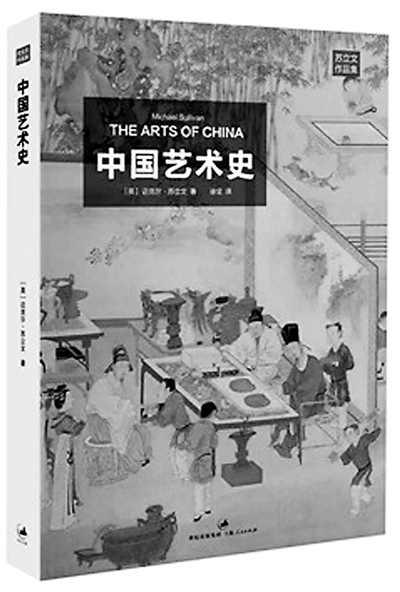-
沒有記錄!
西方藝術史家眼中的中國藝術
2014/6/24 10:41:39 點擊數(shù): 【字體:大 中 小】
《中國藝術史》:(英)邁克爾·蘇立文著;徐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英)邁克爾·蘇立文著;陳衛(wèi)和、錢崗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邁克爾·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 1916—2013)是英國藝術史家,畢生主要從事中國藝術史特別是中國現(xiàn)代藝術史教學和研究,被稱為“中國藝術的知己”,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中國藝術的西方知音”。
蘇立文有三部重要的代表性著作:《東西方藝術的交會》《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中國藝術史》。這些著作曾經(jīng)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或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多次修訂再版,已成為英國高等院校的中國藝術史入門教材或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現(xiàn)代藝術的必讀參考書。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陸續(xù)出版了蘇立文著作中文版,由北京世紀文景文化傳播有限責任公司出品。我認為,最值得我們關注的是蘇立文比較研究的國際視野、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和超越偏見的文化態(tài)度。
所謂“比較研究”主要是指“跨文化比較”,20世紀以來廣泛應用于西方的文化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和文學、藝術等學科研究。蘇立文的著作都具有比較研究的國際視野,開拓了東西方比較藝術研究的領域。在他的《東西方藝術的交會》中,從比較研究的國際視野出發(fā),重點對近現(xiàn)代西方藝術與中國藝術、日本藝術進行比較研究。他試圖總結(jié)東西方藝術的相互影響,并探討造成這種影響和交流的原因。例如,他比較中國與日本接受西方藝術影響的不同態(tài)度,將其歸因于中日兩國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在他的《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中,仍然把西方的沖擊與中國的反應納入比較研究的國際視野,尤其是對中國藝術接受西方寫實主義和現(xiàn)代藝術影響的分析。他說明:“本書的主題是有關在西方文化和藝術的影響之下,中國藝術在20世紀的新生。兩種偉大傳統(tǒng)的相遇,已經(jīng)為中國藝術帶來了難以估量的震動。”甚至在他的《中國藝術史》中,也經(jīng)常比較研究中國藝術與印度、日本及西方藝術的類似與差異,在比較中凸顯中國藝術的特色。
蘇立文身為哈佛大學博士,熟悉西方的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理論,卻自稱:“我沒有理論。”他深信,在人文學科中而不是在自然科學中,“理論,遠離揭示真相,甚至可能是發(fā)現(xiàn)真相的障礙。它們無法被檢驗。”蘇立文的著作基本上采用了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擺脫先驗的或形而上學的理論思辨或假設的固定模式,重視搜集經(jīng)驗材料,通過觀察、調(diào)查、訪問、文獻梳理等方法獲取經(jīng)驗證據(jù),對事實加以分類、比較和歸納,以求得客觀的認識和科學的結(jié)論。我們從蘇立文的《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的撰寫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1942年,蘇立文在成都華西協(xié)和大學博物館工作期間,就開始接觸中國藝術,后來經(jīng)他的中國妻子吳環(huán)介紹,結(jié)識了龐薰琹、丘堤、吳作人、丁聰、劉開渠、關山月等藝術家,到1946年回國時搜集了大量關于中國現(xiàn)代藝術的資料。此后,純粹出于研究的目的,他不斷收藏中國現(xiàn)代藝術品,多達400余件,包括齊白石、黃賓虹、林風眠等名家之作。從1972年起到21世紀初,他又與吳環(huán)多次到中國旅游,與眾多中國藝術家密切交往,掌握了更多關于中國現(xiàn)代藝術的圖像和文獻資料。因此,他撰寫的《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是根據(jù)自己幾十年來對中國現(xiàn)代藝術的經(jīng)驗和觀察,歸納出相對客觀的判斷。也因此,他的藝術史敘事像史話一樣,人物鮮活,細節(jié)生動,繪聲繪色,引人入勝,毫無枯燥乏味之感。
狄德羅和列寧都說過:“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我們要尋求真理就必須克服偏見。可是,要完全克服民族的偏見、文化的偏見、意識形態(tài)的偏見和個人好惡的偏見,幾乎不太可能,所以我們只能迫近真理,而不能窮盡真理。蘇立文說:“我是以西方人的眼光來看中國藝術”,難免產(chǎn)生誤解。不過,對中國文化藝術強烈的求知欲和理解的渴望,以及比較研究的國際視野和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都促使他采取了超越偏見的文化態(tài)度。他寫作《中國藝術史》,編年體例恪守中國傳統(tǒng)的王朝序列,是為了更好地“把握中國人自身對于中國歷史的感覺”。在該書中他承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在發(fā)掘、保護、研究和展示其文化遺產(chǎn)方面,做得比過去更多。”盡管他對“文革”時期破壞文物的現(xiàn)象深感痛心。1959年,他出版《20世紀中國的藝術》時,“多年形成的西方偏見依然非常活躍”,西方同行們批評他“為一個不值得嚴肅對待的課題浪費時間”。直到20世紀70年代,西方學術界才把中國現(xiàn)代藝術列為嚴肅對待的研究課題。蘇立文的《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努力保持實證主義的價值中立,盡量避免意識形態(tài)的偏見。他對中國傳統(tǒng)繪畫、藝術革命、魯迅扶植的木刻運動等,均給以比較客觀的評述;對中國臺灣的現(xiàn)代藝術、移居海外的藝術家的成就,也給以適當篇幅的介紹。曾引起中國學術界和新聞界關注的焦點之一,是蘇立文對徐悲鴻的評價低于林風眠、劉海粟,說徐的繪畫作品“止于合格”。蘇立文的個人愛好確實更加傾向現(xiàn)代主義,不太喜歡寫實主義,但通觀他對徐悲鴻的總體評價:“他是一個有原則的人,一個理想主義者和一個浪漫主義者,在藝術技巧和目的的嚴肅性方面,為學生們樹立了崇高的典范。”“他真誠地相信他的學生所需要的不是根基膚淺的現(xiàn)代派,而是西方技巧的堅實基礎。他貢獻了值得贊揚的東西,或許這就足夠了。”這種態(tài)度比較公允。
2013年8月,97歲高齡的蘇立文在他逝世前夕最后一次訪問中國期間,應邀到上海書展“文景藝文季”現(xiàn)場與中國讀者對話。他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們:商業(yè)化因素對中國當代藝術造成了負面影響。這表明蘇立文作為中國藝術的西方知音,也是我們中國藝術家直言敢諫的諍友,令人肅然起敬,難以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