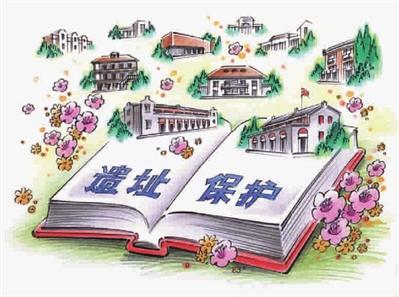精彩推薦
熱點關注
專題推薦
-
沒有記錄!
熱點排行
評論:慰安所遺址要不要保護?
2015/7/9 9:57:24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吳德勝
最近,一位著名歷史學家和帶領的團隊經過十多年的調查研究,在虹口區的東寶興路115弄發現了日軍侵占上海期間的一處慰安所遺址,這里曾經擄掠中國及其他國家良家婦女充當“慰安婦”。這個名為“大一沙龍”的地方,周圍還有“小松亭”、“三好館”、“永樂館”等4個日本僑民經營的風俗場所。隨著調查,上海有166處場所發現當年被日軍指定為特別慰安所。
據悉:“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正在致力于大一沙龍遺址的保護,目標是在此建立紀念館,并申請警示性世界文化遺產”。某報也報道說:“虹口將保護性修繕‘大一沙龍’舊址”,并表示:“肯定不會拆除,不排除對里面的房客進行置換”。
這樣的遺址要不要保護呢?我有些不同看法。
我十分贊成對一些有紀念意義的遺址進行特別保護。就拿虹口區來說,許多重要遺址的發掘和保護工作一直做得很好。一些具有重要意義的遺址經過保護修繕后,已經成為重要紀念場所。比如,“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遺址,已經建成了“四大紀念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地,也建立了紀念館。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原型李白同志生活、工作和被捕地的黃渡路107弄15號,也建成了“李白烈士故居”紀念館。虹口區的“猶太難民避難所”舊址,近年來迎來了世界各國人士絡繹不絕的參觀和回憶。
從一個城市到一個民族,往往有許多具有特定意義的事物。如果沒有這些特定意義,很難想象一個民族如何使自己的集體記憶,一代代地傳承下去。即使是記載著一個民族不幸與災難的那些有意義的遺跡,也應該保留下來,成為民族記憶的一部分。比如“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就已經成為一個有記憶、有血性的民族記憶的一部分,災難的記錄會激發悲壯而強烈的反思和責任感。
但是,遺址的保護不等于一定要恢復原址原貌,也不等于發現一個就要恢復一個。這既要看歷史的價值、城市的總體規劃,也要考慮民眾的情感接受程度。依我看,像“大一沙龍”等166個“慰安所”就不必恢復原址原貌了,也沒必要建立紀念館了。“和服、木屐、澆澡的木桶以及那些具有骯臟特征的東西”,究竟有多大的展示價值呢?
“慰安婦”、“慰安所”等當然記載了日軍的殘暴和喪盡天良,但是那些罪惡通過文字、照片甚至影視劇,已經足以使人們了解真相了,是不是一定都要通過遺址保護的方式,把日軍所有的罪惡都陳列出來,這是十分值得商榷的。特別是究竟是否都需要通過自然主義的方式展現開來,這就更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了。
而且,對于慰安所這類有特殊創傷感的歷史遺址,如何展示也是問題。如果簡單地圈起來,掛個牌子,或恢復內部陳設建立紀念館,讓民眾參觀(包括廣大青少年),效果如何,教育意義何在,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僅僅只是在傷疤上“撒鹽”,恐怕不一定是個好方法。
并且,如果說是“遺址”就一定要恢復的話,那些“跑馬廳”、“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地方,又該怎么辦呢?還有“英租界”、“法租界”,又該怎么辦呢?
那么,在今天,我們應該怎樣保護歷史遺址和文物呢?
其一,對于有重要歷史意義和歷史價值的地方,精心安排,盡可能恢復原址原貌。像上海的“一大”、“二大”會址,思南路上的“周公館”,“宋慶齡故居”,“魯迅故居”等等,恢復得越真實越好,讓參觀者感到“身臨其境”。
其二,對于有些已經不能恢復的遺址和文物,可以就近建立紀念館、豎立紀念牌,以告示人們,這里是某事件的發生地。比如中共四大會址,當年已毀于日軍戰火,虹口區就近在四川北路綠地建立了“中共四大紀念館”,很好地進行了展示。另一處“五卅烈士墓”,也被日軍炸毀,原地已是一個小學所在地,就通過豎立紀念牌的方式進行展示。
其三,可以更多地通過現代技術手段,比如多媒體影像展示的方式,進行更有效、更合理的展示。對一些遺址和文物,可以多角度地拍攝下來,無論是展示還是研究、保存,都極為方便,輔之于文字記錄,可以做得十分詳盡、真實。不必非得通過實物、實景的方式展現。比如最近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與騰訊網共同制作的多媒體《上海抗日救亡分布圖》正式上線公布,以直觀、科學的時空分布圖作為表現形式,很好地再現了歷史。像“大一沙龍”之類,完全可以采用這種情況,而不必非得實物實景,效果可能也更好一些。
保護“遺址”、“文物”應該還有很多方法,我看重要的是要有這個意識和共識,特別是對一些有重要教育作用、體現正能量價值的,更要做好保護工作。同時采取更符合實際、符合參觀心理、符合節儉實用原則的方式,思路可以拓寬一些,方式可以多樣一些,不必完全用一些舊有模式,這樣一來才能做到既有紀念意義,又有教育意義、激勵意義。
責任編輯:M005文章來源:中國廣播網
下一條:文化地標大可喜新不厭舊上一條:戲曲傳承,好政策下應更有作為
相關信息
精彩展示
評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