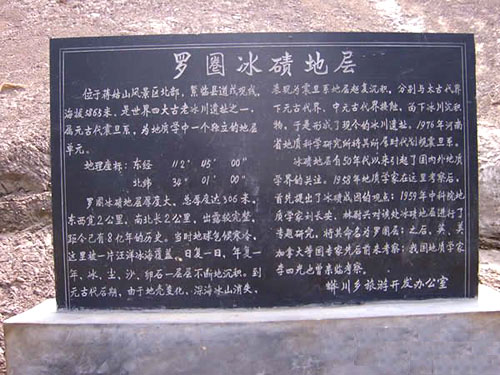-
沒有記錄!
水經注:水色清媚三里河(一)
2013/11/9 17:26:03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結束了對沙河上游溪澗的采訪,根據從前走訪平原水系的經驗,我對三里河是否有水,不敢抱太大期望。
2009年1月5日,和張店鄉水利站技術員李軍來一起,乘車自魯山縣城一路向北,探訪這個鄉的水源河脈。出城第一站,到李村行政村的楝樹莊自然村,村東有將相河上源老龍潭。聽人說,早先這片曠野郁郁蒼蒼,曾經涵養得泉流縱橫,匯成百多畝大的深潭,黑釅釅看不到底,泉水南流,成一道將相河。汽車在曾經的老龍潭北岸停下,筆者見到的只是潭水的遺跡:洪水沖刷出道道橫線的土岸,潭水浸漬而成的干灘泥地,瞎枯的巨眼一樣望向天空。北邊不遠,碎石機仍然不依不饒地轟響著,滾滾煙塵飄蕩而來,這景象讓人徒生惆悵。好在數十座石灰窯已全部停產,如果假以時日,山野恢復草木青青的樣貌,老龍潭也許還會重現吧。
折回大路北行,終于追上了一條水質清澈的河溝。別看這是一條地圖上找不見的無名河溝,反倒水流淙淙,一年四季都不停息,是三里河的常年溪源。漫長的冬季無雨雪,溝水卻出人意料的好。水幅兩三米,深處及膝,淺處一尺多,無橋不渡。河溝里一灣一灣都是三四把頭兒粗的楊樹。到上游盤崗繞嶺,一路串起三個小水庫。有了水的澤潤,山垛、田地、村落,立馬變得清媚亮眼起來。
唐溝水庫在郭莊行政村,建成于1979年12月,設計蓄洪量15萬立方米,澆地1000畝。水庫建成后一直沒配套,到2008年方才修了一道水渠,澆地二三百畝。眼前水面兩三畝,深2米左右。上游河溝常年有水,天再旱壩下溢水也有兩三寸管量,到白象店并入三里河。
與唐溝一水相連的王灣水庫,建成于1978年5月,總庫容138萬立方米,配建8座提灌站,設計澆地1180畝,屬小型一類水庫。因年久失修,配套工程毀廢,供村民飲牛驢喂豬羊之外,澆地400多畝。再往上去地勢抬升,二三公里就到了溝水源頭的邢溝行政村。最高的明泉在半坡陽自然村北山坡上出露,兩寸管量,流到坡根,進入半坡陽水庫。水庫修成于1970年代,水面約25畝,水深八九米。雨季浮水和泉溪不是主要水源,庫底有好幾處暗水泉流。當年曾修有兩個提灌站,千米長渠如二龍吐須,澆灌幾百畝田地,可惜后來水渠毀壞了,眼下能澆的也就五六畝地。
半坡陽是一個古老的村落,村中有三處清代民居。其中一進三的楊姓古宅保存尚好。大門西南不遠有眼古井,光滑的井臺、汲水的轆轤,都是先人手漬的舊物。井北幾米處,有座立于咸豐年間的貞節牌坊,匾額題字,坊眉雕花,清晰可辨。聽村黨支部書記王大利說,這座牌坊原有4層,“文革”中扒掉兩層。現在的半坡陽,人上千口,年輕人都出外打工,誰也不死守著崗田薄地過日子了。從生產工具到生產方式,30年間發生了躍遷式的變化。“鐮是一塊鐵,全指胳膊曳”的傳統農耕時代一去不復返。隨著生活習俗的變遷,貞節牌坊也就成了純粹的文物。
說到村名,志書上有兩說:一是村落建在山陽半坡處而得名;二是坡上有天生青石酷似羊形而得名。可在半坡陽村民口中,還有個代代相傳的典故:村東800米的山坡上,天生一對石羊,滿山的石頭都是紅色的,只有這對石羊是白色的,俗稱馬雅石,也就是石英。兩只羊大小顏色都和真羊一樣,相隔不足一米,看上去活像一對兒吃飽了反芻的臥羊。過石羊往東去一公里,有大石門、小石門、白馬,也是石英象形石。傳說早年西鄉人起五更翻山去梁洼趕集,一過石羊,就看見前邊四五十米有羊領路,羊脖子里的鈴鐺一路叮叮當當。鬼神皆避。一直領過大石門、小石門,到十字路口那兒,才看不見羊聽不見聲了。大石門中間有塊兩尺多高、丈把長的紅色火焦石,傳說那是一道門拴。一到晚上,就會自動橫過來把石門堵住,沒有石羊領路,人是過不去的。小石門旁邊有塊鷹咀石,頭朝東,尾朝西,有風水先生說,這只鷹吃東方屙西方,富半坡陽窮梁洼。那邊的人聽說后,就用炸藥把它給崩了。裂開的石頭堵住路,到現在小石門那兒只能過手扶拖拉機,過不了大車。這是半坡陽人的說法。到了劉潭村人的嘴里,就成了另一個版本:劉潭自然村翻過去山就是梁洼鎮的泉上村。劉潭村東的山坡上也有一羊形巨石,頭朝劉潭,屁股朝泉上。劉潭村的人一直很窮,而泉上的日子年年都比這邊好。劉潭人開始犯嘀咕,琢磨來琢磨去,就覺著是石羊壞了村里的風水,它“吃劉潭,屙泉上”,不把它除了,劉潭永遠都得受窮。于是就攛掇人把石羊炸成了一堆亂石頭。
看來無論是哪里的曠山野水老石頭,與人處久了,都會成為人的近鄰和至親,不但有名有姓,有情仇好惡,還有鼻子有眼有故事。正是這摞了一層又一層的故事,才使得一代人與一代人呼吸相聞,才使得這一道山水與那一道山水情意相連吧?(曲令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