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推薦

樊鐘秀設(shè)計(jì)滅
為生計(jì)所迫逃亡到陜西后,樊鐘秀設(shè)計(jì)消滅掉欺負(fù)妹妹的黃..[詳細(xì)]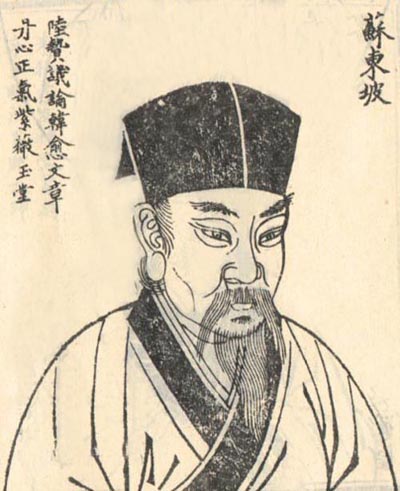
蘇軾與烏臺(tái)詩
蘇軾像(資料圖片)詩文惹禍端蘇軾,字子瞻,號(hào)東坡居士,北..[詳細(xì)]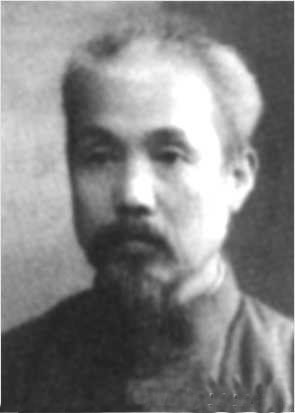
徐玉諾三訪葉
徐玉諾照片(資料圖片)人們多知徐玉諾與郭紹虞的友誼,而..[詳細(xì)]
熱點(diǎn)關(guān)注
專題推薦
-
沒有記錄!
熱點(diǎn)排行
蘇軾是“文人”嗎
2014/12/9 14:44:44 點(diǎn)擊數(shù): 【字體:大 中 小】
今天的書畫界、學(xué)術(shù)界,多把蘇軾、李公麟、黃庭堅(jiān)等稱作“文人”;他們的書畫,也被稱作“文人畫”、“文人書法”;他們的雅集活動(dòng),更被稱作“文人雅集”。總之,宋代讀書界的代表人物,一概地都是“文人”。然而,蘇軾們真的是“文人”嗎?他們樂意別人、包括當(dāng)時(shí)人和作為后人的我們稱他們?yōu)?ldquo;文人”嗎?
顧炎武《日知錄》“文人之多”一節(jié)中提到:“宋劉摯之訓(xùn)子孫,每曰:‘士當(dāng)以器識(shí)為先,一號(hào)為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可見,宋代的讀書人,其主流是恥為文人的。
我們來看蘇軾自己的文字,他從主流面所評(píng)論的讀書人,幾乎沒有稱“文人”的,而都稱“士”、“士人”、“士大夫”。如《書李承宴墨》:“近時(shí)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盡其技。”《書王君佐所蓄墨》:“今時(shí)士大夫多貴蘇浩然墨。”《書外曾祖程公逸事》:“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yuǎn)宦,官闕,選士人有行義者攝。”《跋司馬溫公布衾銘后》:“士之得道者,視死生禍福,如寒暑晝夜,不知所擇,況膏梁脫粟文繡布褐之間哉!”《書黃道輔品茶要錄后》:“博學(xué)能文,淡然精深,有道之士也。”《題劉景文所收歐陽公書》:“乃知士大夫進(jìn)易而退難,可以為后生汲汲者之戒。”《題歐陽帖》:“以是知士非進(jìn)身之難,乞身之難也。”《跋歐陽文忠公書》:“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于心……”《又跋漢杰畫山二首》:“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跋李伯時(shí)卜居圖》:“士大夫逢時(shí)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歸田古今難事也。”《凈因院畫記》:“蓋達(dá)士之所寓也歟。”《書杜氏藏諸葛筆》:“善待諸葛氏,如遇士人,以故為盡力,常得其善筆。”《書吳說筆》:“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工書人不能用,若便于工書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書王定國贈(zèng)吳說帖》:“去國八年,歸見中原士大夫。”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對(duì)于真正的文人,他又如何稱謂呢?由于在北宋的讀書界,文人并不被看重,所以,他一般不稱“文人”,但也決不稱“士”、“士人”、“士大夫”。如《記子美八陣圖詩》稱杜甫“真書生習(xí)氣也”;《書朱象先畫后》稱閻立本“始以文學(xué)進(jìn)身,卒蒙畫師之恥”。包括李賀也說:“若個(gè)書生萬戶侯。”一言以蔽之,在唐宋,尤其是宋,文人們決不把自己歸屬于士人,而士人們更不會(huì)把自己歸屬于文人。
雖然,我們習(xí)慣上將“文人士大夫”并稱,但實(shí)際上,“文人”和“士人”(即“士大夫”)是兩個(gè)不同的概念。兩者都是文化人、讀書人,但文人以賦詩作文的才華擅長,士人卻以志道弘毅的學(xué)養(yǎng)處世;文人所標(biāo)舉的是個(gè)性的風(fēng)流倜儻,士人所標(biāo)舉的是天下的是非風(fēng)范。
文人,其釋義有二。上古時(shí)指有文德的人,《書·文侯之命》:“追效于前文人。”《疏》:“追行孝道于前世文德之人。”重在德行 。漢魏以后,專指擅長文章詞賦的讀書人,王充《論衡·超奇》:“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相當(dāng)于今天的“文秘”。曹丕《典論·論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則衍而為以吟風(fēng)弄月、傷懷感時(shí)的文采辭藻為勝的人了,相當(dāng)于今天的“文學(xué)家”。今天,更發(fā)展為囊括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研究的“文化人”了,包括“文學(xué)家”和“文史專家”。士人,在北宋之前有多種釋義,包括一切從事耕種和軍旅的青壯年男子、習(xí)文習(xí)武而取得官職者、讀書人,包括作為文人的讀書人和“志道弘毅”的讀書人。北宋以降則專指“志道弘毅”的讀書人。直到晚明,則把兩者的概念混淆,而把一切讀書人、尤其是有文采的讀書人統(tǒng)稱為文人,很少再用“士人”這一名詞了。
并不是說,凡是讀書人、文化人就是文人,無非有些文人“學(xué)優(yōu)而仕”當(dāng)了官,而兼有士人的身份。這是今天專家的認(rèn)識(shí),在唐、宋、元人并不這樣認(rèn)識(shí),包括文人和士人;在顧炎武、黃梨洲、傅青主也不這樣認(rèn)識(shí);在魯迅等同樣不是這樣認(rèn)識(shí)。像蘇洵、司馬光、揚(yáng)補(bǔ)之、吳鎮(zhèn)、顧炎武一類讀書人、文化人,他們的根本身份是士人,做上了官不是文人,做不上同樣不是文人;而像李白、徐渭、董其昌、袁中郎、袁子才一類讀書人、文化人,他們的根本身份是文人,做不上官不是士人,做上了官同樣不是士人。“《通鑒》不載文人”。并不是說《資治通鑒》中沒有記載讀書人、文化人,恰恰相反,讀書人、文化人在《通鑒》中占有重要的比重,但因?yàn)樗麄兊母旧矸荻酁槭咳硕皇俏娜耍哉f“《通鑒》不載文人”。如果以讀書人、文化人即文人,又何來“《通鑒》不載文人”一說?
幾年前,讀到一篇書評(píng),評(píng)的是一位老外的著作《這個(gè)世界被知識(shí)分子弄得一團(tuán)糟》。所指的知識(shí)分子,不包括科學(xué)家、工程師、醫(yī)生,而專指從事文藝創(chuàng)作和文史哲研究的各類專家,大體上相當(dāng)于我們所講的文人。文人無行,聞一多稱作“詩人的蠻橫”,一兩個(gè),可以使這個(gè)世界更精彩;普遍了,這個(gè)世界就被“弄得一團(tuán)糟”。所以,自古至今,文人不僅與有知識(shí)、有文化的科學(xué)家、工程師、醫(yī)生不是同一類人,更與士人不是同一類人。兩者的區(qū)別,不在于有沒有文化知識(shí),尤其是吟詩作賦的才華,而在于,實(shí)的方面,所從事的具體工作,是賣弄風(fēng)雅還是經(jīng)時(shí)濟(jì)世;虛的方面,有沒有文化的學(xué)養(yǎng),尤其是“志道弘毅”的器識(shí)。顧炎武以文人為“不識(shí)經(jīng)術(shù),不通古今”,也就是缺少“器識(shí)”的根本,故其骨頭亦軟。魯迅認(rèn)為文人的本性即“奴性”,梁?jiǎn)⒊瑒t稱作“上流無用,下流無恥”,正是魯迅所指“當(dāng)上了奴才”和“沒有當(dāng)上奴才”的兩種文人的不同表現(xiàn)。昔人評(píng)李白、蘇軾之異同,認(rèn)為:“太白有東坡之才,無東坡之學(xué)。”“才”者,詩文的才華;“學(xué)”者,經(jīng)濟(jì)的學(xué)識(shí)。雖然,蘇軾也以賦詩作文的才華名世,但他更以道德忠義的學(xué)養(yǎng)貫日月而妙天下,他是士人,決不是文人。顧炎武甚至認(rèn)為,韓愈如果不做詩文,其“原道”的形象將更高大。
混淆士人和文人的概念,誣蘇軾們?yōu)槲娜耍菑耐砻魇⑿械摹?ldquo;明三百年養(yǎng)士之不精”,造成了讀書界的“何文人之多”,士風(fēng)大壞,儒學(xué)淡泊,文人無行,不可收拾。文人們一面離經(jīng)叛道,推出與士人迥然相反的價(jià)值觀,如士人“以天下是非風(fēng)范為己任”(漢李膺)、不計(jì)個(gè)人的榮辱得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宋范仲淹);他們則鼓吹人活著就是為自己,不為自己而為別人、為社會(huì),這一輩子就白活了,“雖夷齊等同塵埃,雖堯舜等同秕糠”(李贄);人生一世,“五大真樂”、“三大敗興”,就是個(gè)人能否盡興地吃喝玩樂,“破國亡家不與焉”(袁宏道)。一面又把與他們的價(jià)值觀根本不同的士人也稱作文人,如董其昌明確提出“文人之畫”的觀點(diǎn),把從唐王維到“元四家”的繪畫稱作“文人畫”。事實(shí)上,不要說唐代,就是宋代、元代,根本就沒有“文人畫”這個(gè)術(shù)語。“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文人雖然很早就有了,但迄止晚明之前,只有畫家畫、畫工畫、士人畫,而絕無文人畫,不是說當(dāng)時(shí)的文人中沒有一個(gè)偶爾也畫畫的,至少他們的畫根本不成氣候。蘇軾所講的是“士人畫”,已如前述;吳鎮(zhèn)、黃公望所講的,同樣是“士人畫”、“士夫畫”而不是“文人畫”。唯一的例外,是南宋鄧椿在《畫繼》中所講的一段話:“畫者,文之極也。故古今之人,頗多著意。張彥遠(yuǎn)所次歷代畫人,冠裳大半。唐則少陵題詠,曲盡形容,昌黎作記,不遺毫發(fā)。本朝文忠歐公、三蘇父子、兩晁兄弟、山谷、后山、宛邱、淮海、月巖,以至漫仕、龍眠,或品評(píng)精高,或揮染超拔。然則畫者,豈獨(dú)藝之云乎?難者以為自古文人,何止數(shù)公……”云云。但是一,這里所側(cè)重的,并不是繪畫的創(chuàng)作,而是繪畫的評(píng)論,所提到的人物,除蘇軾、米芾、李公麟外,均非“揮染超拔”的“畫人”,而是“品評(píng)精高”的觀畫人。其二,當(dāng)時(shí)對(duì)繪畫的評(píng)論,多用詩文的形式展開,不僅文人杜甫用詩文評(píng)賞繪畫,士人韓愈、蘇軾、歐陽修、黃庭堅(jiān)也用詩文評(píng)賞繪畫,由于不是從學(xué)養(yǎng)的有還是無來論證他們不同的身份,而是從詩文評(píng)畫的精高來論證他們共同的貢獻(xiàn),所以,用“文人”來統(tǒng)稱之,雖然不妥,但也是不得已而為之。這就像我們討論20世紀(jì)的書法,不妨把毛主席、弘一與白蕉一并稱作書法家,但論根本的身份,毛主席是政治家、思想家,弘一是高僧。同樣,談?wù)撛娢臅r(shí),不妨把韓愈、歐陽修、蘇軾們一并稱作文人,但論根本的身份,他們都是士人。
但晚明之后的文人們把蘇軾們也稱作文人,性質(zhì)就完全不同了。大抵任何創(chuàng)新者,包括打著“創(chuàng)新”旗號(hào)的腐敗者,都要把自己與前賢等同在一起。或者將“我”向“他”靠,如“四人幫”明明搞的是封建法西斯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根本不同,卻把自己說成也是“馬克思主義”;或者拉“他”向“我”靠,如晚明的文人們把蘇軾等一大批士人稱作是“文人”。其用心,就是通過誣蘇軾為文人,推崇其才華而泯滅其學(xué)養(yǎng),進(jìn)而放縱自己的個(gè)性人欲。今天美協(xié)畫院的某些當(dāng)權(quán)者,把吳冠中“解散美協(xié)畫院體制”的“真實(shí)意思”,解釋為“把美協(xié)畫院做大做強(qiáng)”與之同一套路。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且不論這一觀點(diǎn)是否正確,讀書人在社會(huì)各階層心目中的印象之高則是毋庸置疑的。從而,不僅士人以天下是非風(fēng)范為己任,可以表率社會(huì)的風(fēng)氣;文人以個(gè)性人欲訴求為天理,同樣可以表率社會(huì)的風(fēng)氣。士人、文人,各有優(yōu)長,也各有缺陷。士人可敬、可畏,淪于迂腐則可厭;文人可愛、可憐,淪于無恥則可恨。這個(gè)“無恥”,在士人看作貶義詞,“行己有恥”,是圣人的教誨;但在文人,卻是褒義詞,如袁中郎便說過,人生的最大快樂就是“恬不知恥”地享受個(gè)人物質(zhì)的和精神的人欲,“用足政策”死去后不為別人、社會(huì)留下一分錢。所以,當(dāng)讀書界以士人為主流,文人只是少數(shù),士人為社會(huì)的和諧織成了一塊錦,揚(yáng)雄、李白、周邦彥等文人便為這塊錦上添加了幾朵美麗的花。而當(dāng)讀書界以文人為主流,士人成了少數(shù),社會(huì)和諧的錦便被光怪陸離的花搞得支離破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顧炎武),文化的腐敗,結(jié)果導(dǎo)致的便是“國將不國”。顧炎武有“亡國、亡天下”之說,“亡國”就是政權(quán)的更迭,“亡天下”就是文化的腐敗,讀書人不僅不再成為構(gòu)建社會(huì)和諧的正能量,反而成為敗壞社會(huì)和諧的負(fù)能量。明朝的覆滅,有多方面的原因,軍隊(duì)的腐敗,政治的腐敗,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場(chǎng)的腐敗……根本的則是因?yàn)槲幕母瘮 n櫻孜錃w于“何文人之多”,文人之多又歸于李贄“叛圣人之教”的“異端邪說”,“異端邪說”的熾興又歸于王陽明的“心學(xué)”。梁?jiǎn)⒊瑒t認(rèn)為,陽明心學(xué)對(duì)于解放程朱理學(xué)的束縛還是有功的,但對(duì)于李贄以后“上流無用,下流無恥”的文人們,那些“花和尚”,確是“一個(gè)也不能饒恕的”。
一言以蔽之,把蘇軾們稱作“文人”,正標(biāo)志著從此拉開了文化腐敗的序幕。從此,讀書界豐富了文人的性靈,卻蕩然了士人的風(fēng)骨。所以,“天下興亡”的責(zé)任也就需要由“匹夫之賤”來承當(dāng)了。
我們看看晚明的社會(huì),內(nèi)亂外患,風(fēng)雨飄搖,那些文人們?cè)诟墒裁茨兀吭诔某瑝m脫俗,逍遙于市井風(fēng)月;在野的憤世嫉俗,放蕩于市井風(fēng)月,酒肆、茶樓、妓院,盛極一時(shí),是發(fā)達(dá)者奢靡的場(chǎng)所,同時(shí)也是失意者放浪的場(chǎng)所。李闖入京,清移明祚,“開門迎賊者生員,縛官投偽者生員”,風(fēng)雅所致的,竟是斯文掃地如此!將蘇軾與之同伍為“文人”,誣蘇軾亦甚矣!所以,不扭轉(zhuǎn)“蘇軾是文人”的觀念,對(duì)讀書人的才華認(rèn)識(shí)縱然有益,對(duì)讀書人的學(xué)養(yǎng)認(rèn)識(shí)則必定有害。而沒有對(duì)讀書人應(yīng)有的學(xué)養(yǎng)即社會(huì)責(zé)任、社會(huì)擔(dān)當(dāng)?shù)恼J(rèn)識(shí),文化的腐敗便沒有底止。一切腐敗,始于文化的腐敗,亦莫甚于文化的腐敗。即使在今天,也還是如此。無非相比于其他的腐敗之有法律條文可依從而可治,文化的腐敗是無法可依的,無法可依也就是不犯法,不犯法也就沒法治。
今天,當(dāng)我們口口聲聲稱蘇軾是“文人”的時(shí)候,或許正自知或不知地繼續(xù)推動(dòng)著晚明文人的文化腐敗。當(dāng)然,這絕對(duì)不犯法。在士人風(fēng)骨支撐著社會(huì)之錦的時(shí)候,它還可以為之增添更優(yōu)雅的花色。
顧炎武《日知錄》“文人之多”一節(jié)中提到:“宋劉摯之訓(xùn)子孫,每曰:‘士當(dāng)以器識(shí)為先,一號(hào)為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可見,宋代的讀書人,其主流是恥為文人的。
我們來看蘇軾自己的文字,他從主流面所評(píng)論的讀書人,幾乎沒有稱“文人”的,而都稱“士”、“士人”、“士大夫”。如《書李承宴墨》:“近時(shí)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盡其技。”《書王君佐所蓄墨》:“今時(shí)士大夫多貴蘇浩然墨。”《書外曾祖程公逸事》:“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yuǎn)宦,官闕,選士人有行義者攝。”《跋司馬溫公布衾銘后》:“士之得道者,視死生禍福,如寒暑晝夜,不知所擇,況膏梁脫粟文繡布褐之間哉!”《書黃道輔品茶要錄后》:“博學(xué)能文,淡然精深,有道之士也。”《題劉景文所收歐陽公書》:“乃知士大夫進(jìn)易而退難,可以為后生汲汲者之戒。”《題歐陽帖》:“以是知士非進(jìn)身之難,乞身之難也。”《跋歐陽文忠公書》:“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于心……”《又跋漢杰畫山二首》:“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跋李伯時(shí)卜居圖》:“士大夫逢時(shí)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歸田古今難事也。”《凈因院畫記》:“蓋達(dá)士之所寓也歟。”《書杜氏藏諸葛筆》:“善待諸葛氏,如遇士人,以故為盡力,常得其善筆。”《書吳說筆》:“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工書人不能用,若便于工書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書王定國贈(zèng)吳說帖》:“去國八年,歸見中原士大夫。”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對(duì)于真正的文人,他又如何稱謂呢?由于在北宋的讀書界,文人并不被看重,所以,他一般不稱“文人”,但也決不稱“士”、“士人”、“士大夫”。如《記子美八陣圖詩》稱杜甫“真書生習(xí)氣也”;《書朱象先畫后》稱閻立本“始以文學(xué)進(jìn)身,卒蒙畫師之恥”。包括李賀也說:“若個(gè)書生萬戶侯。”一言以蔽之,在唐宋,尤其是宋,文人們決不把自己歸屬于士人,而士人們更不會(huì)把自己歸屬于文人。
雖然,我們習(xí)慣上將“文人士大夫”并稱,但實(shí)際上,“文人”和“士人”(即“士大夫”)是兩個(gè)不同的概念。兩者都是文化人、讀書人,但文人以賦詩作文的才華擅長,士人卻以志道弘毅的學(xué)養(yǎng)處世;文人所標(biāo)舉的是個(gè)性的風(fēng)流倜儻,士人所標(biāo)舉的是天下的是非風(fēng)范。
文人,其釋義有二。上古時(shí)指有文德的人,《書·文侯之命》:“追效于前文人。”《疏》:“追行孝道于前世文德之人。”重在德行 。漢魏以后,專指擅長文章詞賦的讀書人,王充《論衡·超奇》:“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相當(dāng)于今天的“文秘”。曹丕《典論·論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則衍而為以吟風(fēng)弄月、傷懷感時(shí)的文采辭藻為勝的人了,相當(dāng)于今天的“文學(xué)家”。今天,更發(fā)展為囊括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研究的“文化人”了,包括“文學(xué)家”和“文史專家”。士人,在北宋之前有多種釋義,包括一切從事耕種和軍旅的青壯年男子、習(xí)文習(xí)武而取得官職者、讀書人,包括作為文人的讀書人和“志道弘毅”的讀書人。北宋以降則專指“志道弘毅”的讀書人。直到晚明,則把兩者的概念混淆,而把一切讀書人、尤其是有文采的讀書人統(tǒng)稱為文人,很少再用“士人”這一名詞了。
并不是說,凡是讀書人、文化人就是文人,無非有些文人“學(xué)優(yōu)而仕”當(dāng)了官,而兼有士人的身份。這是今天專家的認(rèn)識(shí),在唐、宋、元人并不這樣認(rèn)識(shí),包括文人和士人;在顧炎武、黃梨洲、傅青主也不這樣認(rèn)識(shí);在魯迅等同樣不是這樣認(rèn)識(shí)。像蘇洵、司馬光、揚(yáng)補(bǔ)之、吳鎮(zhèn)、顧炎武一類讀書人、文化人,他們的根本身份是士人,做上了官不是文人,做不上同樣不是文人;而像李白、徐渭、董其昌、袁中郎、袁子才一類讀書人、文化人,他們的根本身份是文人,做不上官不是士人,做上了官同樣不是士人。“《通鑒》不載文人”。并不是說《資治通鑒》中沒有記載讀書人、文化人,恰恰相反,讀書人、文化人在《通鑒》中占有重要的比重,但因?yàn)樗麄兊母旧矸荻酁槭咳硕皇俏娜耍哉f“《通鑒》不載文人”。如果以讀書人、文化人即文人,又何來“《通鑒》不載文人”一說?
幾年前,讀到一篇書評(píng),評(píng)的是一位老外的著作《這個(gè)世界被知識(shí)分子弄得一團(tuán)糟》。所指的知識(shí)分子,不包括科學(xué)家、工程師、醫(yī)生,而專指從事文藝創(chuàng)作和文史哲研究的各類專家,大體上相當(dāng)于我們所講的文人。文人無行,聞一多稱作“詩人的蠻橫”,一兩個(gè),可以使這個(gè)世界更精彩;普遍了,這個(gè)世界就被“弄得一團(tuán)糟”。所以,自古至今,文人不僅與有知識(shí)、有文化的科學(xué)家、工程師、醫(yī)生不是同一類人,更與士人不是同一類人。兩者的區(qū)別,不在于有沒有文化知識(shí),尤其是吟詩作賦的才華,而在于,實(shí)的方面,所從事的具體工作,是賣弄風(fēng)雅還是經(jīng)時(shí)濟(jì)世;虛的方面,有沒有文化的學(xué)養(yǎng),尤其是“志道弘毅”的器識(shí)。顧炎武以文人為“不識(shí)經(jīng)術(shù),不通古今”,也就是缺少“器識(shí)”的根本,故其骨頭亦軟。魯迅認(rèn)為文人的本性即“奴性”,梁?jiǎn)⒊瑒t稱作“上流無用,下流無恥”,正是魯迅所指“當(dāng)上了奴才”和“沒有當(dāng)上奴才”的兩種文人的不同表現(xiàn)。昔人評(píng)李白、蘇軾之異同,認(rèn)為:“太白有東坡之才,無東坡之學(xué)。”“才”者,詩文的才華;“學(xué)”者,經(jīng)濟(jì)的學(xué)識(shí)。雖然,蘇軾也以賦詩作文的才華名世,但他更以道德忠義的學(xué)養(yǎng)貫日月而妙天下,他是士人,決不是文人。顧炎武甚至認(rèn)為,韓愈如果不做詩文,其“原道”的形象將更高大。
混淆士人和文人的概念,誣蘇軾們?yōu)槲娜耍菑耐砻魇⑿械摹?ldquo;明三百年養(yǎng)士之不精”,造成了讀書界的“何文人之多”,士風(fēng)大壞,儒學(xué)淡泊,文人無行,不可收拾。文人們一面離經(jīng)叛道,推出與士人迥然相反的價(jià)值觀,如士人“以天下是非風(fēng)范為己任”(漢李膺)、不計(jì)個(gè)人的榮辱得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宋范仲淹);他們則鼓吹人活著就是為自己,不為自己而為別人、為社會(huì),這一輩子就白活了,“雖夷齊等同塵埃,雖堯舜等同秕糠”(李贄);人生一世,“五大真樂”、“三大敗興”,就是個(gè)人能否盡興地吃喝玩樂,“破國亡家不與焉”(袁宏道)。一面又把與他們的價(jià)值觀根本不同的士人也稱作文人,如董其昌明確提出“文人之畫”的觀點(diǎn),把從唐王維到“元四家”的繪畫稱作“文人畫”。事實(shí)上,不要說唐代,就是宋代、元代,根本就沒有“文人畫”這個(gè)術(shù)語。“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文人雖然很早就有了,但迄止晚明之前,只有畫家畫、畫工畫、士人畫,而絕無文人畫,不是說當(dāng)時(shí)的文人中沒有一個(gè)偶爾也畫畫的,至少他們的畫根本不成氣候。蘇軾所講的是“士人畫”,已如前述;吳鎮(zhèn)、黃公望所講的,同樣是“士人畫”、“士夫畫”而不是“文人畫”。唯一的例外,是南宋鄧椿在《畫繼》中所講的一段話:“畫者,文之極也。故古今之人,頗多著意。張彥遠(yuǎn)所次歷代畫人,冠裳大半。唐則少陵題詠,曲盡形容,昌黎作記,不遺毫發(fā)。本朝文忠歐公、三蘇父子、兩晁兄弟、山谷、后山、宛邱、淮海、月巖,以至漫仕、龍眠,或品評(píng)精高,或揮染超拔。然則畫者,豈獨(dú)藝之云乎?難者以為自古文人,何止數(shù)公……”云云。但是一,這里所側(cè)重的,并不是繪畫的創(chuàng)作,而是繪畫的評(píng)論,所提到的人物,除蘇軾、米芾、李公麟外,均非“揮染超拔”的“畫人”,而是“品評(píng)精高”的觀畫人。其二,當(dāng)時(shí)對(duì)繪畫的評(píng)論,多用詩文的形式展開,不僅文人杜甫用詩文評(píng)賞繪畫,士人韓愈、蘇軾、歐陽修、黃庭堅(jiān)也用詩文評(píng)賞繪畫,由于不是從學(xué)養(yǎng)的有還是無來論證他們不同的身份,而是從詩文評(píng)畫的精高來論證他們共同的貢獻(xiàn),所以,用“文人”來統(tǒng)稱之,雖然不妥,但也是不得已而為之。這就像我們討論20世紀(jì)的書法,不妨把毛主席、弘一與白蕉一并稱作書法家,但論根本的身份,毛主席是政治家、思想家,弘一是高僧。同樣,談?wù)撛娢臅r(shí),不妨把韓愈、歐陽修、蘇軾們一并稱作文人,但論根本的身份,他們都是士人。
但晚明之后的文人們把蘇軾們也稱作文人,性質(zhì)就完全不同了。大抵任何創(chuàng)新者,包括打著“創(chuàng)新”旗號(hào)的腐敗者,都要把自己與前賢等同在一起。或者將“我”向“他”靠,如“四人幫”明明搞的是封建法西斯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根本不同,卻把自己說成也是“馬克思主義”;或者拉“他”向“我”靠,如晚明的文人們把蘇軾等一大批士人稱作是“文人”。其用心,就是通過誣蘇軾為文人,推崇其才華而泯滅其學(xué)養(yǎng),進(jìn)而放縱自己的個(gè)性人欲。今天美協(xié)畫院的某些當(dāng)權(quán)者,把吳冠中“解散美協(xié)畫院體制”的“真實(shí)意思”,解釋為“把美協(xié)畫院做大做強(qiáng)”與之同一套路。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且不論這一觀點(diǎn)是否正確,讀書人在社會(huì)各階層心目中的印象之高則是毋庸置疑的。從而,不僅士人以天下是非風(fēng)范為己任,可以表率社會(huì)的風(fēng)氣;文人以個(gè)性人欲訴求為天理,同樣可以表率社會(huì)的風(fēng)氣。士人、文人,各有優(yōu)長,也各有缺陷。士人可敬、可畏,淪于迂腐則可厭;文人可愛、可憐,淪于無恥則可恨。這個(gè)“無恥”,在士人看作貶義詞,“行己有恥”,是圣人的教誨;但在文人,卻是褒義詞,如袁中郎便說過,人生的最大快樂就是“恬不知恥”地享受個(gè)人物質(zhì)的和精神的人欲,“用足政策”死去后不為別人、社會(huì)留下一分錢。所以,當(dāng)讀書界以士人為主流,文人只是少數(shù),士人為社會(huì)的和諧織成了一塊錦,揚(yáng)雄、李白、周邦彥等文人便為這塊錦上添加了幾朵美麗的花。而當(dāng)讀書界以文人為主流,士人成了少數(shù),社會(huì)和諧的錦便被光怪陸離的花搞得支離破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顧炎武),文化的腐敗,結(jié)果導(dǎo)致的便是“國將不國”。顧炎武有“亡國、亡天下”之說,“亡國”就是政權(quán)的更迭,“亡天下”就是文化的腐敗,讀書人不僅不再成為構(gòu)建社會(huì)和諧的正能量,反而成為敗壞社會(huì)和諧的負(fù)能量。明朝的覆滅,有多方面的原因,軍隊(duì)的腐敗,政治的腐敗,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場(chǎng)的腐敗……根本的則是因?yàn)槲幕母瘮 n櫻孜錃w于“何文人之多”,文人之多又歸于李贄“叛圣人之教”的“異端邪說”,“異端邪說”的熾興又歸于王陽明的“心學(xué)”。梁?jiǎn)⒊瑒t認(rèn)為,陽明心學(xué)對(duì)于解放程朱理學(xué)的束縛還是有功的,但對(duì)于李贄以后“上流無用,下流無恥”的文人們,那些“花和尚”,確是“一個(gè)也不能饒恕的”。
一言以蔽之,把蘇軾們稱作“文人”,正標(biāo)志著從此拉開了文化腐敗的序幕。從此,讀書界豐富了文人的性靈,卻蕩然了士人的風(fēng)骨。所以,“天下興亡”的責(zé)任也就需要由“匹夫之賤”來承當(dāng)了。
我們看看晚明的社會(huì),內(nèi)亂外患,風(fēng)雨飄搖,那些文人們?cè)诟墒裁茨兀吭诔某瑝m脫俗,逍遙于市井風(fēng)月;在野的憤世嫉俗,放蕩于市井風(fēng)月,酒肆、茶樓、妓院,盛極一時(shí),是發(fā)達(dá)者奢靡的場(chǎng)所,同時(shí)也是失意者放浪的場(chǎng)所。李闖入京,清移明祚,“開門迎賊者生員,縛官投偽者生員”,風(fēng)雅所致的,竟是斯文掃地如此!將蘇軾與之同伍為“文人”,誣蘇軾亦甚矣!所以,不扭轉(zhuǎn)“蘇軾是文人”的觀念,對(duì)讀書人的才華認(rèn)識(shí)縱然有益,對(duì)讀書人的學(xué)養(yǎng)認(rèn)識(shí)則必定有害。而沒有對(duì)讀書人應(yīng)有的學(xué)養(yǎng)即社會(huì)責(zé)任、社會(huì)擔(dān)當(dāng)?shù)恼J(rèn)識(shí),文化的腐敗便沒有底止。一切腐敗,始于文化的腐敗,亦莫甚于文化的腐敗。即使在今天,也還是如此。無非相比于其他的腐敗之有法律條文可依從而可治,文化的腐敗是無法可依的,無法可依也就是不犯法,不犯法也就沒法治。
今天,當(dāng)我們口口聲聲稱蘇軾是“文人”的時(shí)候,或許正自知或不知地繼續(xù)推動(dòng)著晚明文人的文化腐敗。當(dāng)然,這絕對(duì)不犯法。在士人風(fēng)骨支撐著社會(huì)之錦的時(shí)候,它還可以為之增添更優(yōu)雅的花色。
責(zé)任編輯:C009文章來源:美術(shù)報(bào)(2014-10-18)
下一條:墨子的“亡國七患”與“憂患意識(shí)”上一條:另一個(gè)蘇軾
相關(guān)信息
沒有記錄!
精彩展示
沒有記錄!
評(píng)論區(qū)
友情鏈接
商都網(wǎng)
中國網(wǎng)河南頻道
印象河南網(wǎng)
新華網(wǎng)河南頻道
河南豫劇網(wǎng)
河南省書畫網(wǎng)
中國越調(diào)網(wǎng)
中國古曲網(wǎng)
博雅特產(chǎn)網(wǎng)
福客網(wǎng)
中國戲劇網(wǎng)
中國土特產(chǎn)網(wǎng)
河南自駕旅游網(wǎng)
中華姓氏網(wǎng)
中國旅游網(wǎng)
中國傳統(tǒng)文化藝術(shù)網(wǎng)
族譜錄
文化遺產(chǎn)網(wǎng)
梨園網(wǎng)
河洛大鼓網(wǎng)
剪紙皮影網(wǎng)
中國國家藝術(shù)網(wǎng)
慶陽民俗文化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