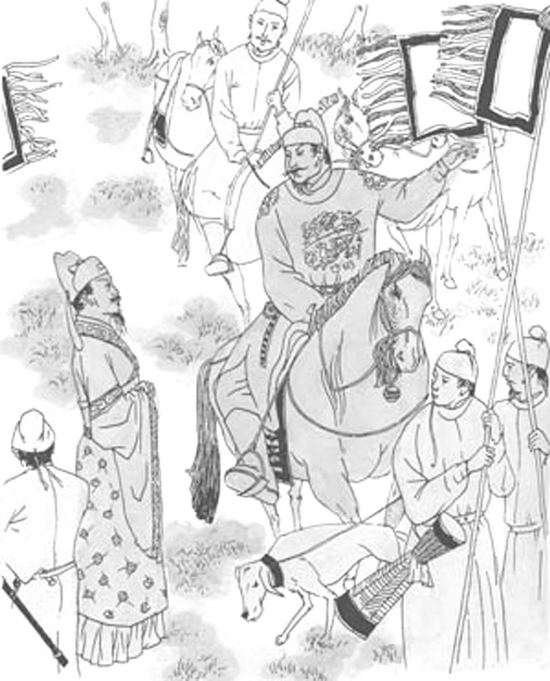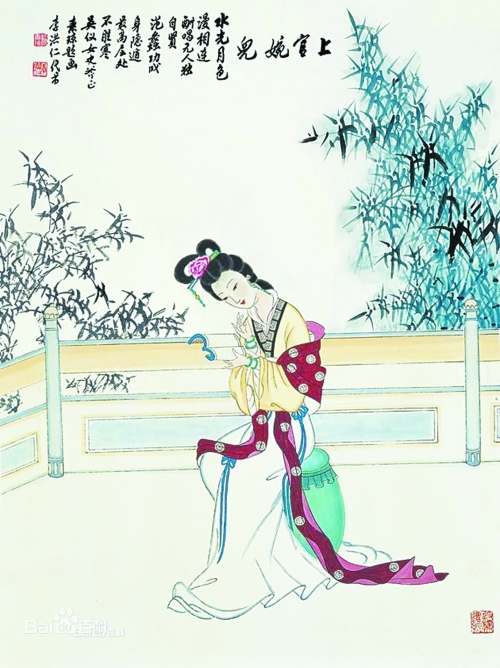-
沒有記錄!
五四瑣憶
2015/1/6 11:49:09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站在八十三歲的山坡上,來回顧六十年前的往事,真如癡人說夢。只得姑妄言之了。
五四運動在中國史上,確實是一件地覆天翻的大事。不管是當時衛道的遺老,也不管是“離經叛道”的青年,對五四驚雷的震撼,能無動于衷的,可說少有。
那時,我只恨自己的“八字”不好:生在豫西“八百里地伏牛山”的腹地。和我同年,并先后在中學同學的一位大學者,在北京大學畢業后,又從美國裝一肚子洋墨水回來,到母校--河南省立第二中學作“學術”講演時,我還在那個中學的教室里啃油印講義呢!
那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慶祝大戰勝利游行時,唱著歌。歌中有兩段:
沉沉大千,彈雨硝煙,而今一旦豁然。伸我公理,屈彼強權協約齊祝凱旋……
在這慶祝別人的凱歌聲中,游行隊伍里,爆發出雷鳴的怒吼:“還我青島!”“抵制日貨!”……
中國的青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被德國帝國主義者霸占。歐戰結束了,德國是戰敗國,照理應該物歸原主,交還中國。可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從中國奪去了,所以中國青年學生游行,要求巴黎和會把青島交還中國。這是五四運動的導火線。中國是一個弱國,當時對付日本的辦法之一,是抵制日貨。
同學們以前凡購有日貨的,都紛紛交出,當眾燒毀。當時最普遍的是操衣領內的硬領,潔白、光亮,是化學制品,全是日貨。同學們爭先恐后地取下,當眾投入火中燒了。那東西象火藥一樣,見火就著。當時把日貨也稱作“仇貨”。對于宰割我們的敵人,那種萬眾一心、同仇敵愾的情感,占據了整個青年的心。
隨著時間的推移,運動的性質和規模,也日益擴大和深入。由抵制日貨、反對帝國主義,進而擴大到反對封建制度,要求民主,要求個性解放、社交公開、言論自由、婚姻自由、反對文言,主張白話等等。凡屬舊的,一概反對,凡屬新的,一律歡迎。
在抵制日貨上,我不但參加學生會,到商店檢查日貨,還從早到晚在宋門守城門,檢查日貨。遇有貨物入城,帖上封條,登記。過后,學生會按登記表前往啟封、檢查。不經檢查,商人不準私自啟封。否則,以盜運日貨論。
除此之外,還參加宣傳隊,沿街向民眾宣傳當前形勢,呼吁各界,一致奮起,參加救國救民運動。
五四運動的怒濤,把我從讀死書的課堂里沖出來,打著“抵制日貨”、“傳播新思想”、“介紹新文化”的旗子,在街頭宣傳,并賣新出的報刊,如《湘江評論》、《每周評論》、《新青年》等等。
五四期間,我還約了五、六位同學,如關尉華、潘保安、王德蘭等,從乞丐似的生活中,擠出錢來,辦青年學會,出《青年》半月刊。大家親自動手寫文章、辦刊物,并親自到街頭賣。
五四運動的次年初,上海舉行“全國第一屆學生聯合會代表大會”,我被選為河南學生代表,到上海開會。這是我第一次跨出省界,到了當時的“十里洋場”,對那光怪陸離的繁華世界,所見所聞,無不反感……
我自幼學寫文章時,是以古文為法的,越古奧越好。稍后,大約在民國初年吧,接觸到《飲冰室》的解放體,又大大被它的文筆吸引了。到了五四,又來了一個大轉彎,決然拋棄文言,改用白話。這使得我的國文老師大發雷霆,把我的文章摔了不看,并在課堂上當眾斥責。他在黑板上畫了一個下邊缺點的問號(事實上他不知道問號下還有一點),指著這半截問號斥責道:“這是什么?這是稱鉤喲,連稱鉤都入到文章里,這還有何話可說!……”我默然不語,任他斥責。最后反駁道:“世界是進化的,別人有的,我們沒有,而且又需要,就借來用。無理阻擋時代潮流,是阻擋不住的……”校長趙琴堂,是一位講道理的忠厚長者,當時支持我的意見,這就使我那位國文老師憤而辭職了。至于被反對的白話文,卻如大江東去,匯流到五四的狂濤巨浪里,沖開一切黑暗的閘門,向著一個嶄新的時代,浩浩蕩蕩地流去了……(作者:曹靖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