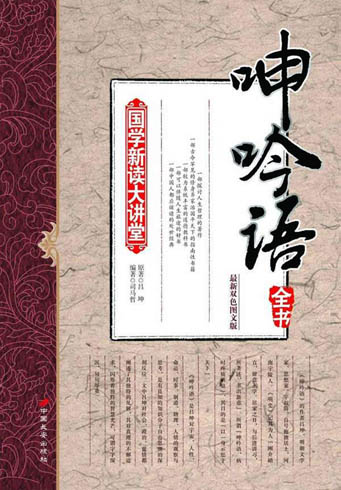-
沒有記錄!
呂坤: 一個人的呻吟
2013/10/25 11:16:19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商丘是中華思想文明的故鄉,因為孔子、莊子、墨子,因為范仲淹、呂坤、楊東明。
思想是一種看不見的智慧。智慧又是什么?這個雙休日讀官場小說《高手過招》,感覺智慧不是來勢洶洶,不是大兵壓境,更不是自命不凡的示威、我行我素的挑釁,或許就只是化干戈為玉帛的一句話,用四兩撥千斤的一股巧勁,樂于度人度己的一種胸懷,于無聲中力挽狂瀾的一種能力。
對牛彈琴不見得不是智慧,大智若愚不見得就是徹底的智慧。表達智慧,是一種智慧;讀懂別人的智慧,才更是一種智慧。
歷史上有一個人的呻吟響徹古今,一己的呻吟成了一個民族的智慧,一個國家的福音。他就是呂坤。
去年,有人建議記者寫寫呂坤,原因是許多思想界人士稱呂坤為“草根圣人”,他的《呻吟語》在臺灣和大陸兩地多次再版,甚至讓許多年輕人愛不釋手。于是開始讀《呻吟語》。但直到今天才敢動筆。
孔子是中國圣人,他思想的視角在廟堂,在君,國貴和,君貴仁,江山才能穩固。呂坤是“草根圣人”,他思想的視角在草野,在民,民安泰,根基牢,社稷才能久安。
呂坤自解其《呻吟語》:“呻吟,病聲也。呻吟語,病時語也。病中疾痛,惟病者知,難與他人道,亦惟病時覺,既愈,旋復忘也。”如同魯迅著《狂人日記》,“狂人”非狂人,“呻吟”也非呻吟。魯迅的“狂人”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憤世吶喊,呂坤的“呻吟”是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熱風語絲。
呂坤的呻吟,是一種思想,一種智慧,與孔子的《論語》一樣,更是一個國家亙古的福音。
【閱讀提示】
選一個切點走近呂坤
周作人曾經選擇呂坤的《演小兒語》,向世人推介這位著名的大明王朝的思想家。
《演小兒語》被稱為我國最早的一部兒歌集,收有包括河南、山西、山東、陜西等地流傳的四十六首兒歌。周作人說:“中國向來缺少為兒童的文學。就是有了一點編纂的著述,也以教訓為主,很少藝術的價值。呂新吾的這一卷《演小兒語》,雖然標語也在‘蒙以養正’,但是知道利用兒童的歌詞,能夠趣味與教訓并重,的確是不可多得的。而且于現在的歌謠研究也不無用處,所以特地把他介紹一下。”
書里收錄的兒歌,如:《鸚哥樂》、《檐前掛》、《為甚過潼關》、《終日不說話》。如:討小狗,要好的。我家狗大卻生癡,不咬賊,只咬雞。如:孩兒哭,哭恁痛。那個打你,我與對命,打我我不嗔,你打我兒我怎禁。如:老王賣瓜,臘臘巴巴。不怕擔子重,只要脊梁硬。不唱,只輕聲品讀,不知已喚醒多少人的童年記憶。
呂坤的《演小兒語》原書一冊,總稱《小兒語》;內計呂得勝(近溪漁隱)的《小兒語》一卷,《女小兒語》一卷,呂坤(抱獨居士)的《續小兒語》三卷,《演小兒語》一卷。前面的五卷書,都是自作的格言,仿佛《三字經》的一部分,也有以諺語為本而改作的。末一卷性質有點不同。小引里說:系采取直隸、河南、山西、陜西的童謠加以修改,為訓蒙之用者。
書前面有嘉靖戊午(1558)呂得勝的序,末有萬歷癸巳(1593)呂坤的書跋,說明他們對于歌謠的意見。序里說:兒之有知而能言也,皆有歌謠以遂其樂,群相習,代相傳,不知作者所自,如梁宋間《盤腳盤》、《東屋點燈西屋明》之類。學焉而于重子無補,余每笑之。夫蒙以養正,有知識時便是養正時也。是俚語者固無害,胡為乎習哉?書跋里說:小兒皆有語,語皆成章,然無謂。先君謂無謂也,更之;又謂所更之未備也,命余續之;既成刻矣,余又借小兒原語而演之。語云,教之嬰孩。
周作人表示:“在我們看來,把好好的歌謠改成箴言,覺得很可惜,但是怪不得三百年以前的古人,而且虧得這本小書,使我們能夠知道在明朝有怎樣的兒歌,可以去留心搜集類似的例,我們實在還應感謝的。”
《演小兒語》被周作人高度評價為“庶幾乎嬰孩一正傳”。 后來,周作人把那四十六首《演小兒語》轉錄在北大《歌謠周刊》上面,旨在希望直隸、河南、山西、陜西各處的人見了書中的歌,記起本地類似的各種歌謠,隨時錄寄。并寄語:“要揀取文詞圓潤自然的,不要用那頭巾氣太重的便好。”
呂坤的《演小兒語》,唯恐“為諸生家言則患其不文,為兒曹家言則患其不俗”,是為“理義身心之學”,旨在“如其鄙俚,使童子樂聞而易曉焉”。
志向中有國家,這是大丈夫胸襟寬廣,因為國家是主權是民主是安身立命之所;關愛里有兒童,這是智者目光遠大,因為孩子是基礎是希望是承載未來的奠基。
周作人以《演小兒語》推介呂坤,讓我們看到了這位“漢奸文人”溫情和博大的一面。呂坤作《演小兒語》收錄兒歌,讓我們看到了這位偉大的思想家平易和平民的一面。
周作人大張旗鼓地評點《演小兒語》,是因為當時的人們看不起兒童歌謠。當今的文化和藝術市場,兒童歌謠、兒童書籍、兒童影視等兒童藝術,依然不為人樂道和開發。這的確應該引發今人深思。
從大音希聲說《呻吟語》之呻吟
呂坤(1536—1618),字叔簡,一字心吾、新吾,自號抱獨居土,商丘寧陵人,明朝文學家、思想家。作品除《呻吟語》、《實政錄》外,還有《夜氣銘》、《招良心詩》、《去偽齋集》等十余種,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刑法、軍事、水利、教育、音韻、醫學等各個方面。
呂坤與沈鯉、郭正域一起,被譽為大明萬歷年間的天下“三大賢”。其性情剛正不阿,其為政清廉愛民,其思想對后世有很大影響,《呂坤全集》被視作文化典籍整理中的原創經典。
因屢次上疏痛陳天下安危,反對當朝“以壓卵之威,行竭澤之計”,力倡寬政待民,暢通言路。但朝廷人心懈弛,奸邪窺伺,呂坤所奏之事每不得報,遂稱疾乞休。
如果一個政客歸隱,可能是去享受財富與安寧,呂坤不同,他并不是真正的歸隱,這個剛介峭直、端方守理的人無法消泯關心民生疾苦、憂慮國家前途的本性,于是著書立說,把自己的洞見用文字表達出來。
《呻吟語》是呂坤積三十年心血,于明萬歷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成書的一部鴻篇巨制。呂坤自己解釋說:“呻吟,病聲也,呻吟語,病時疾痛語也。”“三十年來,所志《呻吟語》凡若干卷,攜以自藥”,“擇其狂而未甚者存之”。
這就是說,呂坤不是無病呻吟閑得無聊寫著玩兒的,他是在展示一個思想者的敏感心靈,是在盡一個政治家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而這樣的事情,政客是不屑于去做的。呂坤做了,他不是一個政客,他是一位官員,一位擁有民本思想的官員。
呂坤在《呻吟語》自序中述其刊刻本書的原因,說他的友人見到此書力勸他公布于世:“吾人之病大都相同,子既志之矣,盍以公人!蓋三益焉:醫病者見子呻吟,起將死病,同病者見子呻吟,醫各有病;未病者見子呻吟,謹未然病。是子以一身示懲于天下,而所壽者眾也。即子不愈,能以愈人,不既多乎?”這才有《呻吟語》流傳后世。
《呻吟語》全書共六卷,前三卷為內篇,后三卷為外篇,分為性命、存心、倫理、談道、修身、問學、應務、養生、天地、世運、圣賢、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廣喻、詞章等十七篇。
《呻吟語》是呂坤對宇宙、人性、命運、時事、制道、物理、人情的觀察與思考,充滿了哲理性,閃爍著智慧之光,字字深沉,句句厚重,真知灼見,時時閃現,警句妙語,不一而足。
“德性以收斂沉著為第一,收斂沉著中又以精明平易為第一。大段收斂沉著人怕含糊,怕深險。淺浮子雖光明洞達,非蓄德之器也。”意思為:人的德性以自我收斂而又沉著冷靜為第一,在收斂而沉著冷靜中,又首推精明能干、平易近人為關鍵。一般來說,收斂而又沉著冷靜的人不喜歡含糊,害怕深險。輕浮淺薄的人,即便表面上豁達開明,也仍然算不上是具備高尚道德的人。
“真機、真味要含蓄,休點破。其妙無窮,不可言喻。所以圣人無言。一犯口頰,窮年說不盡,又離披澆漓,無一些咀嚼處矣。”意思為:人生的真機、真味只有默默細致地去體會才能得到,千萬不要隨意點破。其中的奧妙無窮無盡,是不能用語言文字來表達的。所以,圣人常常保持沉默,從不夸夸其談。若是犯了口舌,長年累月也說不盡,即便說出來,也是眾說紛紜,讓人無法得到其中的要領,也沒有什么耐人尋味的地方。
“性分不可使虧欠,故其取數也常多,曰窮理,曰盡性,曰達天,曰入神,曰致廣大、極高明。情欲不可使贏余,故其取數也常少,曰謹言,曰慎行,曰約己,曰清心,曰節飲食、寡嗜欲。”意思為:人天生的善良本性,是不能讓它虧損欠缺的。所以,它的表現形式通常是多種多樣的。如果要達到較高的境界,就要努力探究真理,盡量發揮人的善良的本性,要通達天道出神入化,盡量做到廣大圓滿,做到最高明。人的情感和欲望不能過分地放縱,因此要經常克制,在這些方面的要求要盡量少。要在言語上十分謹慎,要三思而后行,要約束自己,要清心寡欲,要節制飲食、減少不良的嗜好。
呂坤對人生的反思,對宇宙的探索,對朝政的詰問,對真理的追求,對自然的向往,對心靈的修煉,對大道的感悟,都深有心得,獨具魅力。這樣的洞察,這樣的明辨,這樣的胸懷,這樣的境界,這樣的智慧,這樣的思想,如何會是一個病者的呻吟?分明是“推堪人情物理,研辨內外公私,痛切之至,令人當下猛省,奚啻砭骨之神針,苦口之良劑”。
作為莊子的同鄉和后人,呂坤的智慧中折射著老莊思想的光芒。《老子》言“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意為“最美的聲音就是聽起來無聲,最美的形象就是看不見行跡”。這是一種生活的智慧,《呻吟語》讓我們看到了一位智者“情感熱烈深沉,卻不矯飾喧囂;智慧雋永明快,卻不邀寵于形”的思想魅力。(本版圖片為資料圖片)【原標題:策劃/張浩哲 文字/晚報記者 班琳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