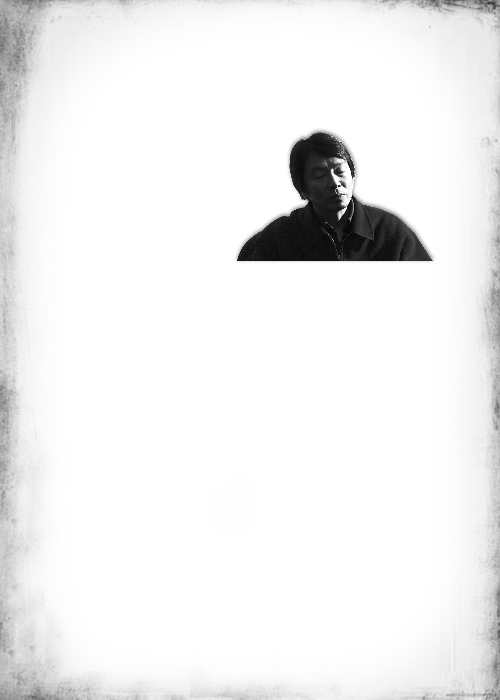- 1、阮咸與琵琶的故事
- 2、韓愈古文改革
- 3、管仲齊勸諫桓公止封禪
- 4、胡秋萍書法欣賞
- 5、馬俊明書法作品欣賞
- 6、書法行長計承江的智慧生活
- 7、劉姓杰出的歷史名人
- 8、“河南墜子滅亡不了”
-
沒有記錄!
- 1、劉姓杰出的歷史名人
- 2、阮咸與琵琶的故事
- 3、韓愈古文改革
- 4、管仲齊勸諫桓公止封禪
- 5、胡秋萍書法欣賞
- 6、“河南墜子滅亡不了”
- 7、馬俊明書法作品欣賞
- 8、法家之"術" 申不害的學術思想
劉震云談"溫故一九四二":河南人用幽默把災難的嚴峻融化
2013/7/12 11:03:53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新聞摘要】
劉震云:其實《溫故一九四二》并不在我寫作的計劃或者想法里,我從來沒想過寫非虛構類的作品。1991年的時候,錢綱(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想編災難史,但他沒從春秋戰國編起,而是從20世紀開始。災難在中國不難找,很快找到了100個,等于幾乎一年一個。1942年河南旱災是其中很大的,因為我是河南人,他就找到了我。但是我對1942年沒有概念,他說1942年死了300萬人,我對300萬這個數字也沒有概念。他比較說:二戰時期納粹的奧斯維辛集中營,迫害的猶太人是100多萬人,也就是說,光在1942年,河南等于有三個奧斯維辛集中營。
早在11月15日,河南商報記者就已在北京專訪了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得主劉震云先生。他是小說《溫故一九四二》的作者、電影《一九四二》的編劇。
在兩個小時的專訪中,他詳細介紹了小說和電影的創作源起、創作過程和鮮為人知的細節,以及他對文學、生活、故鄉等方面的理解。
當天,專訪結束后,他還親自安排河南商報記者在全國報媒中率先觀看了電影《一九四二》的原片。
在電影《一九四二》全國公映新聞發布會舉行之際,在河南商報紀實版《一九四二》持續刊發之時,河南商報特將此專訪刊發,與讀者分享。
關于小說
“1942年的河南,等于有三個奧斯維辛集中營”
河南商報:1992年出版《溫故一九四二》的原因是什么?
劉震云:其實《溫故一九四二》并不在我寫作的計劃或者想法里,我從來沒想過寫非虛構類的作品。1991年的時候,錢綱(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想編災難史,但他沒從春秋戰國編起,而是從20世紀開始。
災難在中國不難找,很快找到了100個,等于幾乎一年一個。1942年河南旱災是其中很大的,因為我是河南人,他就找到了我。但是我對1942年沒有概念,他說1942年死了300萬人,我對300萬這個數字也沒有概念。他比較說:二戰時期納粹的奧斯維辛集中營,迫害的猶太人是100多萬人,也就是說,光在1942年,河南等于有三個奧斯維辛集中營。
這個數字對我比較有觸動,我說我回老家看看。當回到老家的時候,首先遇到的問題是,1942年的親歷者和后代把1942年也給忘了,《溫故一九四二》里有,我姥娘說1942是哪一年?我說餓死人那一年。她說:“餓死人的年頭太多了,你說的到底是哪一年?”
河南商報:遺忘對你的觸動,比300萬這個數字更強烈?
劉震云:對。遺忘有兩種,一種是事情不值得記起,另一種是一件事發生得太頻繁了。一個事情發生得太頻繁,就容易忘記。在中國,餓死人不是個特別的事,餓死300萬人也不是個特別的事,所以容易遺忘。再往下調查,餓死300萬人不僅僅是因為旱災,還有戰爭。
河南商報:當時正是抗日戰爭時期。
劉震云:當時中國在國際上是個特別貧弱的國家。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變”,占了東北,1937年“盧溝橋事變”,占了整個華北華南,但是占了大半個中國,中國一直沒對日本宣戰,就像強盜進你家燒殺搶掠,你不敢說“我跟你打吧”。什么時候宣戰呢,1941年12月9日,距離1931年整整十年。
1942年,河南發生旱災的時候,日本大兵壓境,因為跟美國發生了太平洋戰爭,他就想鞏固中國這個戰略后方,掠奪戰爭資源、人力資源、物質資源,所以想把河南占了。
這個時候中國政府最大的智慧是,一個地方發生了這樣的旱災,相比于國際上別的事,是一件特別小的事,比如和英國關系、美國關系、蘇聯關系,一個處理不好,這個民族就會走向另一個方向。所以它無力救助旱災,就想把河南丟給日本人,日軍發現后,就不進攻,這就把戰爭轉成了政治真空。河南人就在這種政治真空中,往陜西逃荒的路上一個個餓死的。
“用幽默對付災難,就把嚴峻融化了”
河南商報:這是你對1942年的探究?
劉震云:當然,1942年如果探究到這種地步,是可以寫部不錯的作品,但是當我把這些事實從1942年打撈出來,又擺到這些幸存者面前時,他們的腦子開始轉了,他們的“轉”給你提供了親身經歷的細節,這就是300萬人面臨死亡的態度。
河南商報:你一直提到“態度”,這是種什么樣的態度?
劉震云:如果是一個歐洲人或一個美國人,遇到這種事會想為什么死,到底是誰把我餓死的,但是河南人給這個世界留下的是最后的幽默。老張死的時候,會想起好朋友老李,老李在3天前死了,老張最后的想法就是“我比老李多活了3天”。一個民族面對生死的態度,一定決定了生存的秘籍。這個秘籍就是幽默和自嘲。
另外一個就是面對這種災難的嚴峻,你能用嚴峻對付嚴峻嗎?這時候嚴峻就變成一塊鐵,你反抗就是雞蛋碰到鐵上。但是如果用幽默來對付,嚴峻就變成了一塊冰,到幽默的大海里就融化了。真正讓我震撼的,是300萬人面對死亡的態度,幽默的態度,是與眾不同,與別的民族不同,這就是我寫《溫故一九四二》的緣起。
關于電影
一部電影的19年“孕育”歷程
河南商報:把《溫故一九四二》拍成電影,這是怎樣一步步實現的?
劉震云:馮小剛最初提出來,他的想法確實在別人看來非常瘋狂,一開始是非常危險的事,因為首先有幾個不可能。
把這個小說改成電影不可能,沒有電影元素,故事、人物、情節、起承轉合的結構,它都沒有,就是一個調查體的材料的堆積。所以他一開始說拍這個片子的時候是1993年,到現在19年了,我當時說想一想,別著急,后來開了個論證會,所有專家都說這個不可能,因為它不具備,沒有這些元素。
就像做羊肉燴面,要有羊肉、白面、蔥姜蒜,都得有,這都沒有,怎么可能,瘋了吧。
所以會開完,我問小剛弄不弄,他說,弄吧?那就證明他一定看到了電影元素背面的。我們看到了今天,是不是小剛看到了昨天和明天?他說,其實對《一九四二》特別感興趣的是幽默,《辛德勒名單》嚴峻,這個幽默,說明他看到的是態度,災民的態度、作者的態度,這比里邊的電影元素重要。
缺少的東西從哪來呢?一個在賓館里邊大家商量,另一個就是像你們一樣,走一下災民的路線、委員長的路線、日本人的路線、白修德的路線,接著就上路了。幾大路線走的時候,缺少的東西自己就出來了,所有的人物都是自己生長出來的,老東家一家、佃戶一家,這些人物小說都沒有,自己就生長出來了。
還有就是19年了,拍攝這個影片幾起幾落。19年堅持下來,為什么?我覺得作為一個導演,一定不是因為要拍這個電影,而是走逃荒路,和災民有了血肉相連的關系。另外就是這個劇本本身,別的導演來拍,也是不可能,因為幾大方面不見面,災民和委員長、日本人、白修德、天主教會都不見面,在一個戲里,幾個主角不見面,戲能成立嗎?咱幾個不見面,演一臺戲,怎么能行呢?小剛說,你說行就行,為什么呢?好就好在不見面,不見面這就形成了政治真空。是不是更深刻一些?另外就是用幽默的態度對待,是不是更悲涼一些?生活原理和藝術原理,小剛比別人參悟的要不同,要深刻。看了就覺得是他拍的前所未有的。
河南商報:這部電影的看點,或者社會價值和商業價值怎么完美實現呢?
劉震云:第一,電影很特別。態度特別,出來的態度是災民的態度,看了很多細節,幽默,笑了之后更悲涼。第二,內容特別。因為一場旱災死了300萬人,各大方位的錯動,氣勢恢弘。第三,全明星陣容,這個吸引力也很高。在別的劇里你可能是主角,這里就幾句臺詞,另外還有好萊塢的影帝,聚集在一個片子里。第四,有原來的小說,有劉震云的名字。第五,有馮小剛的名字。幾大因素聚集到一起了。
我跟小剛還說呢,也許1993年拍了,就不是這個樣子,因為那時候能拿出3000萬元,就是天文數字,而且那時候小剛拍電影的經驗還不很豐富,后來19年中拍了那么多大片,攢了那么多好口碑,這肯定對票房也有拉動作用。
重要的是,19年,不管是小剛,還是我,我們對生活、對藝術、對自己、對1942年的認識,和19年前不一樣。更重要的是,19年中正因為有了這么多積累,投資跟以前也不一樣,兩億多元的投資,能夠達到“前不見頭后不見尾”,3000萬元你達不到。記者 李肖肖 陳和生【原標題:劉震云談"溫故一九四二":河南人用幽默把災難的嚴峻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