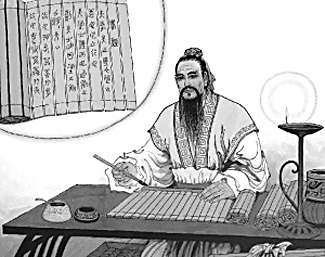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鉆龜與祝蓍。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zhèn)螐驼l知。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白居易因主持正義而遭當權者忌恨和打壓,被貶為江州司馬。放逐途中,有感于好友元稹《放言》五首所表達出來的悲憤情懷,遂以同名組詩奉和。以上便是其中之三,也是流傳最廣的一首。
在這首詩中,白居易以“試玉”、“辨材”為譬曉諭世人,辨識人品的真?zhèn)涡枰欢ǖ臅r間,甚至要終其一生。因為人品是內在的,隱性的,很難從一時一事中看出來,即便眼力超凡的高人,也有看走眼的時候。
曾子的人品是非常高尚的,是儒門數一數二的道德模范,古籍中有不少典故贊揚他。可就是這樣一位圣賢級的人物,當年也曾有被誤解的時候。據《說苑》記載:曾子37歲時,被費國國君聘請到費國。恰逢魯國發(fā)兵攻打費國,曾參向費國國君請辭說,我要出去幾天,等魯國退兵后再回來,請您派人看好我的家,不要讓豬狗拱壞了。費國國君聽了頗為不悅,心里說,我待先生之情,人所共知。如今魯國軍隊就要打過來了,先生卻要離我而去,還讓我替你管家,這說得過去嗎?結果,曾參去的是魯國,質詢魯國出兵攻費國的理由。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進行外交斡旋。魯國列舉了費國的十大罪狀,被曾參駁倒了九條。于是,魯國決定撤軍。費國國君聞知后,趕忙派人把曾參的房舍修整妥善,迎接曾子歸來。圣人尚且如此,何況是常人呢?
好人名聲的論定需要時間,壞人品行的暴露也需要時間。宋相戴剔成素有仁愛、清廉之名,但卻野心勃勃,專權好戰(zhàn),變法初見成效后,不懷好意地對宋桓侯說,國家的安危,百姓的順逆,關鍵在于賞罰。賞罰得當,賢人就會得志,惡人就會受制;賞罰不當,賢人就會受壓,惡人就會得勢,并通過結黨營私、蒙蔽君王來爭名奪利。賞賜人人喜愛,這種受歡迎的事由您來做;刑罰人人討厭,這個黑臉就由我來扮演。宋桓侯聽了高興地說,好極了,就照你說的,我當好人,你當壞人。這樣一來,生死予奪大權完全操控在戴剔成手里,宋國臣民無不畏懼,唯戴剔成之命是從。沒過多久,戴剔成就廢黜宋桓侯取而代之。宋桓侯這才明白過來,原來戴剔成所謂的仁愛、廉潔和忠誠,都是偽裝的。可是,噩夢醒來是黃昏,這一切都晚了。
西漢大臣公孫弘善,圓滑世故,特別善于偽裝自己,且能一以貫之,將作假進行到底,即便被汲黯揭了老底,依然能高姿態(tài)認賬,漢武帝還以為他寬宏大量,虛懷若谷,以至功成名就,拜相封侯。盡管如此,后世論及他的品行時,仍然不敢恭維,稱他是個典型的“兩面人”。由此讓我們聯(lián)想起當今那些被繩之以法的貪官,他們中有些人在落馬前,頭上還罩著反腐倡廉的光環(huán),孰料剛走下警示教育講臺就被“雙規(guī)”了。河南省原交通廳長張坤桐剛上任時,曾信誓旦旦地說:“全省的高速公路修到哪里,黨風廉政建設就延伸到哪里!”可他一下基層,就沿途收受賄賂,終至案發(fā)。成克杰在接受中央媒體采訪時曾說:“想到廣西還有700萬人沒有脫貧,我這個當主席的是覺也睡不好呀!”然而誰會想到,這位憂國憂民之心溢于言表的主席先生受賄款物竟達4000多萬。湖北省財政廳原副廳長曾繁衍曾主編過廉政教材《歷史的啟迪》,并為該書作序,大聲疾呼“改革開放,繁榮經濟,要堅定不移;保持廉潔,反對腐敗,也要堅定不移”。這些臺上大講腐敗危害,臺下依然受賄的人,就是當代的“兩面人”,到頭來難免露出馬腳,落得個身敗名裂鎖枷扛的悲慘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