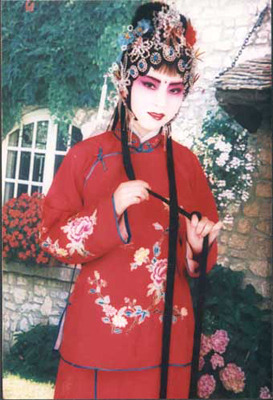- 1、豫劇《三上關》精彩唱段欣賞
- 2、梨花盛開說大鼓
- 3、【文化中原】吹腔藝術的傳承與發展
- 4、豫劇舞臺走來新版“麻風女”
- 5、桐柏皮影:燈影斑斕唱千年
- 6、雖不常睹面 民間有其聲
- 7、淮調
- 8、籌音樂的過去與未來
-
沒有記錄!
稀有劇種到底有啥稀罕
2017/4/14 19:58:51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每個劇能夠在一方水土安身立命,必然要有自己的絕活。過去是這樣,未來亦如此。保持自己的特色,哪怕地盤小,就如宛梆一樣,生在那一方水土,守在那一方水土,自吟自唱得好,松松就過去了幾百年,魅力在家鄉人眼里并不退減,流行歌曲和電影跟它比,倒還像是剛出生的小孩呢。
壹
一鳴驚人
“稀罕,看了一輩子戲,這個真沒見過。”
3月27日晚,河南稀有劇種公益展演已經接近尾聲,見多識廣的戲曲專家和老戲迷們,卻被來自平輿縣的一臺“從未見過”的絲弦道大戲所震撼。
這臺戲叫《德孝情》,講的是古時姜灣村,鄉紳姜文娶妻龐三春,生子安安,家庭富裕和睦,卻因賭徒馬三挑撥,使得不明真相的婆婆中招,趕走三春。最終,在姜文、安安的德孝精神感召下,真相大白,合家團圓。故事取材于明代《躍鯉記》中的安安送米,又有大的改造加工,劇情既帶鄉土氣,又具時代感。
讓觀眾耳目一新的,是舞臺呈現。
看過戲的都知道,舞臺之下,觀眾席第一排之前有個碩大的樂池,整場樂隊都藏在里面演奏。《德孝情》卻不同,樂池空空如也,40位樂師卻長袍馬褂,正襟危坐在舞臺中央后方的高臺之上操持各種樂器,還有六位身著旗袍的女性八角鼓手,于樂隊左側或坐或立,相當“搶鏡”。樂隊前方有一道小柵欄作分界,再往前的舞臺才是留給演員的。“稀罕,看了一輩子戲,這個真沒見過。”著名作曲家、河南省戲曲音樂學會會長朱超倫說。
這樂隊坐臺上可不“白坐”,還要“摻和”劇情,隨著情節發展跟演員互動。一開場,八角鼓手就邊奏邊唱:“洪汝河畔姜灣村,有一鄉紳名姜文……”跟劇中的說書人一起,充當劇情旁白,等反面角色馬三一上場,樂隊還要適時發出嘲笑聲,馬三惱:笑啥笑啥,來段音樂!樂隊一聲“好嘞”,樂起,馬三便開唱自己的賭博經,表明賭徒身份,隨后走向樂手:“嫂子,借點錢!”“哥,借點錢!”樂手們以一聲“滾”予以回絕。
馬三借不來錢,正是要打龐三春歪主意的原因,樂手們就這樣自然而然地參與了劇情推進。引人的題材,新穎的形式,柔美悠揚的古曲新韻,加上絲弦道的“清音”純、脆、甜的三大特色,讓整場演出掌聲不斷,在網上同步觀看的網友也超過了4萬。盡管這部戲已在駐馬店戲曲大賽拔得頭籌,第一次走進省城收獲如此反響,仍然讓劇團和專家們有些意外。
演出結束后已近深夜11點,專家和這部戲的主創們意猶未盡地聚在劇場的會議室里對這部戲作研討,李樹建、朱超倫、劉景亮、耿玉卿、羅云、譚靜波、吳亞明、牛冠力、陳紅旭等戲曲界、曲藝界名人大腕都來了,討論立刻就炸了鍋。知名編劇牛冠力連稱“開眼界”,一部戲的表達通常要么是敘事體,要么是代言體,這部戲則將兩者結合得很完美。導演羅云更是直言,“這或許既是個新劇種,又是個新氣象!”
專家們炸鍋的原因,除了“稀罕”“驚艷”,還有一個背景,這部戲究竟是戲曲還是曲藝,沒看之前他們單憑資料介紹一直拿不準,《中國戲曲志》《中國戲曲音樂集成》的河南卷中都沒有絲弦道,《中國曲藝志》中倒是簡略地提過它。平輿縣絲弦道非遺傳承保護中心主任田春筍告訴記者,實際上,這部戲是作為參加展演活動的18個劇目中唯一的“特邀曲種”來到省會的。由此,研討會上,為這部戲“驗明正身”成了話題,專家們基本認為,從這部戲的呈現來看,歸入戲曲是完全可以的。
作為平輿土生土長的一個小劇種,能夠亮相省會并得到觀眾和專家的認可,《德孝情》的主創們也很興奮。這部戲的編劇、作曲陳嶺告訴記者,絲弦道經歷坎坷,可謂死而復生,其原本是一種以琴會友、自娛自樂的坐唱藝術形式,早期清音演唱,參與者多為文人雅士、仕官階層。清末,平輿人萬道同融“鼓子曲”和當地的民間小調于其中,逐步演變為有領唱、伴唱、對唱的形式,絲弦道也從“曲高和寡”走向千家萬戶。最紅火時,1935年僅汝南一縣,絲弦道班社就有40多個,演員350多人,班社遍布城鄉,廣泛流行于駐馬店、信陽、周口及安徽阜陽一帶。不過,隨著社會變遷,絲弦道在經歷短暫的繁榮之后,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銷聲匿跡甚至失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絲弦道才被重新挖掘,重新尋找音樂曲牌和譜子,2007年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貳
繁花錦簇
一旦有機會展示,仍然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傾倒觀眾
絲弦道只是諸多稀有劇種的一個縮影。其實,每個稀有劇種都極有自己的特色,都有安身立命的絕活,只是露臉的機會越來越少,知道的人越來越少,但它們的獨特魅力仍在,一旦有機會展示,仍然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傾倒觀眾。
參與此次展演文案整理的戲曲音樂理論家、80歲的范立方先生幾乎看過河南所有劇種的演出,一聽就能辨出是什么戲。他告訴記者,從表演形式上,河南的30多個劇種主要分為三類:一類是近百年來戲曲改良發展后受昆曲、京劇影響較大的當代劇種,比如豫劇,它們的分布如同現代文化一樣,跟鐵路的擴張重疊;第二類是很少受現代文化影響、至今保留著粗獷、原生態表演方式的古老劇種,比如大弦戲、大平調、羅戲,它們至今還存在于一些相對偏遠地區的鄉村;第三類是具有戲曲早期的表演形態,比如信陽的很多小戲,與現在的戲曲不同,它們很少使用樂隊,演員敞開嗓子“干唱”。
2014年12月,河南省文化廳主持的河南省稀有劇種搶救工程落下帷幕,當時確定河南共計有32個劇種。經過最近兩年的發掘整理,又增加了蒲劇、地燈戲兩種,達到34個。其中,去掉通俗所說的三大劇種豫劇、曲劇和越調,31個稀有劇種中,誕生于明末及更早之前的劇種至少有14個,包括宛梆、懷梆、大平調、柳子戲、大弦戲、目連戲、光山花鼓戲、羅卷戲、淮調、大辮戲、嗨子戲、商城花籃戲、棗梆、揚高戲等;誕生于清代至遲至民國的則有四平調、道情戲、二夾弦、二股弦、落腔、漢劇、河陽花鼓戲、虞城花鼓戲、柳琴戲、四股弦、墜劇等;此外,皮影戲、杠天神、扁擔戲等起源年代待考。
換句話說,這些劇種少則已有百歲,多則已有400年以上歷史。其中,目連戲這個名字很多人都覺陌生,但它最早的文字記錄見之于南宋盂元老所撰《東京夢華錄》,距今已有900年,因此被譽為中國戲曲的“戲祖”。“可以說,稀有劇種考據起來都很有來頭。別看它們現在影響范圍小,掂起來,每個都沉甸甸的。”范立方說。
翻閱河南劇種分布圖,能發現幾乎每個市地都有,而尤其以豫北、豫東的南樂、滑縣、內黃、武陟、睢縣為最多,每個縣保有劇種都在四個以上,這就是戲曲研究者所說的“戲窩子”。為什么河南有這么多劇種?豫北和豫東又為何格外多?
范立方說,戲曲的流傳與衍變是非常復雜的,但簡單來說,一種戲曲總是產生或者興起于一定的地域,形成之始就帶著地方語言及音樂等地方文化的特性。隨著這種戲曲的流傳,當它來到一個新的地方,就會逐步接受當地語言和民間音樂的影響,音隨地改,落戶生根,又由于許多劇種在全國流布的影響,各地又出現了不少以說唱藝術、民間歌舞發展而成的新興地方劇種,最終都統一于戲曲劇種的概念。所以,千百年來,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百花爭艷、年齡不一、雅俗有別的各個劇種。
豫北、豫東戲多,則跟開封密切相關。元雜劇、宋雜劇、宮廷戲的興盛,是戲曲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北宋滅亡后,藝人一部分南下,一部分被金人擄走,還有一部分流落民間,開封南北兩個方向聚攏了很多藝人,而在后來的社會發展特別是最近的百年變遷中,這兩個地方又并不在鐵路線上,各種戲曲一直是當地特別是鄉村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得以滋養保留。拿目連戲來說,河南境內僅存的兩處傳承地,正好就在豫北南樂和豫東商丘睢陽。
叁
精彩絕活
即使你不愛戲曲,也不由得驚嘆
具體到這些劇種的絕活兒,朱超倫、劉景亮、范立方等老戲曲人給記者娓娓道來,聽他們的描述,即使你不愛戲曲,也不由得驚嘆。
論武,要說大弦戲,每次演出現場觀眾的掌聲與呼喊聲都是山呼海嘯,這種古老劇種至今保留著赤膊戲、滑稽戲等古老的表演藝術形態,演員會在關鍵場次脫掉上衣,赤膊表演,身段也不是花拳繡腿,而真實吸納了大洪拳、梅花拳等武術元素,粗獷潑辣,武生、武旦出場多是大蹦大跳,善用旋風腳,可連旋數十個,它的武打戲更是長期使用真刀真槍,驚險火爆。
大弦戲最知名的還有很多種特技表演,每逢這些戲份上臺,既精彩,又恐怖,兒童哭叫連天,成人膽戰心驚。《孫二娘開店》中有一招“雙頭人”,孫二娘拿大頂,兩腿叉開,腿襠出現一個假面人頭,用假手理假面,撫假發,給武松制造錯覺;《胡羅鍋搶親》中有“打五把彩”,分別用抓鉤、菜刀、剪刀、腰刀、鍘刀五樣道具開打,五樣道具各備一真一假,刀戳剪刺十分逼真;《黑石關》里有“削柳椽”,張定邊持鏡鐮,常遇春握柳椽,激烈對打中柳椽被削成木片,只剩尺余時,張定邊持鏡鐮猛向常遇春頭上削來,常低頭將柳椽轉向背部在腦后一擋,恰被鋒利的鏡鐮勾住,相持繞場一周后張用力一拉,柳椽又被削去一節。
論氣勢和視覺特效,還要說說大平調、目連戲和淮調。大平調是明末就已形成的梆子腔,流行于豫北濮陽、滑縣、延津、浚縣、內黃一帶,代表劇目《包公碑》,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紅臉與黑臉戲多,表演上動作粗獷豪放,彪悍夸張,有中原民間武術雜技的風采。樂器尖子號以及包括大鐃、大镲各一對的“四大扇”奏起來氣勢恢宏,聲聞數里,若戰馬嘶鳴。大平調更有一門“銅眼獠牙”的絕技,演員表演時眼戴好似一副泳鏡的銅鈴,嘴含兩根長15厘米的獠牙,憑著嘴里的功夫,獠牙可以上翻下翻,還能插入鼻孔,卻不耽誤人翻轉騰挪,嘴里演唱。
淮調是一個古老的劇種,傳統劇目就有300多部,袍帶戲居多,如《平遼東》《闖幽州》,至今保留很多絕活,除了與大平調相似的“耍獠牙”,還有刀鍘帶彩,以假亂真。目連戲則更古老,表演上仍有“鋸解”“磨研”“開腸”“破肚”等帶彩特技,還能在舞臺上噴火,極為震撼,服飾化妝都古老獨特,透著宋代藝人的原生態。
豫北尚武,武術、雜技流行,所以在視覺效果上豫北的很多劇種很搶眼。往南往東,又有別的表演特色。
論高音,得說南陽宛梆。這種只流傳于內鄉一帶的劇種行當齊全,曲調豐富,唱腔獨特,但最驚艷的,則是女演員在一些唱詞的結尾突然釋放出高八度的嘔音花腔,委婉清亮,配之以梆胡發出的“唧唧”聲,猶如鳥鳴,讓人如癡如醉。還有陜縣、靈寶的揚高戲,聽名字就知道它的調門高,這種戲有說來源于秧歌,有說來源于牧羊小曲,總之音樂起伏很大,句尾旋律向上,調尾上揚,猶如大跳。
有高就有低,論溫柔細膩,永城柳琴戲的柔潤也是一絕,曾有藝人拿曲劇《曹莊殺妻》里的唱詞形容其為“蜜蜂哼,打茶盅,孩子叫娘頭一聲”。還有與它一字之差的柳子戲,有北曲的粗獷渾厚,也有南戲和宮廷戲曲的華麗婉約,特別是演唱極有規范,“小旦唱得顫巍巍,小生唱得云上飛,青衣哎哎水上漂,老旦唱得聲如雷”。
論起舌尖功夫,也得說說太康道情,此戲以小生、小旦和小丑為主,讓人印象最深的是節奏感很快,嘴皮兒很巧,可以一口氣唱幾十句,演唱極富生活情趣,尤其是運用打嘟嚕的彈舌音唱法,非常逗人。而說到搞怪逗人,聲音可以,臉也可以,河南地方戲里還有一招“耍蛤螭”,淮調、懷梆、蒲劇、豫劇都有這種面部表演特技,演員額部勾蛤蟆狀,前爪畫在眼皮及眉棱骨上,后爪畫在兩額角,嘴置于眉心,演員運用額部肌肉的伸縮顫動,可以讓蛤蟆跳起來,加上瞪眼、擠眼的巧妙結合,活靈活現,妙趣橫生,就像一只蛤蟆欲從額頭跳下一樣,用來表現琢磨、思考、悔恨、焦躁等復雜的心理活動。
有的劇是往繁里走,也有的為了藝人行走民間方便,是往簡里走。光山花鼓戲的表演,故事多是兒女情長,但你可聽不到胡琴、笛簫之類的抒情管弦,只有打擊器樂伴奏;商城花籃戲,也是只用鑼鼓等打擊樂器,它的服裝道具也格外簡單,一個籃子就可以盛裝全部行頭,所以得名。論起省人手,新蔡扁擔戲則是極致,表演時一個人就夠了,用手控制各種木偶人物表演和道具應用,口中說唱,腳踏鑼鼓,真的是一人一臺戲。
肆
重拾特色
經典劇目展示得好,它才有藝術價值和生存之道
稀有劇種發展到今天,雖然數量仍然不少,但很多劇種的表演團體已經很少了,多位研究者告訴記者,一個團與一個劇種的生死存亡直接掛鉤的“天下第一團”約占一半,有的甚至連專業團都沒有,只有業余團體的農民演員,平時務農,閑時操琴弄鼓,傳承手藝。
“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稀有劇種承載著諸多地方文化元素和文化記憶,有著較高的藝術審美、社會文化、歷史認知和學術研究價值,但是隨著現代藝術形式和現代傳播手段的普及,稀有劇種的傳承和發展遇到了較大困難,個別劇種甚至到了瀕危狀態。”河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主任裴景嶺受訪時說。
這些年,稀有劇種基本都被納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給予演出補貼、記錄整理等形式的保護,情況好轉很多,多數團體能夠保證“餓不死”,就拿這次展演來說,十年前,想一下拉出10多個劇種團體在鄭州展演是想都不敢想的。不過,稀有劇種的生存仍然面臨很大挑戰。不少團體后繼乏人,甚至有編制指標都招不夠人,還有一些團名義上是某一劇種,大部分時間里卻不得不依靠演出豫劇等其他劇種來生存,本門藝術面臨弱化、異化甚至失傳的危險。
稀有劇種究竟該怎么走?采訪中,不少專家認為,應該創造性地對稀有劇種區別對待,不能一刀切。一些仍有生命力,能夠排演出自家經典劇目的劇種,不光要進行數字記錄整理,給予演職員補貼,更要重視它們的展示和傳播。
“只有傳播才會有傳承,才能真正獲得生命力。”戲劇評論家劉景亮認為,一定要把這些劇種的經典劇目挖掘整理好,用最好的演員去演,精雕細刻地去排練,盡可能地達到理想狀態,戲可以不多,但要精,之后通過展演活動推向公眾。“經典劇目最能代表一種戲的特色,代表它跟其他戲曲不一樣的地方,也是最能展示其魅力和絕活的,經典劇目展示得好,它才有藝術價值和生存之道,經典劇目如果死了,這個劇種實際上就已經死了。”
拿絲弦道來說,它的主奏樂器嘟嚕胡非常有特色,弓子與弦似挨似不挨能奏出類似“嘟嘟嘟”的聲音,這是只屬于這一劇種的獨特樂器,因為《德孝情》中沒有獨奏的展示,著名作曲家耿玉卿還耿耿于懷,“大家都想聽聽嘟嚕胡是怎么嘟嚕的,劇里為什么沒有安排一段solo(單人表演)?”
范立方也認為,過去很多劇種就是活在泥土里的,咋讓老百姓喜歡就咋來,所以很多傳統劇種有一種自在的游戲性,沒有承擔很多額外功能的束縛反倒魅力無窮。稀有劇種在游戲性上原本就有特色和優勢,在困難時刻更應當時時擦亮。
也有聲音認為,戲曲不再像從前那樣火,大劇種活得尚且艱難,小劇種或可自生自滅?劉景亮認為,文化應該保持多樣性,每一種文化都是千百年來前人智慧的結晶,很多大劇種也是由小到大,從稀有劇種走過來的,可能有些劇種現在萎縮了,比如羅卷戲,曾經火得耽誤農事、擾亂治安,政府不得不多次下令禁演,它曾經是民眾的精神家園,到現在,只要它還沒有消失,它就仍然是一方百姓的精神家園。“稀有劇種當中也承載著優秀傳統文化,我們沒有理由不保護它,讓它的生命停止在我們這一代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