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記錄!
聽,古建筑的呼吸
2013/11/18 11:57:34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雪色中的故宮寧靜安詳。北京故宮氣魄宏偉,規劃嚴整,有種一望而知的均衡美。


日漸陳舊的天井壁畫。(攝于桂林市廟頭古鎮)

侗族建筑營造技藝的一大特色是不用一釘一鉚。(攝于湖南通道縣)

江南園林特有的水鄉韻致。(攝于蘇州木瀆古鎮)

磚木結構的殿閣聳立山巔,在霧氣中顯得典雅靈秀。(攝于浙江東陽市橫店鎮)

匾額、壁畫、對聯、雕刻是古建筑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攝于山西運城解州關帝廟)

大理崇圣寺的古塔,白云纏繞中與蒼山腳下的民居相映成趣,別具風情。

寬窄巷子里保存完好的清末民初風格的建筑群,使其成為成都的文化地標之一。

福建土樓擁有獨特的圓形結構,星空下的土樓如夢如幻。(攝于福建南靖縣)

河南社旗縣的山陜會館,融合了北方的雄渾和南方的柔美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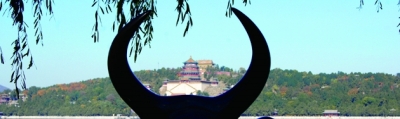
北京頤和園汲取了許多江南園林的手法。
建筑,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人類技術與藝術創造的重要結晶,是固定的物化造型。其功能是為人類活動提供場所,如房屋、廣場等。或是有利于人們生產生活方便而有意識制作建設成形的事物,如道路、橋梁、水渠等。建筑產生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由于采集經濟逐漸形成了食物經濟,農業的出現,使“定居”成為必然要求,因“定居”而產生了“建筑”。由于定居,人類便有了“家”的概念,因對自然崇拜的產生,進而有了“神的家”(神廟)的概念、階級的劃分和國家的出現。統治者住所和公共空間,便形成了王宮、廣場等不同功能的形態。聚集的人群形成了邑(村落),邑在不知不覺中發展成為“大邑”(城鎮),接著便出現了“城市”,國家的首腦駐地“都城”,建筑的體系便完全形成了。
隨著歷史的演化,許多遠古時期的“城”“邑”消失了,成為了遺址、遺存,中古和近世的許多城市保留下來了,城中的許多建筑也存活下來,這些便成了“古建筑”。在鄉村亦有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古村落得以存活,這些古村落便成了一個群體歷史的記憶和文化的載體。細讀古城、古鎮、古村中各種不同功用、不同風格、不同造型的古建筑,便會深深感到這是一種遠古與現實的對話,古建筑身上散發出的氣息,正訴說著人類文明的興衰史。
就西方建筑而言,無論是英格蘭威爾特郡的巨石陣,還是古埃及尼羅河岸的金字塔;無論是傳說中的古巴比倫“空中花園”,還是古希臘、羅馬的柱式建筑;無論是拜占庭磚石混砌的穹頂,還是哥特式直入云霄的尖塔;無論是文藝復興建筑的不規則造型,還是巴洛克式曲線……無不折射出古建筑的深厚蘊涵與歷史靈光。
在中國古建筑譜系里,無論是半坡人的半穴居式,還是河姆渡人的干欄式雛形;無論是文人筆下的阿房宮賦,還是大明宮詞的絕響;無論是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東京繁華,還是明故宮的恢弘氣勢;無論是晉城皇城相府所展示的中國大家大族的豪宅氣派,還是徽州西遞宏村所反映出鄉土中國村落的精致生活;無論是塞北的氈房蒙古包,還是侗鄉苗寨的吊腳樓;無論是蘇州的園林,還是傣家的竹樓……無不是古老文明的活態綻放。
一個柱杵,支撐的是一個民族的大廈;一塊秦磚,刻畫的是一個民族的形象;一片漢瓦,遮擋的是一個民族的家園;一扇格窗,打開的是一個民族的心扉;一道大門,敞開的是一個民族的胸懷。這便是一個偉大民族鐫刻在古建筑上的豐碑,這便是一個民族書寫在古建筑上的文明史,這便是古建筑的長長詠嘆與深深呼吸!
當現代文明的隆隆機器聲正碾碎著古建筑所代表的傳統文化時,工業文明散發出的濃濃霧霾正窒息著古建筑所代表的古老生命時,我們不禁要問:古建筑的詠嘆,在大都市的喧囂聲中還能夠鳴唱多久?古建筑的呼吸,在快速發展的鄉村城鎮化進程中,還能殘喘多久?(作者系云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研究員)
可觸摸的美
——拍客眼中的古建筑
趙廣超在《大紫禁城》一書里,提過一位日本建筑學者對中國古建筑的感受,他說這位學者,覺得中國宮殿的空間大到令人“茫然”。看到這段描述的幾年后,在一場大雪中,我于頤和園閑逛,四野無人,地無走獸,屋檐挑起了天涯一端,所有建筑都被積雪沉沉覆蓋。那一瞬間就覺得,天下間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看的景致了。后來又去山西逛老城鎮,那里有無數使用青磚灰瓦的民居。走進巷子,就能感受到房屋間空隙狹窄,空間逼仄。院子的大門大都已存百年,開闔間頗為沉重。古建筑之所以能讓人震撼,多半是因為其超出現代建筑范疇之外,獨有的精致、對稱和豐富的細節,也是因為與文明的其他部分相比,這凝固的歷史又像是活生生的,可感知,可觸摸。
人們是這么喜歡把建筑比成一本書,那么作為拍攝者,早已在石頭、木構件和夕陽中,接觸到了無數過往的歲月和記憶。由此可見,建筑確實是歷史的投射。
你相機里的古舊民居與廟堂殿閣,都是真實存在的古韻遺風,且早已匯成一脈文化河流。
數不清的細節在河流中奔騰流淌,掩映在刀劍斧鉞中,映襯于斗拱磚石間,被人們口口相傳。這河流湍急又闊大,延續了兩千余年,已自成一個藝術系統,古建筑物更是文化的具象,藝術上的大宗遺產。
如果一定要說用影像描摹這大宗遺產的意義在哪兒,那便是記錄下它們還未廣為人知的精妙之處和環境美學、歷史文物與建筑本身的獨到之處——“攀緣在中國歷史大廈的梁架之間,感受著我們手指間那精巧的木工和觸手即得的奇跡,以及一種可能已經永遠不可復得的藝術的精微。”(梁 丹)本版攝影: 梁 丹、張炎龍、于冬瑞、張 紅、李 韻、蔣新軍(原標題:聽,古建筑的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