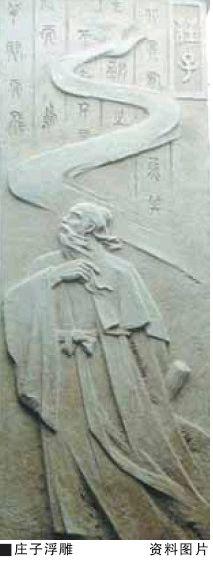精彩推薦
熱點關注
專題推薦
-
沒有記錄!
熱點排行
莊子學派多有關乎鬼神之論
2014/12/10 8:28:45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莊子接受傳統鬼神觀念,但仍以道作為鬼神之所以具有神性的根據。
在殷商時代,人們十分崇拜鬼神,以為人死后魂靈不滅,稱之為鬼,認為鬼神能夠賞善罰惡,主宰人間社會的一切,可以通過向鬼神祈禱來消災求福。但是,在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對何為鬼神、鬼神是否存在等問題卻有了諸多爭論。由《論語》的記載可見,孔子更關注人事而并不想探討鬼神的問題,但他仍然看重對鬼神的祭祀。墨子則力辯鬼神存在,認為如果人們沒有了鬼神觀念則天下會大亂。從墨子的批評來看,當時“無鬼”論已在思想界占有一定的地位。荀子否定“鬼”的存在,認為“見鬼”的經驗是精神恍惚、疑惑迷亂時的錯覺。與鬼神崇拜相關的祭祀活動是人道的發揚,而不是對鬼神的畏懼。處于這一思想潮流中的莊子和莊子后學,對于鬼神問題的討論也頗具代表性。
莊子在《大宗師》中提到勘壞為昆侖山神,馮夷為河伯。馮夷渡河溺死而為河伯,可見莊子認為存在具有人格的人鬼和自然神,且具有神異能力。這表明了莊子接受傳統鬼神觀念,但仍以道作為鬼神之所以具有神性的根據。
《管子》以精氣釋道,認為鬼神并不是有人格的主宰,而是流動于天地之間的精氣,鬼神入舍即精氣存于人心,是得道的表現。莊子沒有明確提出精氣說,不能確定是否同《管子》一樣將鬼神理解為精氣,但他提到的能舍于人心的鬼神,似乎應不是能掌管人間賞罰的人格化的鬼神。
莊子僅在兩處論及鬼神觀念,一處關乎對道的探討,一處關乎對體道的心靈修養方法的探討,而鬼神問題本身并非其所欲討論的對象。兩處相對照,可見莊子對鬼神的理解應該處于由人格化向自然化的過渡之中。
莊子后學對鬼神問題有較多探討。《寓言》明確討論了鬼是否存在的問題,并認為其不能確知。這是戰國時期思想界疑鬼思潮的反映。但是,莊子的大部分后學仍承認鬼的存在。如《庚桑楚》講,精神外馳而不返歸,則死期將至,死則為鬼;心性滅絕而徒留形體,和鬼是同類。此處以精神外馳與形體分離來解釋鬼的產生,是對先秦時期鬼神觀念的發展。此外,還以鬼是與人相對的一種存在,可以對作惡之人進行懲罰,是對傳統鬼神觀念的繼承。
在傳統的鬼神崇拜中,人們認為鬼神可以主宰人間的一切,而疾病的發生往往是因為人觸犯了鬼神,向鬼神祈禱就能治療疾病。甲骨文中有殷王武丁因病向亡故的父母禱告的卜辭,是人們試圖通過對祖先之鬼神的祭祀來祈求疾病痊愈的記錄。《達生》篇講桓公因見鬼而生病,又借皇子告敖之口肯定鬼的存在,且鬼所指具體,數量眾多,有形象、有人格,為傳統的鬼神觀念。但對傳統鬼神崇拜中以觸犯鬼神解釋疾病的產生持反對態度,認為桓公生病的真正原因是出于“自傷”,即氣經郁結,發散而不返回,造成精力不足;氣淤積于上而不下通,使人容易發怒;淤積于下而不上達,使人健忘;不上達不下通,淤積于中,就會生病。此處以氣的淤積來解釋各種疾病的產生,體現出氣論自然觀在思想界的流行及其對鬼神觀念的挑戰。
春秋戰國時期的鬼神觀念雖然經受了嚴重的考驗,但依然是民間信仰的重要內容。如學者們所搜集的《莊子》佚文中就有對民間驅鬼術的討論,這說明部分莊子后學與鬼神崇拜等民間信仰有密切接觸,但多從養生學的角度解釋驅鬼術的作用,與《達生》篇的觀點思路相類似,而與民間的鬼神信仰并不相同。至于他們對“鬼智不如童子”的看法,更否定了對鬼神的崇拜與畏懼。這說明莊子這部分后學與民間信仰的不同立場。
《莊子》能搜集到的佚文很少,而被郭象刪掉的部分約占3/10,可以推斷,原《莊子》中與鬼神相關的內容應該比較多。這或與其思想發展的背景有直接關系。殷周時期的鬼神崇拜雖然在春秋戰國時期受到質疑,但在民間依然盛行,莊子后學用氣論、醫學、養生學的觀點對鬼神進行解釋和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其對人間社會生活的主宰作用。作者:王威威
在殷商時代,人們十分崇拜鬼神,以為人死后魂靈不滅,稱之為鬼,認為鬼神能夠賞善罰惡,主宰人間社會的一切,可以通過向鬼神祈禱來消災求福。但是,在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對何為鬼神、鬼神是否存在等問題卻有了諸多爭論。由《論語》的記載可見,孔子更關注人事而并不想探討鬼神的問題,但他仍然看重對鬼神的祭祀。墨子則力辯鬼神存在,認為如果人們沒有了鬼神觀念則天下會大亂。從墨子的批評來看,當時“無鬼”論已在思想界占有一定的地位。荀子否定“鬼”的存在,認為“見鬼”的經驗是精神恍惚、疑惑迷亂時的錯覺。與鬼神崇拜相關的祭祀活動是人道的發揚,而不是對鬼神的畏懼。處于這一思想潮流中的莊子和莊子后學,對于鬼神問題的討論也頗具代表性。
莊子在《大宗師》中提到勘壞為昆侖山神,馮夷為河伯。馮夷渡河溺死而為河伯,可見莊子認為存在具有人格的人鬼和自然神,且具有神異能力。這表明了莊子接受傳統鬼神觀念,但仍以道作為鬼神之所以具有神性的根據。
《管子》以精氣釋道,認為鬼神并不是有人格的主宰,而是流動于天地之間的精氣,鬼神入舍即精氣存于人心,是得道的表現。莊子沒有明確提出精氣說,不能確定是否同《管子》一樣將鬼神理解為精氣,但他提到的能舍于人心的鬼神,似乎應不是能掌管人間賞罰的人格化的鬼神。
莊子僅在兩處論及鬼神觀念,一處關乎對道的探討,一處關乎對體道的心靈修養方法的探討,而鬼神問題本身并非其所欲討論的對象。兩處相對照,可見莊子對鬼神的理解應該處于由人格化向自然化的過渡之中。
莊子后學對鬼神問題有較多探討。《寓言》明確討論了鬼是否存在的問題,并認為其不能確知。這是戰國時期思想界疑鬼思潮的反映。但是,莊子的大部分后學仍承認鬼的存在。如《庚桑楚》講,精神外馳而不返歸,則死期將至,死則為鬼;心性滅絕而徒留形體,和鬼是同類。此處以精神外馳與形體分離來解釋鬼的產生,是對先秦時期鬼神觀念的發展。此外,還以鬼是與人相對的一種存在,可以對作惡之人進行懲罰,是對傳統鬼神觀念的繼承。
在傳統的鬼神崇拜中,人們認為鬼神可以主宰人間的一切,而疾病的發生往往是因為人觸犯了鬼神,向鬼神祈禱就能治療疾病。甲骨文中有殷王武丁因病向亡故的父母禱告的卜辭,是人們試圖通過對祖先之鬼神的祭祀來祈求疾病痊愈的記錄。《達生》篇講桓公因見鬼而生病,又借皇子告敖之口肯定鬼的存在,且鬼所指具體,數量眾多,有形象、有人格,為傳統的鬼神觀念。但對傳統鬼神崇拜中以觸犯鬼神解釋疾病的產生持反對態度,認為桓公生病的真正原因是出于“自傷”,即氣經郁結,發散而不返回,造成精力不足;氣淤積于上而不下通,使人容易發怒;淤積于下而不上達,使人健忘;不上達不下通,淤積于中,就會生病。此處以氣的淤積來解釋各種疾病的產生,體現出氣論自然觀在思想界的流行及其對鬼神觀念的挑戰。
春秋戰國時期的鬼神觀念雖然經受了嚴重的考驗,但依然是民間信仰的重要內容。如學者們所搜集的《莊子》佚文中就有對民間驅鬼術的討論,這說明部分莊子后學與鬼神崇拜等民間信仰有密切接觸,但多從養生學的角度解釋驅鬼術的作用,與《達生》篇的觀點思路相類似,而與民間的鬼神信仰并不相同。至于他們對“鬼智不如童子”的看法,更否定了對鬼神的崇拜與畏懼。這說明莊子這部分后學與民間信仰的不同立場。
《莊子》能搜集到的佚文很少,而被郭象刪掉的部分約占3/10,可以推斷,原《莊子》中與鬼神相關的內容應該比較多。這或與其思想發展的背景有直接關系。殷周時期的鬼神崇拜雖然在春秋戰國時期受到質疑,但在民間依然盛行,莊子后學用氣論、醫學、養生學的觀點對鬼神進行解釋和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其對人間社會生活的主宰作用。作者:王威威
責任編輯:C009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9月1日第641期)
下一條:《莊子》中的“無用”與“無待”上一條:論莊子懷疑論美學的方法與姿態
相關信息
精彩展示
沒有記錄!
評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