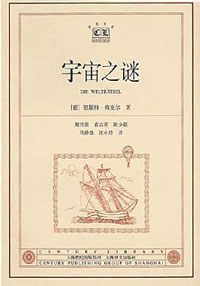-
沒有記錄!
張冠生:一本書記住一句話
2013/10/30 17:32:31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人物簡介:張冠生,為費孝通先生做過十多年助手。在《求是》、《讀書》、《東方》等刊物發表大量文章。著有《鄉土先知》、《知道》等書,最新出版《紙年輪》。
張冠生說,跟閱讀這個文化儀式相比,什么身份都是微不足道的。三年前他作為終審評委參加深圳讀書月好書評選活動時,堅稱自己是“讀者代表”;最近,他又以一個普通讀者的姿態,搜羅了百年間的尋常讀物,做了一次年輪式閱讀,寫成《紙年輪》一書。
讀書是在抓緊時間補課
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十多年里,張冠生一直擔任費孝通先生的助手,因此也受到老先生不少影響。
“費老先生說過一句話,‘八十歲了想起八歲該看的書’,所以他有幾年在抓緊時間‘補課’。我高興的是,能在他晚年‘補課’時為他買了不少書,錢穆的、陳寅恪的、梁漱溟的、馮友蘭的都有。那時候,我大概五十歲,開始找五歲該看的書,然后六歲、七歲……事實上,《紙年輪》就是我在費老影響下自我布置的一次補課的書面作業。文革開始那年,我是小學五年級,正該讀書的年齡無書可讀。”
張冠生的工作跟閱讀并無直接聯系,他認為自己對閱讀的興趣來源于緊迫感、缺失感。“正該讀書的年齡無書可讀,過去讀得少,未來時間又不多,所以,補課該是一輩子的事了。”
一本書一句話就夠用了
張冠生說,因為不靠讀書吃飯,所以多數閱讀是在業余時間。“平時家居習慣于睡前、醒后、午間、傍晚閱讀,出差時,候機廳、航程中、火車上,都是比較理想的大段讀書環境。上下班的地鐵上,也是不錯的地方。加上我又不搞研究做學問,屬于隨意翻書、不求甚解的類型。”
張冠生列舉了幾本對他產生影響的書,他認為與其給人知識,一本好書更應該給人啟發。
“《宇宙之謎》、《浮士德》、《愛默森文選》、《寬容》、《論語》、《羅曼·羅蘭文鈔》對我影響都非常大。這些書影響到了我看待世界、理解生活、與人相處、生命感受等人生基本方面。閱讀和生活歷練的結合,使我逐漸具備了較強的精神韌性和足夠的心理承受能力,體會到多讀好書對擴展心靈的極端重要。”
“假定一個人一輩子能讀一百本書,其實泛讀就好,每本書能夠記住一句話,這句話對你的人生能起到激勵、指導的作用,這輩子也就夠用了。”張冠生有著自己的讀書體會,他認為,這種讀書方法對自己很有用。“《浮士德》有幾千幾萬行詩,我只記住一句,‘在硬化的生活里,要多保留善良的天性。’讀普希金的詩,我也只記住一句,‘生活過,而且思索過。’這些話都教會我如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