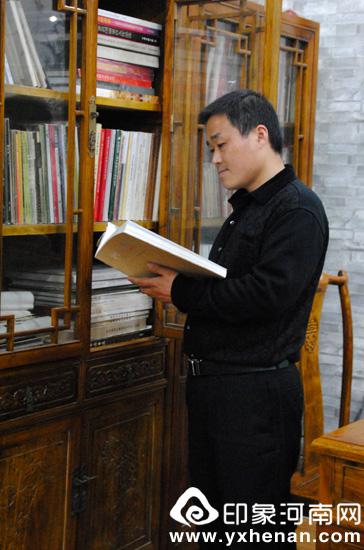-
沒有記錄!
話說印章創(chuàng)作:印材之用
2013/11/8 16:22:59 點(diǎn)擊數(shù): 【字體:大 中 小】
“我之為我,自有我在”,這是出自《石濤畫語(yǔ)錄》中的一句名言。我覺得一個(gè)藝術(shù)家應(yīng)該在他的作品中將個(gè)性化的東西明確而自覺地顯現(xiàn)出來,唯有如此,他的作品才會(huì)被賦之獨(dú)特的生命形象。
藝術(shù)創(chuàng)作離不開藝術(shù)思維,藝術(shù)家獨(dú)立的創(chuàng)作個(gè)性必然要給藝術(shù)思維活動(dòng)以內(nèi)在的影響,并通過藝術(shù)思維活動(dòng)而得到鮮明的展現(xiàn)。卡西爾在《人論》中曾引用過這樣一個(gè)創(chuàng)作實(shí)例:“畫家路德維奇·李希特在他的自傳中談到他年輕時(shí)在蒂沃利和三個(gè)朋友打算畫一幅相同的風(fēng)景的情形。他們都堅(jiān)持不背離自然,盡可能精確地復(fù)寫他們所看到的東西。然而結(jié)果是畫出了四幅完全不同的畫,彼此之間的差別正像這些藝術(shù)家的個(gè)性一樣。從這個(gè)經(jīng)驗(yàn)中他得出結(jié)論說,沒有客觀眼光這樣的東西,而且形式和色彩總是根據(jù)個(gè)人的氣質(zhì)來領(lǐng)悟。”這也就是說藝術(shù)感知的不同,自然會(huì)使每一個(gè)優(yōu)秀的藝術(shù)家形成自己鮮明的個(gè)性印記。更何況各不相同的人生際遇、人生感受,經(jīng)過藝術(shù)家獨(dú)具個(gè)性的審美心理結(jié)構(gòu)的過濾與升華,怎么可能出現(xiàn)千篇一律的作品呢?
我們都知道,藝術(shù)思維不等同于形象思維,在藝術(shù)思維中還包括極為重要的靈感、直覺、頓悟等,對(duì)于以追求新穎和獨(dú)創(chuàng)為宗旨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來說,靈感、直覺、頓悟的出現(xiàn),標(biāo)志著創(chuàng)造力的產(chǎn)生,獨(dú)特藝術(shù)境界的誕生就會(huì)成為現(xiàn)實(shí)。具有自己鮮明創(chuàng)作個(gè)性的藝術(shù)家,不僅有著自己相對(duì)穩(wěn)定的藝術(shù)思維類型,更有著與此相應(yīng)的自己獨(dú)特的思維方式。創(chuàng)作個(gè)性是優(yōu)秀藝術(shù)家在藝術(shù)作品的內(nèi)容和形式的有機(jī)統(tǒng)一中顯現(xiàn)出來的鮮明特征。譬如,同樣刻一部《心經(jīng)》,黃牧甫刻過,方介堪刻過,筆者不揣簡(jiǎn)陋地也曾刻過。若將三部印譜放在一起,我想大家一眼就會(huì)分辨出各自是誰所刻。這就是創(chuàng)作個(gè)性和藝術(shù)思維的差異所致。籠統(tǒng)地講,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風(fēng)格不同。
說到風(fēng)格,其實(shí)一個(gè)人一生中會(huì)發(fā)生多次變化,因?yàn)槿说母惺軙?huì)隨著年齡、閱歷、知識(shí)結(jié)構(gòu)等因素的變化而發(fā)生改變。像余光中就在他的那首非常出名的《鄉(xiāng)愁》中寫道:小時(shí)候,鄉(xiāng)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長(zhǎng)大后,鄉(xiāng)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后來,鄉(xiāng)愁是一方矮矮的墳?zāi)梗欢F(xiàn)在,鄉(xiāng)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同樣是鄉(xiāng)愁,感受卻不同,那么藝術(shù)風(fēng)格的變化,應(yīng)該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然而我們知道,事實(shí)上往往并非如此,不少藝術(shù)家在成名以后,由于受各種因素(主觀的或客觀的)制約,不愿或不能擺脫自己創(chuàng)作的老路、窠臼。我們說,藝術(shù)家一旦形成自己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誠(chéng)然需要一定的穩(wěn)定性,以使作品顯得更加內(nèi)蘊(yùn)豐富、深刻,而不致于輕飄、浮淺;但是這也會(huì)在一定程度上有礙于獲得新穎獨(dú)特的情感體驗(yàn),不利于豐富和發(fā)展自己的創(chuàng)作個(gè)性、深化或改變自己的藝術(shù)風(fēng)格。
藝術(shù)創(chuàng)作到了一定程度,要避開別人并不困難,要突破自我卻并不那么容易。小說家王蒙曾說過一句引人深思的話,他說:“那些所謂非常有風(fēng)格即一眼能看出風(fēng)格的作家藝術(shù)家,如果不能突破自己的風(fēng)格而被風(fēng)格所囿,如果其風(fēng)格本身就相當(dāng)狹窄,創(chuàng)作量越來就越被人一覽無遺,越暴露自己的艱窘貧乏。”這對(duì)那些想以創(chuàng)作數(shù)量取勝,卻又不注重豐富和發(fā)展自己的創(chuàng)作個(gè)性的藝術(shù)家來說,真可謂當(dāng)頭棒喝。
所以我覺得,為了不致于使自己也陷入到上述的窘境,應(yīng)該首先要不斷深入傳統(tǒng),吃透?jìng)鹘y(tǒng)。有朋友說我的印風(fēng)、書風(fēng)好象一直在變,跟我學(xué)很困難。我想說的是,第一,不要學(xué)我,要學(xué)傳統(tǒng),傳統(tǒng)是最有營(yíng)養(yǎng)的母乳;第二,我基本上還是沿著典雅一路在走;第三,書、畫、印我都努力保持相對(duì)穩(wěn)定統(tǒng)一的基調(diào),三者之間有序地探索發(fā)展;第四,我覺得創(chuàng)作個(gè)性和藝術(shù)風(fēng)格是豐富性和獨(dú)創(chuàng)性、穩(wěn)定性和新異性的統(tǒng)一。以上四點(diǎn),一言以蔽之,曰學(xué)傳統(tǒng)。
猶記得少年時(shí)代學(xué)習(xí)刻印時(shí),我用的大多是浙江青田石,那是因?yàn)榍嗵锸暂^穩(wěn)加上價(jià)格便宜之故。后來,待我長(zhǎng)大在圈子里小有名氣的時(shí)候,找我刻印的人漸漸多了起來。如今想想,當(dāng)時(shí)都是些對(duì)印章藝術(shù)一知半解的且找我刻印可以圖個(gè)方便的人,送來的印材自是五花八門應(yīng)有盡有。但印象最深的是有位我的小學(xué)同學(xué),他的家里素有收藏。一次,他拿來一方已經(jīng)蘑去印面,邊款卻赫然在目的壽山石印章,他根本不知道這刻有“叔蓋”的窮款,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身為西泠八家之一的錢松!他告訴我,為了省我的事,他事先已把印面磨平拋光……。天哪,此豈不是暴殄天物!然而盡管這樣,待我把印章刻成后,這方老芙蓉印章的細(xì)膩溫潤(rùn)的刀感,卻給我留下了美好而難忘的記憶。這是我從未體味過的刀筆意趣和歡愉感受。打這以后,我便更加留意起這壽山石中的芙蓉石來。
一晃幾十年過去。為迎接國(guó)慶六十周年和舉世矚目的世博會(huì)的到來,2008年歲冬,受上海市委宣傳部和東方出版中心的囑托,我正式著手《中華民族印譜》的創(chuàng)作準(zhǔn)備。長(zhǎng)期以來,我所采用的篆刻印材,竟然大多是壽山石一類。因此,在刻制《中華民族印譜》時(shí),我當(dāng)然也會(huì)考慮運(yùn)用這些讓自己得心應(yīng)手的石材。好在長(zhǎng)久以來,我原本就積累了不少,所以就有了寬綽的選擇余地。如今,讀者們所看到的這一部由五十七方各式印石組成的《中華民族印譜》,大抵都來自色彩豐富的福建壽山石系。
由于我的篆刻風(fēng)格歸屬于相對(duì)古麗典雅和細(xì)膩一派,故而壽山石的石性,很適合表現(xiàn)我的創(chuàng)作路子,她會(huì)成為我的一生喜好。劉一聞【原標(biāo)題:話說印章創(chuàng)作:印材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