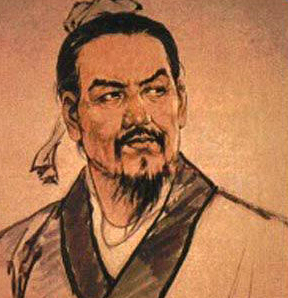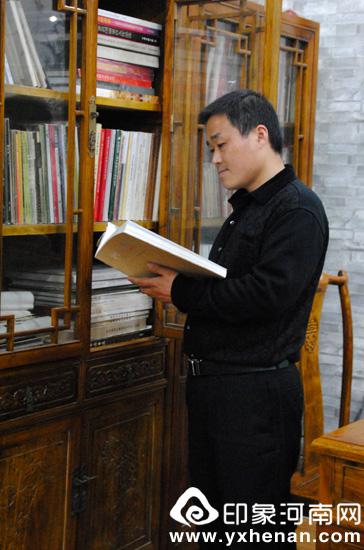精彩推薦
熱點關(guān)注
專題推薦
-
沒有記錄!
熱點排行
荀子與韓非子人性論辨析
2014/12/11 17:43:32 點擊數(shù): 【字體:大 中 小】
原標(biāo)題:荀子與韓非子人性論辨析
先秦時期是我國古代人性論思想的形成階段。諸子百家從各自立場出發(fā),提出了各種各樣的人性論主張。荀子是“性惡論”的典型代表,而由于韓非子與荀子的師承關(guān)系,學(xué)界普遍認(rèn)為韓非子是荀子人性論思想的繼承者,甚至比荀子的性惡主張更極端。其實,這是一種誤解。韓非子雖就學(xué)于儒家的荀子,但卻另辟蹊徑成為法家,就其人性思想的基本立場與本質(zhì)精神而言,韓非子跳出了性善、性惡的分析框架。他所闡發(fā)的是一種自然主義的人性自私論。
荀韓均堅持人性是人“好利”的自然屬性,但在人性“好利”的評價方面,二者卻分道揚(yáng)鑣,荀子對“好利”做出了“惡”的價值判斷,而韓非子只是對“好利”進(jìn)行事實描述,不作價值評價。
荀子的人性論以人的自然本性為出發(fā)點,他把人的自然欲求看作人性,“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yīng),不事而自然,謂之性。”(《荀子·正名》)并將這種欲求歸納為“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同時,荀子對其社會危害做了詳細(xì)描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荀子·性惡》)在荀子看來,人好利之心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必然會導(dǎo)致爭斗與社會動蕩,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惡”。由此,基于儒家道德主義的立場,荀子將人“好利”的本性與倫理道德對立起來,最終對人性做了“惡”的價值判斷,“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
韓非子繼承了荀子以利欲為人之本性的觀點,認(rèn)為“好利惡害”是人的普遍本性,因此,物欲是人類生存的第一需要,是人們思考問題并指導(dǎo)其行動的原點。但是,與荀子直接將人性的好利惡害界定為“惡”不同,韓非子沒有把“善”與“惡”納入人性討論的范圍。對于人好利惡害的本能需要,韓非子突破了性善、性惡的分析框架,以一種自然主義的筆觸對人性只做事實描述,不做道德評價,既不以之為惡,也不以之為善,表現(xiàn)出價值中立的立場。
由于對人性評價的基本立場不同,在人性是否可變這一問題上,荀子與韓非子的論述也有著根本差別。
荀子認(rèn)為人性可以改變,也必須改變。一方面,人性改變具有可能性。無論圣人,還是普通民眾,其人性都是可以變化的,“途之人可以為禹”,人實際上的善與惡,可以通過主觀努力和后天環(huán)境熏染來實現(xiàn),“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nóng)賈,在勢注錯習(xí)俗之所積耳。”(《荀子·榮辱》)另一方面,人性改變又具有自覺性。“夫薄愿厚,惡愿美,狹愿廣,貧愿富,賤愿貴。”(《荀子·性惡》)每個人都向往美好的東西,荀子由此推論:“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荀子·性惡》)人們因知其性惡,所以才有“欲為善”的意愿與動力。另外,人性改變具有必要性。人性惡如果不加以改變,將會對個體發(fā)展、倫理秩序和社會穩(wěn)定帶來巨大危害,“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荀子·禮論》)因此,為避免社會紛爭、動蕩與窮困,必須對人性加以改造和限制。
與之相反,韓非子主張人的自利本性是先天決定,不能改變,也無須變化。一方面,韓非子堅持人性無法改變。在他看來,人的好利屬性是由人的生理需求誘發(fā)的,是人與生俱來的自然本能,不能改變。比如,民眾之所以會做善事,只是服從于外部壓力,并不是發(fā)自于由人性改變而產(chǎn)生的“義”,“民固服于勢,寡能懷于義。”(《韓非子·五蠹》)可以看出,韓非子對于人性可以通過教化而棄惡從善表現(xiàn)得毫無信心。因此,他主張君主應(yīng)該“不養(yǎng)恩愛之心,而增威嚴(yán)之勢。”(《韓非子·六反》)另一方面,韓非子認(rèn)為人性也無須改變。人的自利本性非善非惡,只是一種自然狀態(tài)。既然自利不是“惡”,那也就無需改變了,反而可以利用人們的好利本性,通過物質(zhì)激勵或賞罰,來調(diào)動人們的積極性,進(jìn)而達(dá)到樹立權(quán)威、發(fā)展經(jīng)濟(jì)、維護(hù)統(tǒng)治的目的。
基于人性的變與不變,荀子與韓非子給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性處理方式。
荀子提出“逆性”的觀點,主張對人性加以改造,“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dǎo)之也。”(《荀子·性惡》)要通過“禮義”、“法度”,對人的自利本性進(jìn)行“正之”、“導(dǎo)之”。在人性由惡向善的“逆性”的過程中,荀子特別強(qiáng)調(diào)人為即“偽”的作用,他提出了“化性起偽”的觀點,即通過后天的道德教化、道德修養(yǎng)與踐行,實現(xiàn)對人性的改造,達(dá)到棄惡入善的目的。
面對不變的人性,韓非子提出了“順性因情”的主張。既然人性自利是人的自然本性,又無法通過教化得以改變,那么就只能接受自利本性的事實存在,并讓其順著人的本性自然發(fā)展。進(jìn)行賞罰、制定政策、嚴(yán)肅法紀(jì)必須以人的自利本性為依據(jù),要因循它,而不是否定它、改變它。
荀韓二人對人性的闡釋都是著眼于為他們的治國理念尋找最有力的人性論支持。荀子在性惡論的基礎(chǔ)上形成了“禮治”治國體系,而韓非子則在性私論基礎(chǔ)上找到了“法治”的治國之路。
荀子認(rèn)為人私欲的膨脹導(dǎo)致了“爭”“亂”和“窮”,為了避免這一嚴(yán)重后果,人類應(yīng)該對自己的欲望進(jìn)行控制,要做到這點,就必須創(chuàng)造出復(fù)雜的禮儀體系。“禮”是圣王為使人類免于自我毀滅而設(shè)計的一套道德規(guī)范體系,荀子相信“禮”可以轉(zhuǎn)化人性,通過“禮義以分之”可以使人各安其分、各盡其職,從而達(dá)到維護(hù)人倫秩序和社會穩(wěn)定的目的。因此,“禮”在他的治國理念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法律與正義的基石,從而形成了系統(tǒng)的“禮治”思想體系。
韓非子認(rèn)為人之性皆“好利惡害,自為自利”,在“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yǎng)薄”的戰(zhàn)國時代,根據(jù)“世異事異、事異備變”的原則,文王之政已不能行于后世,寄希望于通過德治來改變?nèi)诵赃M(jìn)而達(dá)到治平的理想,已經(jīng)完全不合時宜。因此,他在深刻體認(rèn)人性自利的基礎(chǔ)上,極力反對儒家的仁義道德,形成了系統(tǒng)的“法治”治國方案。一是主張利用人的好利惡害心理,通過厚賞誘導(dǎo)人民遵守法紀(jì),通過重懲、刑罰迫使人民不敢犯法;二是為使厚賞重刑達(dá)到預(yù)期目的,就必須使“法”成為最高且唯一的行為準(zhǔn)則并為人民所知曉,這就需要以吏為師,以法為教;三是權(quán)不旁落,中主能守。進(jìn)行賞罰、制定法律其目的是為了樹立君主的權(quán)威。因此,韓非子主張利用臣下避害趨利的本性,通過刑德即賞罰來控制群臣、維護(hù)君主統(tǒng)治的穩(wěn)固,“明主之所導(dǎo)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韓非子·二柄》)
綜上所述,韓非子既是荀子性惡思想的繼承者,又是其批判者。他根據(jù)當(dāng)時諸強(qiáng)紛爭、弱肉強(qiáng)食、欲望泛濫的社會現(xiàn)狀,從法家角度綜合諸子之說,跳出性善性惡的歷史紛爭,以推行法治理論為落腳點,建構(gòu)起自己獨特的自然主義性私論學(xué)說,故不能將其簡單地歸結(jié)為性惡論。(河北省社會科學(xué)基金項目課題組 作者:周娜 王維國)
先秦時期是我國古代人性論思想的形成階段。諸子百家從各自立場出發(fā),提出了各種各樣的人性論主張。荀子是“性惡論”的典型代表,而由于韓非子與荀子的師承關(guān)系,學(xué)界普遍認(rèn)為韓非子是荀子人性論思想的繼承者,甚至比荀子的性惡主張更極端。其實,這是一種誤解。韓非子雖就學(xué)于儒家的荀子,但卻另辟蹊徑成為法家,就其人性思想的基本立場與本質(zhì)精神而言,韓非子跳出了性善、性惡的分析框架。他所闡發(fā)的是一種自然主義的人性自私論。
荀韓均堅持人性是人“好利”的自然屬性,但在人性“好利”的評價方面,二者卻分道揚(yáng)鑣,荀子對“好利”做出了“惡”的價值判斷,而韓非子只是對“好利”進(jìn)行事實描述,不作價值評價。
荀子的人性論以人的自然本性為出發(fā)點,他把人的自然欲求看作人性,“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yīng),不事而自然,謂之性。”(《荀子·正名》)并將這種欲求歸納為“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同時,荀子對其社會危害做了詳細(xì)描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荀子·性惡》)在荀子看來,人好利之心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必然會導(dǎo)致爭斗與社會動蕩,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惡”。由此,基于儒家道德主義的立場,荀子將人“好利”的本性與倫理道德對立起來,最終對人性做了“惡”的價值判斷,“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
韓非子繼承了荀子以利欲為人之本性的觀點,認(rèn)為“好利惡害”是人的普遍本性,因此,物欲是人類生存的第一需要,是人們思考問題并指導(dǎo)其行動的原點。但是,與荀子直接將人性的好利惡害界定為“惡”不同,韓非子沒有把“善”與“惡”納入人性討論的范圍。對于人好利惡害的本能需要,韓非子突破了性善、性惡的分析框架,以一種自然主義的筆觸對人性只做事實描述,不做道德評價,既不以之為惡,也不以之為善,表現(xiàn)出價值中立的立場。
由于對人性評價的基本立場不同,在人性是否可變這一問題上,荀子與韓非子的論述也有著根本差別。
荀子認(rèn)為人性可以改變,也必須改變。一方面,人性改變具有可能性。無論圣人,還是普通民眾,其人性都是可以變化的,“途之人可以為禹”,人實際上的善與惡,可以通過主觀努力和后天環(huán)境熏染來實現(xiàn),“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nóng)賈,在勢注錯習(xí)俗之所積耳。”(《荀子·榮辱》)另一方面,人性改變又具有自覺性。“夫薄愿厚,惡愿美,狹愿廣,貧愿富,賤愿貴。”(《荀子·性惡》)每個人都向往美好的東西,荀子由此推論:“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荀子·性惡》)人們因知其性惡,所以才有“欲為善”的意愿與動力。另外,人性改變具有必要性。人性惡如果不加以改變,將會對個體發(fā)展、倫理秩序和社會穩(wěn)定帶來巨大危害,“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荀子·禮論》)因此,為避免社會紛爭、動蕩與窮困,必須對人性加以改造和限制。
與之相反,韓非子主張人的自利本性是先天決定,不能改變,也無須變化。一方面,韓非子堅持人性無法改變。在他看來,人的好利屬性是由人的生理需求誘發(fā)的,是人與生俱來的自然本能,不能改變。比如,民眾之所以會做善事,只是服從于外部壓力,并不是發(fā)自于由人性改變而產(chǎn)生的“義”,“民固服于勢,寡能懷于義。”(《韓非子·五蠹》)可以看出,韓非子對于人性可以通過教化而棄惡從善表現(xiàn)得毫無信心。因此,他主張君主應(yīng)該“不養(yǎng)恩愛之心,而增威嚴(yán)之勢。”(《韓非子·六反》)另一方面,韓非子認(rèn)為人性也無須改變。人的自利本性非善非惡,只是一種自然狀態(tài)。既然自利不是“惡”,那也就無需改變了,反而可以利用人們的好利本性,通過物質(zhì)激勵或賞罰,來調(diào)動人們的積極性,進(jìn)而達(dá)到樹立權(quán)威、發(fā)展經(jīng)濟(jì)、維護(hù)統(tǒng)治的目的。
基于人性的變與不變,荀子與韓非子給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性處理方式。
荀子提出“逆性”的觀點,主張對人性加以改造,“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dǎo)之也。”(《荀子·性惡》)要通過“禮義”、“法度”,對人的自利本性進(jìn)行“正之”、“導(dǎo)之”。在人性由惡向善的“逆性”的過程中,荀子特別強(qiáng)調(diào)人為即“偽”的作用,他提出了“化性起偽”的觀點,即通過后天的道德教化、道德修養(yǎng)與踐行,實現(xiàn)對人性的改造,達(dá)到棄惡入善的目的。
面對不變的人性,韓非子提出了“順性因情”的主張。既然人性自利是人的自然本性,又無法通過教化得以改變,那么就只能接受自利本性的事實存在,并讓其順著人的本性自然發(fā)展。進(jìn)行賞罰、制定政策、嚴(yán)肅法紀(jì)必須以人的自利本性為依據(jù),要因循它,而不是否定它、改變它。
荀韓二人對人性的闡釋都是著眼于為他們的治國理念尋找最有力的人性論支持。荀子在性惡論的基礎(chǔ)上形成了“禮治”治國體系,而韓非子則在性私論基礎(chǔ)上找到了“法治”的治國之路。
荀子認(rèn)為人私欲的膨脹導(dǎo)致了“爭”“亂”和“窮”,為了避免這一嚴(yán)重后果,人類應(yīng)該對自己的欲望進(jìn)行控制,要做到這點,就必須創(chuàng)造出復(fù)雜的禮儀體系。“禮”是圣王為使人類免于自我毀滅而設(shè)計的一套道德規(guī)范體系,荀子相信“禮”可以轉(zhuǎn)化人性,通過“禮義以分之”可以使人各安其分、各盡其職,從而達(dá)到維護(hù)人倫秩序和社會穩(wěn)定的目的。因此,“禮”在他的治國理念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法律與正義的基石,從而形成了系統(tǒng)的“禮治”思想體系。
韓非子認(rèn)為人之性皆“好利惡害,自為自利”,在“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yǎng)薄”的戰(zhàn)國時代,根據(jù)“世異事異、事異備變”的原則,文王之政已不能行于后世,寄希望于通過德治來改變?nèi)诵赃M(jìn)而達(dá)到治平的理想,已經(jīng)完全不合時宜。因此,他在深刻體認(rèn)人性自利的基礎(chǔ)上,極力反對儒家的仁義道德,形成了系統(tǒng)的“法治”治國方案。一是主張利用人的好利惡害心理,通過厚賞誘導(dǎo)人民遵守法紀(jì),通過重懲、刑罰迫使人民不敢犯法;二是為使厚賞重刑達(dá)到預(yù)期目的,就必須使“法”成為最高且唯一的行為準(zhǔn)則并為人民所知曉,這就需要以吏為師,以法為教;三是權(quán)不旁落,中主能守。進(jìn)行賞罰、制定法律其目的是為了樹立君主的權(quán)威。因此,韓非子主張利用臣下避害趨利的本性,通過刑德即賞罰來控制群臣、維護(hù)君主統(tǒng)治的穩(wěn)固,“明主之所導(dǎo)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韓非子·二柄》)
綜上所述,韓非子既是荀子性惡思想的繼承者,又是其批判者。他根據(jù)當(dāng)時諸強(qiáng)紛爭、弱肉強(qiáng)食、欲望泛濫的社會現(xiàn)狀,從法家角度綜合諸子之說,跳出性善性惡的歷史紛爭,以推行法治理論為落腳點,建構(gòu)起自己獨特的自然主義性私論學(xué)說,故不能將其簡單地歸結(jié)為性惡論。(河北省社會科學(xué)基金項目課題組 作者:周娜 王維國)
責(zé)任編輯:C009文章來源:光明日報(2013-09-30)
下一條:劉邦憑什么戰(zhàn)勝項羽上一條:管仲的商戰(zhàn)興國之道
相關(guān)信息
沒有記錄!
精彩展示
沒有記錄!
評論區(qū)
友情鏈接
商都網(wǎng)
中國網(wǎng)河南頻道
印象河南網(wǎng)
新華網(wǎng)河南頻道
河南豫劇網(wǎng)
河南省書畫網(wǎng)
中國越調(diào)網(wǎng)
中國古曲網(wǎng)
博雅特產(chǎn)網(wǎng)
福客網(wǎng)
中國戲劇網(wǎng)
中國土特產(chǎn)網(wǎng)
河南自駕旅游網(wǎng)
中華姓氏網(wǎng)
中國旅游網(wǎng)
中國傳統(tǒng)文化藝術(shù)網(wǎng)
族譜錄
文化遺產(chǎn)網(wǎng)
梨園網(wǎng)
河洛大鼓網(wǎng)
剪紙皮影網(wǎng)
中國國家藝術(shù)網(wǎng)
慶陽民俗文化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