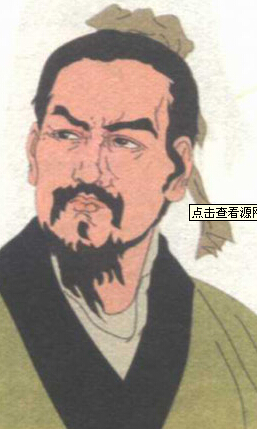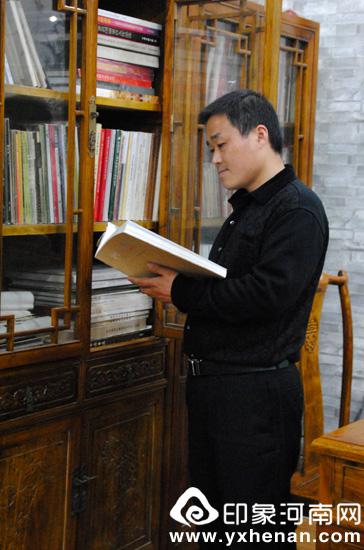-
沒有記錄!
韓非”矛盾“思想的歷史成因
2014/12/25 15:56:53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矛盾律是邏輯學的基本規律之一,其基本內容不會因地域、民族、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區別。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產生過程,卻有著傳統文化的特色。“矛盾”一詞之所以產生于中國古代的韓非,是有其歷史的必然性的。
一、“矛盾”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
韓非所處的時代,百家爭鳴已持續幾百年,但相左的思想仍然在激烈地爭論。孟子所言的“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即歸墨”(《孟子·滕文公下》)的政治思想紛繁復雜的情況仍然存在,如何培養“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仍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雖然此期間也有老子的要求在認識事物中,要正確地從事物的正面規定性中,分析出與之相反的反面規定性,從而在語言表達的形式上,以“知此兩者亦稽式”(《老子·六十五章》)的認識法式為歸結的辯證認識,但其“正言若反”的思維方法,只是一種帶有道統思想的“辯證法的名學”[1]。雖然墨子通過揭露論敵混淆概念的邏輯錯誤,將“悖”的“違反”、“背逆”的最初意義上升為一個具有邏輯學意義的概念,并通過對各種“悖”現象的語言分析,揭露了論敵自相矛盾的邏輯錯誤。[2]但這個具有邏輯學意義的概念并沒有在總結“矛盾”現象的意義上得到普及。雖然莊子從“齊物”、“齊是非”、“辯無勝”的心路軌跡,以其“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的反調,提出了“辯無勝”,以反對名辯思潮的不諧和音來剽剝儒墨。但“辯無勝”仍有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首先是關于“是非”及“是非”的標準問題;其次是由“是、非”所引申出來的關于如何認識矛盾、解決矛盾以及對于是非的判斷有無一個規范認識的思維規律的問題。它所要解決的問題是仍然是當時百家爭鳴中所出現的是非“樊然殽亂”的現實情況。[3]而從理論上解決這些問題的是后期墨家及韓非。
后期墨家對矛盾律思想的理論分析,是借助于“取辯于一物”來完成的:“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不當若犬。”(《墨子·經說上》75)“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墨子·經說下》135)這些分析表明了,其一,一對相互反對的對立判斷不能同時都正確:“是不俱當”;其中必有一個是錯誤的:“必或不當”。其二,判斷正確的,就為“辯勝”的一方:“當者勝也”。但這些分析只說明了矛盾律的基本內容及邏輯要求,并無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定名”。而韓非在探索“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思慮)規矩也,圣人盡隨于萬物之規矩”(《韓非子·解老》)的過程中,“觀往者得失之變”,索察當時社會的政弊成因,從分析自然、社會、思維中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對立的現象,開始了解決這些問題的艱難之旅。
二、韓非對“矛盾”現象的考察
韓非在總結前人對矛盾現象認識的成果上,對舉凡自然、社會、思維中所存在的大量矛盾現象進行了系統的分析。
從自然界來講,對立的事物不能相容:“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韓非子·顯學》以下《韓非子》只注篇名)
從人的生理特點來講,對立的功能不能并成:“左手畫圓,右手畫方,不能兩成。”(《功名》)
從社會領域來講,在社會現實中,當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是建立在利害的基礎之上的:“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而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賣,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備內》)
在家庭中,父母與子女也是利害關系的結合:“父母之于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妊,然男子受賀,女之殺之者,慮其后便,計其長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六反》)
在君臣之間也存在著利害沖突:“君臣之利異”,“臣利立而主利滅”(《內儲說下》);“君臣異心”,相交以“計”(《飾邪》)。
至于君民之間的對立就更為嚴重了:“君上之于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于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六反》)
還有,法術之士與當涂之人也是勢不兩立,不可同存:“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其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奸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人與當涂之人,不可兩存之仇。”(《孤憤》)“且法術之士,與當涂之臣,不相容也。……而勢不兩立。”(《人主》)
在治理國家上,有賢治與勢治的不可兩立:“夫賢之為道不可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賢與無不禁之勢,……不相容亦明矣。”(《難勢》)
不僅自然、社會領域存在著廣泛的沖突和對立,在思維領域,也存在著大量的沖突和對立現象。如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儒者之一派)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于臧獲,行直則怒于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斗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儀。……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謬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顯學》)韓非認為如果對這些相反思想都認可,必然會造成是非不明、思想混亂的局面。
又如,圣堯與賢舜也不可兩譽:“歷山之農侵畔,舜往耕焉,期年,圳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嘆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之為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圣堯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奸也。令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之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圣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不可兩譽”。(《難一》)從對民有利的角度講,賢舜就應該非堯,圣堯就應該非舜。而儒者也是一概加以溢美之辭。韓非認為這也必然會造成是非不明、思想混亂的局面。
又如,君主言行對立的現象:“圣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以同道也。……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為治相反也。”(《詭使》)
所以,“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為治相反也”就是是非不明、思想混亂;而“世一治一亂者”,也就是這種是非不明、思想混亂的惡果:“無功而受事,無貴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五蠹》)
正是由于考察了這許多自然、社會、思維領域的種種對立和沖突,韓非認識到了這許多現象的“勢不兩立”,并將其歸結到自己的政治主張上來:“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難勢》)并以楚人賣矛、盾的寓言說理故事,從認識論角度,揭示了這些矛盾對立現象之間的“不兩立”特點:“楚人有鬻盾與矛者,譽之曰:‘吾盾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盾之說也。”(《難一》)
并且韓非還從談說論辯的思維規律角度強調了對立的判斷之間,“為名不可兩立”:“人有鬻矛與盾者,譽其盾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之。以為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道不可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賢與無不禁之勢,此矛盾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難勢》)
所謂“不可同世而立”,強調的是“同世”這一概念。也即,在同一時間、同一條件下,“不可陷之矛”與“無不陷之盾”這兩種相互對立的事物不可能同時存在。因為,在“吾盾之堅,物莫能陷也”,和“吾矛之利,于物無不陷也”的對立之間,蘊涵著一種自相矛盾,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把這一矛盾現象揭示了出來。因為,“吾盾之堅,物莫能陷也”,即言“一切東西都不能刺穿我的盾”,此也蘊涵著“我的矛不能刺穿我的盾”。而“吾矛之利,于物無不陷也” 即言“我的矛能刺穿一切東西”,此也蘊涵著“我的矛能刺穿我的盾”。在同一時間、同一條件下,這種現象是不可能同時存在的。這也就是為什么“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原因所在。
所謂“為名不可兩立”,則是強調了在同一時間、同一條件下,針對同一事物所構成的不相容,反映在思維上的不相容,或對于針對同一事物所構成的一對相互對立的判斷,思維不能同時予以肯定為真,其中必有一個為假。這也就是韓非所說的,“夫是(肯定)墨子之儉,將非(否定)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今兼聽雜學謬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實際上是為這種“安得無亂乎”所做的一個注腳。
總之,“不可兩存……不可兩立”的思維進程,表明了客觀事物“兩存”的對立,是思維中“兩立(可)”對立的原因,韓非以其反對“矛盾之說”的態度,將“矛盾”現象提高到哲學和辯學的高度予以了評斷:“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并且用“矛盾”一詞形象地概括了思維基本規律中矛盾律的基本內容:兩個相互反對的命題不能同真,必有一假。明確地表述了矛盾律的本質。
三、“矛盾”定名的歷史必然性
韓非的“矛盾之說”,為先秦以來諸子談說論辯中所體現出來的矛盾律思想做了最后的總結,使矛盾律思想從“悖”、“謬”、“惑”等詞語上根基于“矛盾”一詞上,并使這種矛盾的對立比之“兩端”、“兩可”更為直觀形象,使后人對于矛盾律思想的理解更為清晰,其“定名”過程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思維的必然性。
1.歷史的必然性
先秦時代,諸子百家均“思以其道易天下”,其間的相左思想交鋒可謂激烈。既要思想交鋒,就希望以一個思維標準規范是非認識,而韓非之前對這種是非相反的現象,大多以“悖”、“謬”、“惑”等詞語來表示,缺乏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大家都理解接受的定名。
而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僅僅以這些詞語來決定這些思想交鋒的“是非”,顯然不夠方便。“求勝”、“求當”的歷史要求,也必然要求產生一個能夠簡潔判定“勝”、“當”的“定名”,從而洞察是非論辯的理性要求,賦予“辨勝”、“論當”的理性內容。在這種情況下,以往對事物“種類”的認識必然要地進一步深化。、
亦即,事物自身的發展變化雖然是毋庸置疑的,但在確定的條件下,也即在一定的時間、空間內,事物的存在仍然有著它“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的本質規定性,從而使我們對這個林林總總的大千世界有一個確定性的認識。因此,對于確定的事物存在,人們仍然是可以認識它的,并以此而判定它的“是非”。思維判斷中的是非對立,就是從對認識對象屬性的同異比較開始的。
既然思維判斷中的是非對立是從對認識對象屬性的同異比較開始的。那么,在這種認識過程中,思維完全可以按認識對象的相同屬性,取同進行歸納;按不同屬性,取異進行劃分,進而形成思維認識中的同異判斷。正確反映這種同異的判斷為真,為“是”,否則便是為假,為“非”。基于此,思維判斷的是非真假是靠所判定的客規事物的同異聯系是否符合實際情況所決定的,思維的是非矛盾根源于客觀事物的同異矛盾。但是,兩者還是有所不同,客觀世界的同異矛盾無時不在,卻從來不存在是非矛盾,是非矛盾只存在于主觀思維判斷中,在思維判斷以是非矛盾認識事物的同異矛盾的過程中,它始終受思維規律的規范。在抽象思維階段,它抽取共同之點,撇開差異;在辯證思維階段,它遵從多樣性的規定。因此,解決思維中的非矛盾,只有根據思維規律的規范,堅決按事物的質的規定性劃分是非、真假的區別界限,肯定真的思想,否定假的思想,而不允許在同一個思維過程中,沒有條件地讓思維中的是非矛盾調和及同一。
這個探索思維標準以規范是非認識的工作,如我們在本文第二部分中所描述的,由韓非深化了。
2.思維的必然性
所謂思維發展的必然是指,事物與事物之間的對立,人與人之間的對立,人自我身心的對立,有著一致的道理,有著相同的同異比較,因此可以通過觀象取類,由此及彼,得到普遍性的認識。如果這種具有普遍性的認識能夠得到一個合適的載體,這種思維的必然性就呼之欲出了。而韓非在對先秦諸子關于矛盾律思想研究的深化中,自《詩經》開始的“善假于物”(《荀子·勸學》)的類推方法,自然也會進入韓非的視野。
“類推”作為一種思維法式,具有一定的依據、取法標準、思維進程等,它即是經驗積累的結果,又是理論總結的結晶。[4]在這種“取辯于一物”(晉魯勝《墨辯注序》)的類推中,“取辯于”什么,有其隨意性,只要兩個思維對象或用來用來做“比”的事物與所要論證的事物之間具有“舉相似”(《孟子·告子上》)的同一性,就可以斷定對于它們的思維取舍也即肯定或否定也應該相同。顯然,這種類事理上“同情”、“同理”的同一性,可以增強“說明”的力度。
雖然這種“取辯于一物”的隨意性對于古人論辯各種政治倫理問題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但作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思維規范又顯然不足為用。因此,由莊子所開創的由隨意類推發展而來的寓言說理故事,不但以其“意在此而言寄于彼”的類推特點,更以其具有完整的故事結構、具有寓意性、故事奇特卻又合理、語言簡潔等特點,在其隱喻手法的意義轉移的穩定性與合理性的根據中,[5]充當了韓非“矛盾之說”的形式。而這種形象化的直觀感受,很容易讓人相信寓言所預設的故事情景存在,從而從淺顯的小事理中,理解并接受其所蘊涵的深邃道理。《韓非子》一書中所保存的大量的寓言說理故事,并且這些故事大多已經積淀為一個個成語,融化在中華傳統文化的血脈里,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方法,就鮮明地表明了韓非已經是在自覺地使用了這種寓言說理故事的形式,在“取辯于一物”地“說理”了。而這理應是古人善“譬”思維方法的自然延伸。
四、結語
清人方以智曾經說過:“設教之言惟恐矛盾,而學天地者不妨矛盾。”(清方以智《一貫問答》)此話鮮明地表述了人們對于思維中的矛盾與事物中的矛盾的認識。至如今,“矛盾”一詞的廣泛使用,對于人們自覺保持思維的確定性,避免自相矛盾,時刻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并且,只要人類還在思維,“矛盾”一詞就將永遠燦爛。此功歸于韓非,彪炳千秋。但是,韓非通過寓言說理故事所概括的“矛盾”之說,與傳統邏輯學與現代邏輯學的矛盾律思想相比,還是有區別的。
亞里士多德的矛盾律思想主要是指同一主項不能有相互矛盾的謂項。他說:“所討論命題只涉及肯定與否定兩種情況,每一個肯定命題都有一個對立的否定命題,每一個否定命題也有一個對立的肯定命題。”[6]“兩個互相矛盾的判斷不能同時對于同一對象為真,兩個反對判斷也如此。”[7]由此可以看出,亞里士多德的矛盾律思想所涉及的是具有矛盾關系和反對關系的一對直言判斷。
而現代邏輯是這樣定義矛盾原則的:一個邏輯系統是一致的,當且僅當,不存在任何公式A,A和非A在這個系統內同時都可證。換言之,在一個無矛盾系統內,沒有在該系統中同時都可證的一對相互矛盾的公式A和非A。
而韓非的矛盾律思想,從“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來看,應該是兩個主項不同,謂項也不同的關系命題(判斷)之間的真假關系問題,似乎并非是A和非A的一對直言矛盾命題之間的真假關系問題。但從對韓非的“矛盾之說”所做的分析來看,“矛盾之說”顯然也蘊涵著一對矛盾命題:“我的矛不能刺穿我的盾”與“我的矛能刺穿我的盾”。韓非雖沒有明確地指出這一點,但是,從他認識到“不相容之事”“不得兩立”來看,無論是矛盾關系還是反對關系,它們之間的談說論辯共性,都足以從他所揭示的不相容的思想不得同真中得以體現了。而從對立現象歸二為一的目的來看,矛盾的對立在“同世”、“兼時”、“同器”所明示的同一時間、同一條件的因素規定下,也只能是一真一假,一是一非了。因此,對于韓非的矛盾律思想,我們用不著去苛求它是適用于矛盾關系還是反對關系,直言判斷還是關系判斷,只要理解了他的“不相容之事”是“不可同世而立”,就足以藉此認識為什么“今堯舜不可兩譽”的“矛盾之說”了。
另外,韓非盡管前無古人地提煉出了“矛盾”一詞,并以此為根據,大量地使用著兩刀論法以及演連珠進行著論辯,[8]但是,法家對于“勢不兩立”的“不可兩存之仇”的矛盾解決辦法,卻是為了避免“兩則相爭,雜則兩傷”(《慎子·德立》),只能歸二為一,體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君主為“一”,也即“威不二錯,政不二門”(《管子·法禁》);體現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是“末產不禁,則野不辟”(《管子·修權》);體現在思想領域,則是禁絕異端,使“一國戚,齊士義”(《管子·法禁》)。韓非則將上述一切歸于“一民之軌莫如法”(《五蠹》),體現在思想領域則是消滅異說,擯棄百家,統一思想,惟法是從,故而“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于法令者必禁”(《問辯》)。如是,韓非的矛盾觀就與他所希冀的強權政治、文化專制主義緊密地扯在了一起。而這種“是非”的標準問題,同如何認識矛盾、解決矛盾以及對于是非的判斷有無一個規范一樣,同樣是先秦時代歷史發展的必然和思維發展的必然所致。
【參考文獻】
[1] 張汝倫編:《理性與良知——張東蓀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第365頁。
[2] 張曉芒:《中國古代論辯藝術》,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6~106頁。
[3] 張曉芒:《莊子“辯無勝”的名辯學意義與現代啟示》,《晉陽學刊》2002年第1期。
[4] 張曉芒:《中國古代的推類思想與中國古代宗族社會》,《中國哲學史》2003年第1期。
[5] 張曉芒:《中國古代論辯藝術》,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225頁。
[6] 亞里士多德:《解釋篇》,17a30~31。
[7] 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第15~16頁。
[8] 張曉芒:《中國古代論辯藝術》,第334~3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