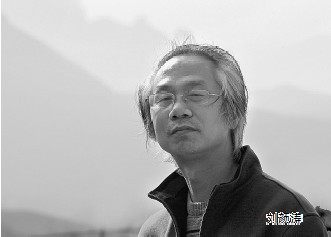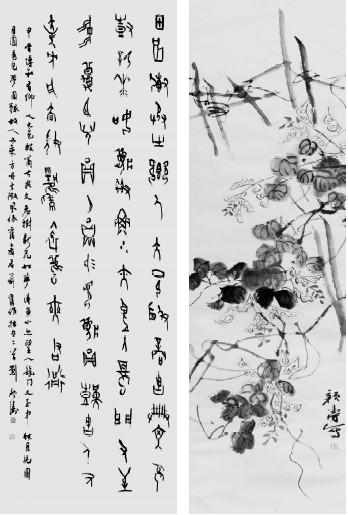傅維學(xué)書(shū)法三
金玉甫(首都師范大學(xué)中國(guó)書(shū)法文化研究院博士)安陽(yáng)書(shū)家..[詳細(xì)]
-
沒(méi)有記錄!
劉顏濤:文化是書(shū)法的支撐
2013/10/25 17:41:42 點(diǎn)擊數(shù): 【字體:大 中 小】
記者:您的朋友,無(wú)論是書(shū)法圈里的還是圈外的,都特別喜歡您,他們認(rèn)為您有真性情,所以特別親近您。
劉顏濤:我雖不敢自詡?cè)缣K東坡的“一肚子不合時(shí)宜”,卻亦是一介話語(yǔ)冷硬、不諳世事、不懂迂回、不善應(yīng)酬的書(shū)呆子。覺(jué)得自己有一身的臭毛病,之所以還能得到那么多好朋友的理解和寬容,就是因?yàn)樵谏鐣?huì)上滾爬打拼了這么多年,依然不失本色,稚氣未脫,癡情依舊,赤心猶在。因?yàn)樾郧檎妫约旱暮芏嗳秉c(diǎn)朋友們都不計(jì)較了,這也算是“一白遮百丑”吧。
記者:真性情。您喜歡自己的這個(gè)性格嗎?大家都特別喜歡。
劉顏濤:不過(guò)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罷了。各人有各人的性格,誰(shuí)也不可能做到讓每個(gè)人都喜歡自己。自己的性格不是自己刻意做出來(lái)的,是由先天的基因、生活的環(huán)境、成長(zhǎng)的閱歷等各方面綜合形成的。我也知道自己的性格有很多弱點(diǎn),也想努力改變,但的確很難。
記者:您的這個(gè)真性情,是不是讓您自己覺(jué)得活得很自在?
劉顏濤:我覺(jué)得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只要保持自我而又尊重別人,在不傷害別人的情況下,自己樂(lè)意什么樣的生活方式就以什么樣的方式生活。想想自己除了躲進(jìn)小樓寫(xiě)寫(xiě)畫(huà)畫(huà),又會(huì)干什么?又能干什么呢?我只能也安樂(lè)于這種適合我的方式生活。
記者:您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樣的?
劉顏濤: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從農(nóng)村走出來(lái)了,不能像古代文人說(shuō)的那樣,過(guò)晴耕雨讀的生活,也不實(shí)際。但是自己還是很向往那種可以作為虛擬的理想化的生活狀態(tài)。在那個(gè)世界里,我覺(jué)得很純粹,很干凈,天天沉醉在這里面,看看書(shū)、寫(xiě)寫(xiě)字,寫(xiě)寫(xiě)字、看看書(shū),累了,去田園走走、轉(zhuǎn)轉(zhuǎn),覺(jué)得那種生活方式最適合我,悠哉游哉,樂(lè)在其中。
記者:您給自己營(yíng)造了一個(gè)很單純、很干凈的世界。
劉顏濤:這個(gè)世界應(yīng)該說(shuō)是書(shū)法人生、藝術(shù)生活,那是前人和先賢們營(yíng)造出來(lái)的,是他們營(yíng)造的那種理想的桃花源夢(mèng)境,使我向往。
記者:您營(yíng)造的這個(gè)小環(huán)境達(dá)到了那樣的一個(gè)意境了嗎?
劉顏濤:沒(méi)有,而且清楚今后也不可能真正達(dá)到,但那種獨(dú)立自由、質(zhì)樸天然、率性本真、單純干凈仍然是我雖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標(biāo)尺與境界。
記者:您剛才告訴我,您最欣賞林語(yǔ)堂的《生活的藝術(shù)》。是這樣嗎?
劉顏濤:林語(yǔ)堂先生著有《生活的藝術(shù)》一書(shū),講到生活的藝術(shù)化才是真正的、最高的生活。我們則可以引申為,藝術(shù)的生活化也應(yīng)該是真正的、最高的藝術(shù)。正如余秋雨先生在《筆墨祭》一文中談到:“在毛筆文化鼎盛的古代,文人們的衣衫步履、談吐行止、居室布置、交際往來(lái),都是與書(shū)法構(gòu)成和諧,他們的生命行為,整個(gè)兒散發(fā)著墨香。”我覺(jué)得書(shū)法藝術(shù)現(xiàn)在從書(shū)齋能走入神圣的殿堂進(jìn)入展廳,把它打扮得更富麗、更高貴,這是對(duì)書(shū)法、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藝術(shù)的尊崇,因?yàn)橹袊?guó)文明綿延5000余年,文字首當(dāng)其功。伴隨著漢字發(fā)展而成長(zhǎng)的中國(guó)書(shū)法,基于漢字象形表意的特征,在一代又一代書(shū)寫(xiě)者的努力之下,最終超越其實(shí)用意義,成為一門(mén)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字無(wú)法企及的純藝術(shù),并成為漢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在中國(guó)知識(shí)階層來(lái)看,書(shū)法是中國(guó)人“澄懷味象”、寓哲理于詩(shī)性的藝術(shù)最高表現(xiàn)方式,它凈化、提升了人的精神品格,歷來(lái)被視為“道”、“器”合一。中國(guó)書(shū)法包羅萬(wàn)象,從孔孟釋道到各家學(xué)說(shuō),從宇宙自然到社會(huì)生活,中華文化的精粹,在其間都得到了種種反映,書(shū)法無(wú)愧為中華文化的載體。所以,書(shū)法這種藝術(shù)在世界上跟其他任何藝術(shù)門(mén)類相比都不遜色,應(yīng)該有它的尊貴。另一方面,社會(huì)發(fā)展到現(xiàn)在,從鋼筆代替毛筆,又到現(xiàn)在以敲擊電腦代替手工書(shū)寫(xiě),雖然書(shū)法藝術(shù)的血脈在世風(fēng)陵替中,始終頑強(qiáng)不息地流動(dòng)著、傳承著,但畢竟書(shū)法跟生活的那種融入、融匯少了,在生活里面的那種體現(xiàn)也少了。比如一把扇子,它體現(xiàn)的不單單是扇風(fēng)取涼、驅(qū)趕蟲(chóng)蚊等,也是一種文化藝術(shù)載體,一首詩(shī)詞,一幅書(shū)畫(huà),便是一種風(fēng)雅和品格,一種悠然和從容。但現(xiàn)在已很少用了,取而代之的是冬暖夏涼、時(shí)令不分的空調(diào)。再者,現(xiàn)在很少有人寫(xiě)信了,書(shū)簡(jiǎn)信函這一傳統(tǒng)交流的形式已被電話、短信、電子郵件所替代,春節(jié)期間用來(lái)拜年的賀卡,也改用了打印的文字。這些電腦統(tǒng)一制造的東西,千篇一律,全然沒(méi)有了親筆書(shū)寫(xiě)文字特定的表情與溫度,沒(méi)有了與字相對(duì)、如見(jiàn)其人的親切情感。不能從那種盡可以看出一個(gè)人的習(xí)慣、心境、性格和命運(yùn)的最確切的印記——文字手跡中,體驗(yàn)出“見(jiàn)字如晤”的時(shí)空穿越感覺(jué)。以前過(guò)春節(jié),也都是自己書(shū)寫(xiě)春聯(lián),提前幾天就買(mǎi)紅紙,買(mǎi)墨,或者兄弟姐妹幫著裁紙倒墨,出謀劃策,或者在大人指導(dǎo)下讓小孩子一試身手,張貼后在街上互相走走,看看誰(shuí)家寫(xiě)的字好,看內(nèi)容,看書(shū)體,這些都給生活帶來(lái)很多樂(lè)趣,那時(shí)生活窮困,但非常有情趣。我覺(jué)得藝術(shù)跟生活融合到一起的時(shí)候,就給生活帶來(lái)了詩(shī)情畫(huà)意。
現(xiàn)在少有人停下腳步慢慢地欣賞路邊的風(fēng)景,直接乘飛機(jī)、坐高鐵,只有始點(diǎn)和終點(diǎn)而沒(méi)有途中。把沿途的風(fēng)景都忽略掉的時(shí)候,就感到現(xiàn)代人那種都市的焦慮:忙碌而失落,緊張而空虛。人活得太物質(zhì)、太現(xiàn)實(shí)了,什么都慢不下來(lái),富有詩(shī)意化的那些想象就減弱了,所以為什么都說(shuō)現(xiàn)代人想象力比過(guò)去退化了,心境中沒(méi)有清靜從容了,沒(méi)有風(fēng)花雪月了,沒(méi)有閑情逸致了,距啟發(fā)性靈的大自然遠(yuǎn)了,離藝術(shù)化的生活環(huán)境也遠(yuǎn)了。
記者:但是現(xiàn)在我們不可能再回到過(guò)去了,該怎么辦呢?
劉顏濤:雖然過(guò)去的那些年代,有那么多令我們懷念和需要堅(jiān)守的美好東西,但畢竟是“細(xì)雨連芳草,都被他帶將春去了”,時(shí)光不會(huì)倒流,時(shí)勢(shì)不可逆轉(zhuǎn),社會(huì)發(fā)展,時(shí)代潮流,會(huì)有適合這個(gè)時(shí)代的新方式、新事物、新追求。
但是傳統(tǒng)文化應(yīng)該延續(xù),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幾千年,先人給我們留下來(lái)的這些瑰寶,還是應(yīng)該守望、繼承、弘揚(yáng)。在古代寫(xiě)字都是以毛筆為工具,書(shū)法又是仕途必需,是以一種極其廣闊的社會(huì)必需性為背景的。他們?cè)跁r(shí)間和精力上有著更大的投入,產(chǎn)生得特別自然、隨順、誠(chéng)懇。現(xiàn)在毛筆書(shū)法實(shí)用性越來(lái)越弱,已失去了它原來(lái)生存的環(huán)境,“終究是一條刻意維修的幽徑,美則美矣,卻未免失去了整體上的社會(huì)誠(chéng)懇”。而且,社會(huì)分工越來(lái)越細(xì),每個(gè)人都會(huì)選擇不同的謀生手段和生活方式,但無(wú)論從事什么職業(yè),以哪種生活方式安身立命,寫(xiě)一手好字,仍是不同人群的共同需要,因?yàn)閷?xiě)好字是一個(gè)人的臉面,是一個(gè)人的形象。書(shū)法雖然不能成為每個(gè)人賴以生存的手段,卻能體現(xiàn)每個(gè)人的文化素質(zhì)、藝術(shù)修養(yǎng)和生活品位。而且,書(shū)法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精髓,只有對(duì)民族文化自尊、自信,才能有民族的自愛(ài)、自豪。所以說(shuō),書(shū)法普及還是有必要的。但是僅僅普及還不夠,還是要有一些人去提高,哪怕是很少的一些人,真正有憂患意識(shí),有歷史感,有使命感,有責(zé)任感,敢于把自己作為一個(gè)苦行僧,作為一個(gè)殉道者,把畢生的精力用到這方面,哪怕在某些方面被人視為跟這個(gè)時(shí)代有脫節(jié)、有隔膜,真正地去貼近于原汁原味的書(shū)法本質(zhì),使書(shū)法這一“最中國(guó)”的傳統(tǒng)藝術(shù)在當(dāng)代發(fā)揚(yáng)光大,不能讓“一陣風(fēng),留下了千古絕唱”的歌詠成為哀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