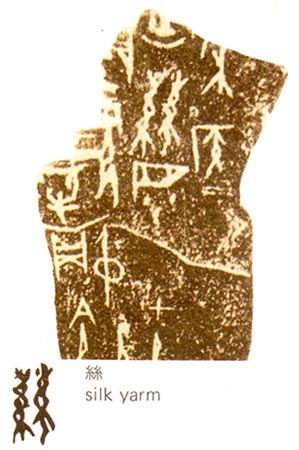-
沒有記錄!
周易文化與河洛文化一脈相承
2013/10/21 17:37:57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五千年文化寶庫中的絢麗瑰寶,其內涵博大精深,名揚海內外。周易文化源于河洛文化,為我國文化之根。河圖乃指無文字時代氣候圖,環形象征為天,洛書是中國遠古時代的方位圖,方形象征為地,天圓地方。從其方位看,洛書與河圖一樣,上南下北,左東右西,說明與萬事萬物生成、變化之規律的深邃理念等同,后發展為周易,除方位異曲同工外,奇數為陽,偶數為陰,奇偶相生濡化及“數”、“象”也同族同宗。尤其是在易卦與河洛文化意蘊中均含有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之規律。今天,我們站在這孕育古老文明的土地上,著眼于中原崛起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放眼全球化浪潮和文化經濟日益融合的時代潮流,共同研討河洛文化,這對于進一步弘揚優秀文化傳統具有深遠的歷史與現實意義。
河圖、洛書的淵源多從古代儒家關于《周易》和《洪范》兩書的來源與傳說。《易•系辭上》載:“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傳說伏羲氏時期,有龍馬從黃河出現,背負“河圖”;有神龜從洛水出現,背負“洛書”。伏羲氏根據“圖”、“書”畫成八卦,即是后來周易的來源。從河洛的探源數理、精義而言,通常人們視河圖為先天,洛書為后天;河圖為體,洛書為用,河洛乃說明宇宙間萬事萬物的根本原理;為形上與形下之道,為先天、后天八卦之緣由;更為歷代道統之衍繼,四圣心法之相證,是天人合一之橋梁。因此《周易》被儒家稱之為五經之首,并冠為經典中的經典,哲學中的哲學。
易學博大精深,宇宙萬物生存,往來造化之“理”,天地盈虛之“道”,先天后天之“名”,大生廣生之“德”,動靜失得之“時”,仰觀俯察之“法”,近遠諸物之“取”,道德性命之“究”,出入內外之“度”,剛柔相推之“動”,倔身相感之“生”,窮理盡性之“義”,內圣外王之“學”等無不源于易。易之所以被稱為群經之首,圣賢至尊,因其是中國學術思想之源頭活水,更是有史以來傳承文化之中樞。孔子曾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故易學之義,高深莫測,其變化應用無窮;內中闡明天道、地道、人道之宇宙至理,昔日孔子講易傳授門人至“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以此《易經》一書,乃啟示陰陽正反之理,抉明動靜闔辟之象,貫通三才而化成人文,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凡形上之道與形下之器,有關宇宙人生精神、物質之奧秘者,無不包涵。而大凡之歷史、文化、學術、思想、政治、宗教、天文、地理、物理及六藝之文,諸子之術,百家之宗等,也皆從此孕育而出。
然綜觀古今學者,諾貝爾獎得主,悉稱其理論源于易。這也成為“崇德而廣業”、“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之例證。漢書《藝文志》曰:“易為諸經之源。”宋朱熹則贊曰:“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以著名微積分和二進位(二元式)數學而名震世界的17世紀德國大哲學家兼數學家賴布尼茲曾說:“我的不可思議的發現,就是六千多年前中國伏羲氏,古代文字秘密發現。”又說:“易圖真是宇宙間最古老的科學紀念物。”
由此可見《易經》一書,為群經之首,萬經之王,無所不貫,無所不包。上以窮生化之初,下以辨變易之軌,幽以探于心神,明于合于日月,遠以微于四極,近于求于一心,而后天地生成,物類化育也。這是中國文化思想的結晶,也是實踐人生哲學必讀之書,無論處世為人,成功立業,治國安邦,造福人類均大有裨益。
周易與人類生活無不息息相關。生活易經是一個嶄新的卻又涵蓋傳統的觀念。自有易經以來,易經就用于生活之中。但在上古時代,易經應用范圍并不廣,往往只限于王庭內巫師所用,而且針對重大事件進行占卜來定決策。迨至孔子“韋編三絕”之后及孔門弟子的有益探索,《易經》一書所包含的哲學內涵,尤其是形而上學中的“本體宇宙論”與“本體倫理理學”的內涵,被發掘出來,《易經》得以更廣泛應用于人生和社會發展,成為儒家所崇德而廣業之書。其套用含義有二:一是知的含義,從思考易經預測所包含的宇宙變化中取得通變的智慧,以用于對萬事萬物的理解;二是德的含義,從反思易象所包含的價值中取得德行的義理,以用于做人處世的行為。這是易經所以發展為孔門的易傳理由。不管易傳十翼是否出自孔子之手,基于“帛書易經”的發現,孔子從人的生命與生活中揭示易的含義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上,孔子把“學易”與“學詩”與“學禮”都看成人生所以能立,所以能思與所以能行的根本事業,在這基礎上,他才能夠做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如果我們要尋找一個在生活中實踐易經智慧的最佳典型,舍孔子而無他人了。
在生活實踐中,易學之所以有時得不到很好的倡導和推廣,除社會上個別人存在認識上的偏見與誤解外,主要源于易學路徑上的兩個極端:一是追求玄理化與象數化的奧秘,而遠離實際的運用;再就是追求短暫的利益與實用,脫離了知識與智慧的開發。我們必須從一個更寬廣的視野來認識易經的智慧,把易經的玄理與象數用于生活之中,這就是我們所理解的“生活易經”的要旨所在。
在“生活易經”中,儒家常以不同的視角窺探易學在生活中的實用性與實踐性價值取向,如對時間含義的重視;對空間含義的重視;對生命與生活全局的反思與認識;對人生與世界變化的體會與理解;對宇宙萬物存在的價值與意義的思考,尤其是在世界經濟一體化、信息化、高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更應重視人性的培護與人格的充實,尤其要有參天地化育的宇宙本體精神,方足以維護天地之正氣,保持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和諧。
然而,研易者且不可將研讀易經用于算命、斷卦、看風水、識地理等小技上,并作為炫耀和謀生的工具,自稱“半仙”、鐵口直斷之徒,而是要將易學的精神不斷提升,以所具三才之德,發揮天人合一與相感之意,以樸素的哲理,調適心靈,體天察地,以仁義之道,修己以安人,達者兼善天下,力達大人境界,品味人生。
河洛文化貫于宇宙,統于萬理,其探源、易理、精義、真諦雖有浩如瀚海般的神秘與神奇,且又被世人稱為千古不解之謎,但在今天,在周易被省政府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并有望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同時,我們有責任對其進行詮釋與解讀,更有義務把河洛文化研究不斷引向深入。(作者系市政協副主席、中國安陽周易研究會名譽會長 劉曉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