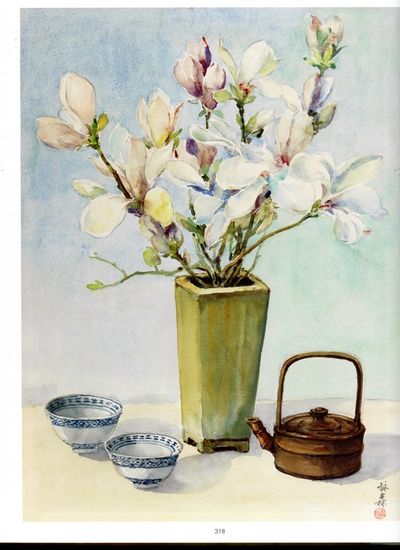-
沒有記錄!
限定和超越:談中國水彩畫的問題
2013/10/23 11:50:11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中國水彩畫所面對的問題是,從西方引進的水彩畫尚缺乏中國本土文化的根系,而且自身傳統短缺。這不僅因為水彩畫在中國的歷史不長,還因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障礙,國人對西方傳統了解亦不深。與傳統中國畫相比,中國水彩畫既沒有大量的創作積累,也沒有豐富的理論積淀。
水彩畫的名稱源自英文俗稱的water-color,其意就是水加彩,指以水為溶劑稀釋顏料的方式作畫。水彩畫作為外來畫種,是最早傳播西洋畫的便捷媒介,對西方美術及其觀念傳入我國和推動中國現代美術發展起著重要作用。水彩既是中國人最早接觸西方繪畫的主要媒介,也是中國人最容易接受的繪畫語言,因為它與傳統中國畫,特別是水墨畫、墨彩畫,有許多相通之處。不過,水彩畫對傳播和普及西方繪畫觀念的貢獻,在中國現代繪畫發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還是常常被人們忽視。
不以種類論成敗
建國初期,也許是出于對藝術的教育功能的重視,以江豐為代表的美術決策者,以革命的主題性創作作為衡量標準,于是繪畫門類被分成幾等。例如:將油畫稱為大畫種,因為它作畫比較從容,能夠精雕細刻、便于修改,適合創作以人物和情節為主的主題性繪畫;而版畫有革命傳統和復制功能,也被列為重要畫種,只是它在技術上比較麻煩,尺寸也不宜太大,因此影響力似乎顯得弱于油畫;水粉畫,也被稱為廣告畫,材料便宜成本低,便于修改,適合于大量印刷的宣傳畫和群眾宣傳欄的報頭插畫,在當時擁有較重要的地位;至于中國畫,由于歷史上缺少對人物的寫實經驗,所畫人物大多禁不起解剖、透視、明暗等寫實標準的挑剔,看上去不夠嚴謹,雖是民族的,但需要進行改造,或者說,要加強畫家們的人物畫和寫生、寫實的訓練,方能應對主題性創作的需求,但因為它是民族的,所以后來居上,備受重視;而水彩畫不易修改,故尺寸不宜大,基于當時畫家的寫實能力尚低,不適合作以人物為主的主題性繪畫,但由于較受觀眾喜愛,所以被寬容地稱為“輕音樂”,有時還是“無標題”的,自然就被列于末等,屬于小畫種。因此,習慣上常有油、國、版或國、油、版的排序。在三大類中水彩還排不上位次,為此,水彩畫家常常背上包袱,耿耿于懷,與其他種類的畫家相比,難免有些自卑。
水彩畫是個開放體。無論觀念還是技巧,水彩畫都極富彈性,可以在中西之間、各畫種之間吸納眾長,游刃有余。它不但與國畫、油畫相通,而且亦與版畫相通。例如版畫的黑白、明暗、陰陽等關系以及其高度的概括性等,與水彩語言相近,亦可為水彩所用。如何兼得眾長而不為其所囿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從西方水彩畫歷史上看,水彩畫也經歷過擺脫類似油畫的作畫步驟,放棄追逐油畫效果,避免成為其附庸的過程,到19世紀,開始呈現出水彩畫獨特的輕快明朗簡練的效果,顯示出與眾不同的繪畫特性,其地位也因此得到提升。
觀念決定形態
要恢復水彩畫家的自信,首先應擺脫水彩畫的附庸身份,樹立水彩畫首先是繪畫的觀念,正如林風眠說的,“繪畫的本質是繪畫,無所謂派別也無所謂‘中西’” ,他并不認為不同畫法和派別本身對作品價值有什么決定性影響,當然也不會在意畫種大小的區分,以及由此人為造成的畫種對立和門戶偏見。因此,水彩畫家和研究者不應為水彩畫之名所困,而要把關注點從“技”轉向“道”,觀念創新是繪畫發展的根本。
19世紀英國以透納為代表的浪漫主義繪畫,尤其是水彩畫,影響到后來法國的印象派,并通過后者沖擊了沙龍的審美標準,推動了20世紀繪畫的新潮,其革命意義不可低估。但今天在中國,水彩畫能夠引領觀念的意義和作用被忽視了,似乎拱手讓給了油畫和國畫等所謂大畫種。至少在水彩畫的展覽和批評中,觀念創新一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雖說有其客觀的歷史原因,但從主觀上看,水彩畫家大多過分拘泥于技法的實驗和描述性的繪畫語言,無意中忽視了與時俱進的觀念創新,放棄了對繪畫話語權的觸摸和掌控。談到水彩畫發展的戰略時,擅長版畫和水彩畫的王維新已注意到觀念創新的重要性,他在上世紀末說過,“為使本畫種更好地向前發展,我們應在觀念上進一步拓寬,以全新的思維觀念和即將到來的新世紀的發展規律相交融,在藝術語言上更加多樣化,在創作中盡量避免依樣描摹和復制自然的被動習慣模式。”
與油畫、國畫、版畫等領域一樣,水彩畫也有自己的難題,承受著沉重的壓力,其表現為畫家們的一種危機感。在1949年以前,水彩畫與油畫地位大致相當,同屬于西畫,沒有什么區別,甚至尺寸大小上一般也沒有太大差距。當時水彩畫只是西畫的一種形式,或者說是一種工具,尚未形成獨立的意識,水彩畫家也沒有感受到危機。水彩畫家的危機感首先出現在新中國成立之后,而中國水彩畫歷史的低谷出現在“文革”時期。當時,水彩畫處在主題性油畫、民族性國畫、政治化年連宣和版畫的縫隙之中,因自身人物造型能力的欠佳,被認為難以承擔重大題材,又缺少民族文化傳統積淀,只具形式上的觀賞性,故被稱為無標題、輕音樂、小畫種,被排除在主旋律之外,最終被徹底邊緣化了,取而代之的是作為宣傳畫、年畫的水粉畫或用水粉、水墨等水溶性顏料創作的連環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