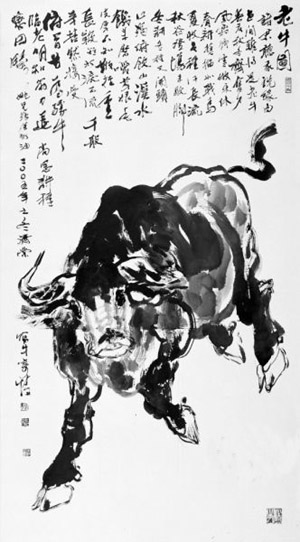-
沒有記錄!
不懂筆墨精神素描再好都不是中國畫(2)
2013/11/20 15:45:12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劉濟榮:我不完全同意這句話。如果不研究傳統,不懂得筆墨精神,素描再好都不是中國畫。就在國畫界而言,很多人的素描能力也是讓人佩服,而一旦他拿起毛筆,藝術的感覺就沒有了。
收藏周刊:這是不是說明人物畫乃至中國畫的變革需要反思?
劉濟榮:一個美學體系的建立肯定有成功的地方,自然也有尚不盡人意的缺陷與不足,人物畫體系同樣如此。我們應該抱著辯證的態度來看待。中國筆墨精神與西方造型體系的融合,依然是當下人物畫、中國畫的重要課題,我們并沒有徹底解決好。“用素描、西方造型手段改造中國畫”的說法是不對的,我們任何時候都應該堅持民族本位,堅持筆墨與線條的根本性價值;但如果只強調筆墨,而沒有造型基礎,人物畫也不會有今天這樣的發展。所以,你看20世紀以來的人物畫家,畫的好的往往都是吸收了外來的營養,造型功力非常高。黃胄這樣的大家也曾直言“后悔沒有學會素描,如果學好了素描,那創作的面貌肯定有更好的提升”。
收藏周刊:也就是說,素描不過是一個提升表現生活能力的重要手段而已。
劉濟榮:為了更快提升表現現實生活的能力,學習素描是必要的。但是,必須在素描中吸收某些為國畫專業所容的現代科學的因素,不是無原則地或喧賓奪主地學習素描,以至企圖以素描代替國畫的寫實基礎。我們只能適當地將素描當做國畫寫生法中的一個步驟,采取某些有益于國畫造型的要求,使它能服務國畫線描的造型特點。
談筆墨
“畫家畫古人,精神要先回到古代”
收藏周刊:其實,美術史上對徐悲鴻“素描為一切造型藝術之基礎”的質疑,一直不絕于耳,在創作上,則有“新文人畫”等思潮,在視覺形式上對徐悲鴻等人所建立的現代美術體系給予反思。比如,王孟奇、劉二剛等人的創作,就與您的作品形成截然不同的風格。您如何看他們的人物畫創作?
劉濟榮:每個人的生活方式、觀察與表現的手法都會不同,藝術的差異性可以理解,也必須鼓勵。讓每位藝術家各自建立自己的藝術特色或者山頭,藝術才會真正多樣化,才會走向健康。
收藏周刊:不少人物畫家的藝術手法是傳統的,題材也是古時候的。對于以古人為題材的人物畫創作,您如何評價?
劉濟榮:可能因為自己孤陋寡聞,我沒有看到太多讓我眼前一亮的作品。很多人畫古人,卻沒有讓人感受到古代的精神面貌,對古人的理解太簡單了。古人不是不能畫,關鍵是畫家的精神首先要回到古代,回到古人所處的歷史環境。而如果創作主體的精神沒有回到古代,畫出來的東西肯定就是概念化的。人物畫就是要表現人的精神面貌,如果這點都做不到,那就沒有多大意思了。
收藏周刊:精神怎樣“進入古代”,又該怎樣從傳統中汲取資源?
劉濟榮:現在,我們一說傳統,就將時間的鐘表扳回秦漢、唐宋,或者元明清。僅僅就時間跨度看,傳統太大了,太豐富了,不能籠統化。要知道,唐宋的藝術傳統與元明清是不一樣的,一個是氣象的博大,一個是筆墨的精妙。
到底是說的哪個時代的傳統呢?或者說哪一塊文化傳統呢?再說,徐悲鴻、蔣兆和所建立的美學的體系,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其實也已經形成了我們的傳統,或者說內化為我們這個民族傳統的一部分。
談書法
“中青年畫家重視書法,才是中國畫的希望”
收藏周刊:您的書法無不骨力勁峭,又不失放逸之氣與意趣之美。您的這種畫家兼書的路子,對您的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劉濟榮:我首先要讓我的字很“配”我的畫。現在,很多畫家不敢在畫面上題字,或者亂題一通,破壞了畫面的完整性。好的題字都是“錦上添花”,給畫面加分,而非“畫蛇添足”,反給畫面減分。畫家為何不能借書法讓畫面“錦上添花”呢?
收藏周刊:在您看來,廣東畫家的書法水平如何?
劉濟榮:坦白地說,咱們廣東畫家的書法水平不太高,書法藝術能夠獨自成立、能充分掌握骨法用筆的畫家并不太多。我想,廣東的繪畫如果想提高一個層次,畫家就要多練習書法,提高書法水平。簡單地說,書法是畫家急需打破的瓶頸。中青年畫家重視書法,這才是中國畫的希望。
收藏周刊:您在教學中是不是很重視引導學生研習書法?
劉濟榮:我個人是很強調書法的,特別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后,但很多年輕學生并不以為然,覺得“畫好就行了”,不愿意把時間花在寫字上。我一直很欣賞中國美院老院長潘天壽先生的做法,有一個“三三三制”的課程設置,即學生畫畫占總課時的1/3,書法占1/3,讀書占1/3,真切希望這個經驗能在全國推廣。
收藏周刊:您已年過八十,還在堅持創作嗎?
劉濟榮: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我的重心就慢慢偏向書法了。現在,書法在我的生活中占據了很大的比重,很多時間都是在寫字。書法用來表達情感更好,我也把書法當做陶冶性靈的最高娛樂方式,也是我晚年最高的藝術追求,已遠不止是我吸收繪畫營養的手段。其實,書法比畫畫要難得多,別看就那么一根線,但太微妙了、太抽象了,可能窮盡一生都難真正窺其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