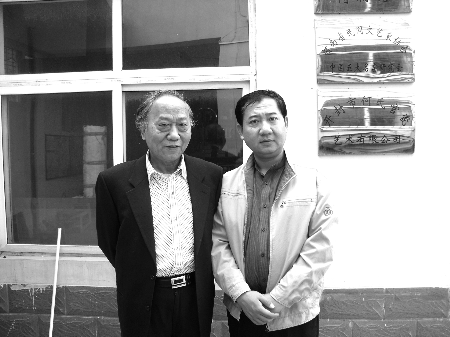精彩推薦
熱點關注
專題推薦
-
沒有記錄!
熱點排行
- 1、北宋官瓷:紫口鐵足 絕響天下
- 2、北宋官瓷:中國青瓷藝術的最高成就
- 3、讓汴繡在法制春風中飄揚
- 4、朱仙鎮木版年畫魅力奪人
- 5、千年古剎相國寺
- 6、汴繡淵源
- 7、"針灸穴位碑"殘石拓片(北宋)
- 8、(刺繡)開封汴繡
大相國寺佛樂 千年梵唄唱到今天
2013/4/2 17:38:50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佛樂的源起
佛樂又稱梵樂或梵唄,不獨是佛教弘揚教法和贊頌佛菩薩等美好事物的一種獨具宗教特色的聲樂,也是佛事活動中必不可缺的形制,廣泛地存在和運用于佛教儀規之中。梁朝慧皎法師所著《高僧傳》曾考證言:“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弦為善。見佛之儀,以歌贊為貴”。也確實,從佛教住世的角度來看,佛經的贊和偈均是通過唱、誦、念才能表達出來,而歌詠佛經伴以管弦之聲,引贊入樂,達致中和、清凈,也是“梵唄”的本意。由此可見,存在和運用佛典及佛事活動中的佛樂,當然緣起于佛教,并同時莊嚴著佛教,且為佛教的弘揚和傳播帶來了深遠的祝福和激勵;另一方面,佛教歷來也猶重運用音樂來“宣唱法理,開導眾心”,提倡音樂在服務佛教教義中的作用,所以佛經與佛學文獻大多涉及音樂,并多方面闡述了佛教對音樂的諸種看法。
佛樂在中國的傳播
佛樂和佛教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白馬馱經,佛教傳播中華,佛教梵唄也開始在我國流傳。早期的中國佛教活動自然完全承襲梵唄形制,即佛教史上稱做“西域化”講經的吟唱方式,梵唱由是冉冉升起于中華大地。佛教史上著名的天竺國竺法蘭大師及康居國康僧會大師,猶對佛樂在華夏的傳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大力推動了佛樂在中國的發展,二人被后世尊稱為南北梵唄祖師。宋大相國寺方丈贊寧在其《高僧傳o續誦篇》言:“原夫經傳震旦,夾譯漢庭,北則竺法蘭,始真聲而宣剖;南惟康僧會,揚曲韻以諷誦”,稱贊竺法蘭和康僧會為中國南北兩地的佛樂的領袖,并道出中國梵唄之南北差異的特點,北以“雄直宣剖”而長,南以“哀婉揚曲”以取勝。而二者佛樂的基本個性的形成,也尊定了佛樂在中國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通過絲綢之路,自東漢佛教的傳入,箜篌、琵琶、篳篥、都曇鼓、雞罈鼓、銅鈸、貝等樂器,及許多著名樂曲,如《摩訶兜勒》等,以及鼓吹、饒歌、蘇袛婆琵琶七調音樂理論,也相續從佛教國家傳入我國,對我國音樂及音樂理論的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公元802年,古印度驃國王太子舒難陀,親率樂隊32人及舞蹈團來華訪問,并贈送樂器十種,極大地推動了我國佛教音樂的發展,諸多上善因緣,終促使我國唐宋以來更進一步的發展且形成了完善的燕山十八調等著名佛樂。
佛樂的中國化
如佛教傳入中國,融會中國儒學和玄學至唐朝最終完成佛教的中國化一樣,佛樂也經歷了佛教普臨東土的需要而中國化的情形,這也是佛教隨緣化物的表現。從漢語發音度而言,漢語發音的口型,音樂的長短,音韻的高低,以及文化素養、審美觀點,欣賞習慣的不同,其旋律也必然隨之改變。梁慧皎法師在其《高僧傳》言:“梵音重復,漢語單奇,用梵音詠漢語,則聲長而偈短;用漢曲詠梵文,則韻短而詞長”。基于這樣的語言矛盾,融會中國各種傳統音樂,探索新的梵唄聲韻以適應弘法需要,成為一項急待解決的問題和工作。隨著人們的不斷攝取中國傳統音樂來探索新梵唄,并使大量典型的中國傳統曲子融入梵曲,其結果也必然導致佛樂的中國化。相傳魏曹植賞游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雅哀婉,深動其心。曹植獨聽良久,大有體會,乃慕其音節,結合我國傳統音樂典籍《瑞應本起》,創作梵曲三千,流傳天下,使得梵曲在傳播實踐中獲得重要的重建和發展,對佛樂“改梵為秦”中國化情形也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后世因此尊曹植為中國梵唄的始創者。
佛樂的發展
佛樂在中國的發展,基本上是佛樂“中國化”的逐步完成和完善。自曹植創作極富中國特色的三千梵曲之后,東晉高僧慧遠大師又以“以歌詠法、廣明教義”為旨,創唱導制。亦即提倡以俗講方式宣講佛教經義,并注重俗講時唱頌的音樂性,因此大師吸收了大量當地音樂素材編制佛曲,用以俗講經義,此也為佛樂民間化取得了良好的開端。接蹱慧遠大唱導制進一步發展而來的講經形式,稱謂“變文”,其對佛樂的發展更是推波助瀾。“變文”主要是講經通俗化、故事化,融佛教精神于中國古代故事之中,形象生動地宣傳了佛教教義。由于“變文”以唱白形式相結合,唱詞為韻文體,且唱頌普遍采用民眾喜聞樂見的民間曲調,這對佛樂的民間化和普及都具有極大的推動作用。至唐代,隨著佛教傳播的深入人心和繁盛發展,佛樂吟唱也隨著佛事活動的隆盛而獲得了廣泛的發展空間,尤其是唐宮廷出于對佛教的信奉,不僅將佛樂引入皇室齋天、祈福、報謝、追悼及宗廟祭祀等傳統宗法活動中,并在禮娛宴樂中,也演奏佛曲,伴以歌舞助興。佛樂的地位得以極大地提高,佛曲從而成為唐代的主要音樂體裁;另一方面,佛教活動愈是大眾化、地方化,佛樂也就愈來愈要求民間化,用民間曲調和漢語聲韻來取代舊的“梵”聲已成為必然之勢。至宋代,佛樂完全采用民間曲調,并普遍為各寺院采用,這就是最終形成了中國佛樂的最基本的音韻調律,確立了自己的風格形成。時至今日,許多名山寶剎,仍是承襲自宋、元、明以來的佛樂曲調,只是由于地方方言之別,各地寺院在具體唱法上自然存在著不同差異。
大相國寺的創立及其佛樂發展狀況
大相國寺始創于北齊天寶六年(555年),其寺址原為戰國時期魏公子無忌之故宅,極富文化歷史意義。寺院初名建國寺,后毀于戰火。唐長安初年(701年),高僧慧云云游至開封,夜宿繁臺,看到城內汴河有紫氣沖天,天明徒步河岸,又見此地瀾漪中有天宮影,參差樓閣九重儀象,如彌勒佛之兜率宮院,慧云隨發愿建寺。后所督造的彌勒佛像,大放金光,照徹天地,震動人心。巧合的是,睿宗帝是夜也于夢中感通寶像奇瑞,且靈應肇發,大有感悟。而為紀念自己由相王龍飛稱帝,應其祥瑞,睿宗帝御筆賜名,對大相國寺以特別眷顧,使其極盡造化,風光莫比;另一方面,開封自古便為大梁故都,天下要沖,至唐代雖為河南道統轄下一地方單位,但自從隋代開通濟渠以來,更為“水陸都會”而名揚天下,商貿和文化活動均十分頻繁和發達,堪為地靈人杰。得益于古都開封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和壯闊的人文活動等上善因緣,大相國寺自創立之初便融入中國歷史文化的洪流之中了,唐代著名畫家吳道子,雕塑家楊惠之、王溫,文化巨匠李邕,以及當時京城第一琵琶大師善本長老的佛樂傳人虛真大師等,均為大相國寺的文化建設留下了光輝的史跡。可以說,大相國寺自建寺之始,在帝王政治權利的直接關照下,加上源源不斷的歷史文化名人關懷的諸多善緣,寺院不獨鑄就了其獨具秉賦的政治文化構架,更成就了其薈萃天下文化精英的文化胸懷,終以文化寺院而享譽天下,成為一方精神圣地。而基于寺院崇高的社會地位和文化傳統,伴隨佛教的弘傳而發展起來的佛樂,也自然與大相國寺的文化建設有著不解之緣。有關寺院和民間音樂的歷史典籍中,大相國寺自創建之始便有樂僧越仁大師、虛真大師在寺院演奏佛樂的記載。至唐天寶年間,大相國寺已出現完整的樂隊,并于高僧在法華經開講之前,敬獻佛樂以報謝佛恩來吸引聽眾。到唐大歷年間,寺院將向佛獻樂定為制度,開壇講經必由樂隊獻樂,以表莊嚴和虔敬。這一傳統的形成也使得寺院開始注意對佛樂曲目的整理和收藏,這無論對寺院佛樂的弘傳和建設,都有著重大意義。時至今日,單從佛樂曲目的傳承來說,由于大相國寺至今仍保存著大量較完整的古樂譜,研究中原佛樂和古代音樂的學者,都必須把大相國寺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這在客觀上,便使得寺院在傳統音樂方面秉賦一種廣泛的代表性,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源于寺院繼承民族優秀文化的優良傳統,大相國寺佛樂,已成為整個中原傳統音樂的典型代表大相國寺佛樂的成熟
唐代承南北朝隆盛的法運,佛教盛行全國,并由華土開始外傳東南亞諸國。大相國寺自經睿宗命名題額,在封建最高統治者大力維護下,迅即發展成為汴州最大的寺院。不僅如此,唐肅宗至德年間,經肅宗帝批準,將河南道統僧錄司設在大相國寺內,這使得寺院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這一變化,對推動大相國寺的佛教建設和文化建設,作用非凡。僅就佛樂而言,佛樂至唐代已發展為黃金時代,其最為顯著的特征是,唐代宮廷音樂中從七步樂到十部樂中,來自佛教國家或以佛樂模式建立起來的樂隊竟達六、七部,可見朝廷對佛樂的喜好和偏愛。而借助朝廷的支持,佛樂的發展當然也更臻鼎盛。
《洛陽伽藍記》描述當時寺院佛樂活動稱“梵樂發音,驚天動地”,可謂盛況空前。正處上升階段的大相國寺也不例外,此時不僅組建了專業的樂隊,且在吸收古樂曲和舞曲來充實佛樂方面,也有著長足的發展。見諸多種文獻記載,被譽為“華夏正音”的大相國寺大型佛樂變奏曲《駐云飛》,經由寺院專業樂僧的整理和創作,終于使這部古代樂曲演變成一部完整的佛樂作品。全曲共有六百一十九個小節,包括九個樂段,另有引子和尾聲的散板部分,作品甚為完整。尤值一提的是,該曲采用許多不同的佛教素材和各種變奏手法,并用統一的佛樂風格貫穿起來,如佛日中天、普臨天下,氣勢甚是博大、恢宏。從一定意義而言,象征佛光普照,降幅世人的大型佛樂《駐云飛》的圓滿問世,實為佛樂成熟的一個標志,其與當時唐代歌舞大曲相比也毫不遜色,或更有過之。此外,歌頌佛教天神摩訶迦羅的傳統樂曲《耍孩兒》,以及《普庵咒》、《水先枝》、《柳含煙》等一大批系列佛樂也在此時匯集或創作于大相國寺,并由此傳誦天下。僅唐崔令欽撰《教坊記》及明永樂年間《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目錄》等音樂典籍,所載唐代大相國寺佛樂就達三十余首(部)。而能為諸音樂史籍所關注,可見大相國寺佛樂的影響和地位了。
北宋時期大相國寺的佛樂
北宋定都開封,作為京都最大佛剎,大相國寺倍受北宋帝王的優禮和崇奉,被北宋王朝欽命為 “為國開堂”的“皇家寺院”,并設中央直屬管理機構“左街”于寺內,與“右街”開寶寺同理和管轄全國佛教事務。大相國寺由此一躍而成為天下首剎,寺院建設也達至空前的鼎盛,轄六十四禪、律院,占地達五百四十余畝。不獨高僧云集,也是朝廷巡幸、祈報、恭謝、祈禱等國禮祝禱的首選道場,以及招待安置外國使節和外國僧侶重要場所,堪為全國中外文化及佛法交流的中心。隨著大相國寺發展的盛勢,大相國寺的佛樂至北宋也達到最隆盛的階段,一方面,由于朝廷對寺院的崇奉,國家許多重大活動和典禮都放在寺院舉行,寺院為適應朝廷禮儀的需要,無論是樂隊還是所演奏的佛樂,都必須更專業更規范,演奏的技藝也必須更高超,入微和莊嚴。因此,大相國寺重視音樂,培養專職樂僧,嚴格訓練技巧和認真演奏樂曲的優良傳統自然形成;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參與以及在財力和人力和物力方面的支持,大相國寺自北宋初期即組織起龐大的專業樂隊,其狀況是空前的。此外,在朝廷的大力支持和安排下,大相國寺在寺內專門修建了演奏七弦琴的佛樂專業“劇院”--維摩院,以及在大殿前修建的專供一般游人和香客欣賞佛樂的演奏廣場--樂棚,這些其他寺院絕無僅有的專業設施,足以說明寺院佛樂發展的鼎盛及專業。更為重要的是,受命于朝廷且秉負“為國開堂”正大使命的大相國寺,每屆主持均由朝廷任命,而出于組織和參與朝廷在寺院舉行的各種禮儀活動,他們大多精通樂律,并在朝廷的要求下,赴任以后必將全部音樂資料做一次梳理工作,使之更加充實完善,并記錄存檔。故大相國寺歷史上不僅涌現大批造詣很高的專業樂僧,且千百年來,佛樂資料也一直得以能妥善地保存下來,實為寺院所建立的良好制度的原因。
北宋佛樂的基本特點
中國佛教自宋代起開始強化佛教化導世俗社會的世間功能,把出世求解脫之道與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統一起來,追求學佛與做人的統一,以及對社會的道德教化,并將愛國主義精神引進佛教,與祖國共命運。這種充滿新鮮空氣的狀況即佛教史上所說的佛教世間化。宋代佛樂也是如此,無論在道德上、習俗上,還是藝術上,都有創造和成就。此時期的佛樂,有別與唐以前的特點,佛樂繼續發展和完善。這種發展和完善,主要表現在技藝實踐上的深入,以及在社會世俗生活中的深入、社會風氣與社會心里的深入和人們情感生活的深入。僅就大相國寺的佛樂而言,自北宋起,由于寺院和朝廷以及民眾廣泛深入的接觸和合作,寺院佛樂大量吸收了民間音樂和宮廷音樂,形成了自身隨緣隨機且以提升道德,凈化人心,祥和社會為目標的自由風格,寺院不僅以“皇家佛剎”自律,致力與朝廷的各種禮儀活動,以莊嚴國土為己任,在寺內創建維摩院式供雅士欣賞“陽春白雪”的音樂廳,且設置樂棚常年舉辦“下里巴人”式普及性大眾音樂盛會,把寺院的佛樂推及到社會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這種宋以前不多見的佛樂活動的形式和盛況,在深入人心以及在最大程度上廣擴佛樂影響的同時,也成就了大相國寺佛樂雅俗共賞的基本特征和海納百川的雄輝氣勢與文化胸襟。此外,由于大相國寺在教內獨高的社會政治地位,做為一座秉負皇命擁有管理天下寺院職能的寶剎,其本身的佛樂,也自是一種標準和典范,不僅在最大程度上代表著帝王禮儀之樂,也是中原傳統音樂最典型的代表。
宋以后的大相國寺佛樂
自金兵攻陷東京,宋室南遷。大相國寺的佛樂活動大受影響。后南宋又在杭州建大相國寺,開封大相國寺不少高僧及樂僧又南渡臨安,曾經籍帝王之力創建的規模宏大的樂隊大為失色。據史料載,北宋大相國寺樂隊鼎盛時期人數達400人之眾,至元初樂隊人數已不足70人,可見其差別之大。不過,好在大相國寺向以皇家寺院著稱于世,在地方和佛教界一直有著非凡的影響,雖宋室南渡,大相國寺仍被中原一帶寺院奉為領袖寺院,故大相國寺樂隊雖人數大為遞減,但每遇寺院有重要的佛事活動,城內其他寺院及城外子孫小廟的樂僧,均會云集寺院,與大相國寺樂隊一道奏樂唱贊。元代詩人陳孚在其感荷“大相國寺天下雄”的詩作里,仍有“三千歌吹燈火上,五百纓縵煙云中”的感嘆,這說明大相國寺至元代,佛樂仍頗具氣勢,縱樂隊編制較北宋不可同日而語,不過佛樂仍為寺院標志性的事物,為人們所注目。而隨著元代雜劇的興起,著稱于世的大相國寺佛樂,也深入其中,尤其是中原地區,不僅大型的劇目吸收了不少佛樂,三、五成群的小型佛樂隊,更是活躍于民間,為鄉村父老操辦各種紅白之事,演奏人們耳熟能詳的大相國寺佛樂,影響甚為廣泛。
明朝開國后,朝廷仍詔命在大相國寺設置僧綱司,管轄開封府各州縣的寺院僧侶。并指令大相國寺重新整理佛樂資料,重組樂隊,服務于社稷。明朝在開封第二代周王朱有燉,酷愛戲曲,因崇慕大相國寺的佛樂盛名,故與大相國寺有著甚深的交誼,他曾組織聯合寺院樂僧,收錄當時流行于世的雜劇三十一種,名“中州弦索”,并指示寺院安住梨園班子,在大相國寺內設置舞臺,使四方藝人云集寺內,每日清唱不斷,佛樂繞梁的大相國寺由此也成為一所音樂雜劇的故鄉,直至明末。
崇禎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義軍與明守城官兵互決黃河,至使開封遭滅頂之災,大相國寺也造毀滅性破壞,寺僧四處逃亡,奔走他鄉,樂曲大多失傳,大相國寺佛樂由此一蹶不振,更談不上什么發展了。清初順治皇帝詔命重修大相國寺后,雖有樂僧不斷零星回寺,但卻無力組建成規模的樂隊了,只是應付佛事,做一些有償的演奏和向佛獻樂活動。直至清末民初,寺院承宋、明文化娛樂的傳統,籍寺院處于鬧市中心之便利,又成為市民娛樂中心,寺院佛樂才藉民間娛樂的興勢有了點起色。是時,寺院經年百戲雜陳,鼓書、相聲、墜子、皮影、說書、戲法等民間娛樂光彩爭華,相映生輝,雖然與北京的天橋,濟南的大觀園一道被專家學者譽為中國曲藝的三大發祥地,但所憾寺院馳譽天下的佛樂卻退而為次,未能占據主導地位,得到發揚光大。1927年軍閥馮玉祥主政河南,動用軍警,驅僧滅佛,沒收寺產以充軍餉,改寺院為市場,至使大相國寺的佛樂與佛教一樣,遭到毀滅性的打擊。1938年日軍侵占開封期間,重新恢復寺院的佛事活動,大相國寺也再度成立了佛樂演奏機構,并設置專職樂僧十余人,每逢佛、菩薩紀念日,還邀請外地樂僧到寺獻樂,雖規模較之太平盛世相去甚遠,但也還式笙管齊鳴,法音繚繞,大相國寺佛樂仍為中州之冠。
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歷史的原因,僧人再度離寺,大相國寺被改為公園,跟隨而來的連年政治運動,就連佛教都被視為封建迷信,更遑論佛樂了;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運動,寺內所保留的樂器和樂譜,全部被付之一炬,大相國寺佛樂活動完全終止,徹底云消煙散。
當今大相國寺的佛樂建設
1992年,在黨和國家宗教政策的關懷下,大相國寺重新做為佛教活動場所開放,千年古剎,迎來中興,不數年時間,大相國寺煥然一新,寶像莊嚴、道風盎然,各項佛教建設,都納入了正常的軌道。
1998年,在已故中國佛協會長趙樸初大德的舉薦下,心廣大和尚晉寺任主持。大和尚晉寺后,在趙樸初會長的囑托下,把繼承寺院優秀文化傳統,弘揚大相國寺高邁超拔的佛教文化,作為寺院建設的一項主要工作來抓,并分步驟對寺院傳統文化進行梳理。2002年,為使大相國寺歷史上極富盛名且已近失傳的佛樂再度重光,大和尚親任團長,成立了大相國寺佛樂團,開始致力于大相國寺傳統佛樂的挖掘整理,并先后聘請十余位國內著名的音樂教授,到寺指導和培訓樂僧。至2002年底,大相國寺佛樂團已培養專職樂僧20余人,寺院佛樂文獻的整理也取得不少成就,基本上能適應各種場合及各種規模的演奏。2003年,寺院佛樂團在大和尚的精心操持下,已大有進境,開始走出寺院,參加國內外各種重大佛事活動及社會慈善活動的演出,受到了社會各界廣泛的好評。大相國寺平和、悠揚、沉靜、清涼的佛樂,猶如璀璨明珠,光照大地。尤其是2004年應邀赴澳門參加澳門回歸祖國5周年的盛大演出,更是以整齊的陣容,恢宏的氣勢而折服無數觀眾,為近百家媒體所報道或轉載,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為天下注目。
今天,大相國寺佛樂團在心廣大和尚的運籌下,正在向更規范、更典型、更精深的方向深入發展,重振唐宋神韻,澤益天下友情,實為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大相國寺水到渠成的發展方向和目標。
大相國寺佛樂的構成
大相國寺佛樂與帝王政權和鬧市民眾長期水乳交融的甚深關系,頗具隨緣化導世俗社會的世間功能,演奏形式上也多有禪心對現實生活的觀察思維,是慈和的人生志向步向覺悟的音樂。因此大相國寺佛樂雖分為聲樂和器樂兩大類,但也兼有聲情并茂的歌舞,且相互之間密不可分,素有“歌聲繞梁,絲管嘹亮,諧妙入神”的贊譽。大相國寺的聲樂包括梵唄和勸世曲兩種:梵唄,《楞嚴經》解釋為“梵土之贊頌也”;“梵”是古印度語“梵摩”的簡稱,意為“清凈”、“寂靜”、“離欲”;“唄”乃“唄匿”音譯之略,意為“止斷止息”或“贊嘆”,指佛教徒以短偈形式贊唱佛、菩薩的頌歌。故從清凈心生發,修心頌佛,安然清唱佛經、偈贊且以歡喜心歌頌佛法,贊頌佛之功德的,均可稱為“梵唄”,如《戒定真香》等。勸世曲可看作佛樂中的通俗歌曲,歌詞多為高僧和文人所作,內容涉及民族英雄,歷史名人,歷史事件,民間故事以及二十四孝,三綱五常等傳統道德范疇,主要用于僧人作法會時,宣傳佛教,教誨世人揚善止惡。大相國寺佛樂中的勸世曲,多為當時文化名人如蘇東坡、王安石、黃庭堅、范仲淹乃至奸臣蔡京等人詠詩填詞,直至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大相國寺還保留并傳唱著這類詞曲。由此也可見,勸世曲能有如此強盛的生命力傳世,實為廣大民眾喜聞樂見的結果。
大相國寺的器樂在其佛樂中占據重要地位,歷史上也有著深遠的影響,遠遠超過了聲樂,這也是大相國寺有別于其他寺院佛樂的根本之處。因為一些大寺院雖有梵唄贊頌,但很少設有能擁有非常多專業器樂的組織。大相國寺卻自北宋開國,便以佛樂著稱于世,且在朝廷的欽命下,設有龐大的樂隊編制,常設樂僧達百余人,鼎盛時有400余人的樂隊組合,氣勢宏大,影響也深遠,更加上寺院不僅擁有大量的演奏曲目,還擁有無數專業和業余的“合唱隊員”,這是其他寺院所不能比擬的。尤為殊勝的是,大相國寺歷來注重樂僧的培養,寺院有專門從事音樂研究的高僧任教,源源不斷為寺院培養著音樂人才,幾乎類似一所職業的佛樂專科學校,至使寺院佛樂一直傳承不息,樂隊人才濟濟,這種其他寺院絕無僅有的情況,自然為世所注目,其演奏的佛樂,當然也冠絕天下,令人仰慕不已。終究,專業的樂隊和精湛的演技,其自身便蓄涵著無比的傳世偉力和影響力量。
大相國寺佛樂使用的樂器
大相國寺樂隊在演奏佛樂時,因基陣容的龐大,運用了大量唐、宋宮廷音樂和古代音樂中使用的、今已失傳或近于失傳的樂器。然而,由于寺院樂隊一直秉承古代遺制,樂隊中從不使用近代才出現的弓弦樂器,只運用了打擊樂器,吹管樂器(包含 樂器)和拔彈樂器,樂隊基本上是仿唐、宋古制而建立起來的。大相國寺主要運用的樂器有:
一、吹奏樂器:其中包括①橫吹,亦即橫笛;②文明笛,即古豎笛又稱君笛;③角笛,其形一端向上彎曲,頂端漸細而尖,另一端漸粗,呈微喇叭形,吹口在中間偏上處,現已失傳。④簫和排簫;簫為豎吹的單支編管,以其形象加為一排編管即為排簫;⑤籌,是為古今中原佛樂中廣泛應用的特有樂器,似簫非簫,似笛非笛,為竹制透底的吹管樂器,吹奏時樂僧面部與籌的管身約呈45度傾斜角,故俗稱“歪嘴籌”。⑤笙,大相國寺佛樂使用的為17管14簧的園笙。⑥螺,又稱法螺、海螺、貝、梵貝,為佛教傳統樂器,此外還有塤葉、篳篥、法號等。
二、拔彈樂器,其中包括①琵琶(曲項、四弦)②五弦,即五弦琵琶;③三弦,即三弦琵琶;④阮咸,即以西晉“竹林七賢”之一阮咸命名的琵琶,因該琵琶勁較長,俗稱“長脖子阮”⑤箜篌,亦即豎琴;此外樂器還有箏、古琴、瑟等拔彈樂器。
三、打擊樂器:大相國寺佛樂運用的打擊樂器種類很多,分擊革、擊金、擊石三部分,僅擊革中鼓類就達十余種鼓,手鼓、腰鼓、架鼓、羯鼓等應有盡有;擊金類不僅包括佛教用的銅鈸、饒、鎧、引磬、金鐸、云鑼等傳統樂器,還有吊鐘、編鐘等中國古老樂器;擊石類主要以和編鐘情況相似的編磬等石樂器為主。另外還有拍板(即檀板或稱紅牙板)、木魚等擊木樂器。
大相國寺的樂隊編制
大相國寺自創建以來,始終與國家和政府有著非同一般的關系,遠過于一般古剎。在唐代,以相王身份等級稱帝的睿宗帝,其所賜“大相國寺”之名,本身就包含著該寺與皇權不可分割的關系,雖然“寺”是宗教的,但“相國”卻是皇權的烙印。至宋代,大相國寺更是得到國家至高的禮遇,被敕封為“為國開堂”的“皇家寺院”,可謂極盡榮光。大相國寺的佛樂,也因寺院的關系與朝廷有著密切的聯系,其樂隊的編制,基本上與唐、宋宮廷的樂隊大同小異,寺院樂隊吹奏部分和隋唐宮廷音樂中清樂、燕樂、唐世俗樂、宋教坊音樂中使用的樂器基本相同,只是多了“籌”等佛樂專有樂器;拔彈樂器和隋唐宮樂、燕樂相近;打擊樂器部分,雖大相國寺佛樂所使用的樂器較多,尤其是木魚、引磬、鐺、鉿等佛教專有法器是宮廷音樂所沒有的,但偏鐘、編磬、振金鐸等,卻和歷代雅樂中用于祭祀的樂器相同,編制也一樣。宋以后,中原漢文化遭少數民族文化侵略,由于習俗和文化的不同,宮廷樂器和大相國寺佛樂使用的樂器相同的越來越少,出現了較大的差異。不過,大相國寺始終堅持自己佛樂隊編制的正宗性,堅信自己代表著華夏正音,且樂隊編制本身即有金石鏗鏘的打擊樂,又有音色清脆悠揚的吹管樂和拔彈樂,是一種大吸收和大融合的燦爛文化,早以融通了古印度以及西域和中國古代的各種樂器,達到了已令世人仰慕的高度,故千百年來,樂隊編制的傳統,極少有什么變化,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
大相國寺佛樂的速度
佛教的宗本是慈悲,佛教的心髓乃智慧。所謂“破迷開悟”,無外乎“慈悲智慧”。佛樂本是佛法與古樂的結合,其終極目標,當然以佛為究竟,是覺悟,是無生涅槃。因此,演奏和聆聽佛樂,最根本的收獲,當是以佛樂去作修心之事、是樂事、沉靜、反省、濾知的自覺過程,亦即覺悟。故而,嚴肅、清凈、安祥、誠實,是為佛樂最顯著的特點。大相國寺佛樂在吸收和圓融宮廷音樂、民間音樂及古代音樂的基礎上,非常講究佛樂演奏的速度,這當然也是修持和弘揚佛法為根本的要求。在這樣的要求下,大相國寺佛樂,在應對演奏的需求上,有著兩個顯著的特色;一是隨緣化物,應病與藥,在一般民間放焰口,祝禱紅白之事上,所奏佛樂,大多來自民歌、戲曲、民間器曲等,并加以變奏和哄托,有著熱場和起興的作用,以便吸引聽眾,達到佛教普度眾生的理想,樂曲的演奏速度,故較為歡快,以適應廣大群眾的欣賞習慣;二是專用于獻佛和國家的重大祭祀,這類佛樂,乃心境之光,充滿了莊嚴、開闊及觀法入境的宗教意義,追求的是曲行人心,直提自心于道,不見凡事,但見圣容的效果,其演奏速度較為深沉緩慢,且不因世俗的欣賞習慣而改變,著重突出對莊嚴、感動、信仰、遠囑以及廣大和沉靜的感悟。這一特征,不獨和古代宮廷音樂的大氣相吻合,也是大相國寺佛樂傳承不息的精華所在。唐、宋以降,大相國寺仍得以為中原傳統音樂的代表,且擁有深遠的 影響力,這種氣韻安祥、從容自若的演奏風格,實為其關鍵所在。
佛樂又稱梵樂或梵唄,不獨是佛教弘揚教法和贊頌佛菩薩等美好事物的一種獨具宗教特色的聲樂,也是佛事活動中必不可缺的形制,廣泛地存在和運用于佛教儀規之中。梁朝慧皎法師所著《高僧傳》曾考證言:“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弦為善。見佛之儀,以歌贊為貴”。也確實,從佛教住世的角度來看,佛經的贊和偈均是通過唱、誦、念才能表達出來,而歌詠佛經伴以管弦之聲,引贊入樂,達致中和、清凈,也是“梵唄”的本意。由此可見,存在和運用佛典及佛事活動中的佛樂,當然緣起于佛教,并同時莊嚴著佛教,且為佛教的弘揚和傳播帶來了深遠的祝福和激勵;另一方面,佛教歷來也猶重運用音樂來“宣唱法理,開導眾心”,提倡音樂在服務佛教教義中的作用,所以佛經與佛學文獻大多涉及音樂,并多方面闡述了佛教對音樂的諸種看法。
佛樂在中國的傳播
佛樂和佛教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白馬馱經,佛教傳播中華,佛教梵唄也開始在我國流傳。早期的中國佛教活動自然完全承襲梵唄形制,即佛教史上稱做“西域化”講經的吟唱方式,梵唱由是冉冉升起于中華大地。佛教史上著名的天竺國竺法蘭大師及康居國康僧會大師,猶對佛樂在華夏的傳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大力推動了佛樂在中國的發展,二人被后世尊稱為南北梵唄祖師。宋大相國寺方丈贊寧在其《高僧傳o續誦篇》言:“原夫經傳震旦,夾譯漢庭,北則竺法蘭,始真聲而宣剖;南惟康僧會,揚曲韻以諷誦”,稱贊竺法蘭和康僧會為中國南北兩地的佛樂的領袖,并道出中國梵唄之南北差異的特點,北以“雄直宣剖”而長,南以“哀婉揚曲”以取勝。而二者佛樂的基本個性的形成,也尊定了佛樂在中國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通過絲綢之路,自東漢佛教的傳入,箜篌、琵琶、篳篥、都曇鼓、雞罈鼓、銅鈸、貝等樂器,及許多著名樂曲,如《摩訶兜勒》等,以及鼓吹、饒歌、蘇袛婆琵琶七調音樂理論,也相續從佛教國家傳入我國,對我國音樂及音樂理論的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公元802年,古印度驃國王太子舒難陀,親率樂隊32人及舞蹈團來華訪問,并贈送樂器十種,極大地推動了我國佛教音樂的發展,諸多上善因緣,終促使我國唐宋以來更進一步的發展且形成了完善的燕山十八調等著名佛樂。
佛樂的中國化
如佛教傳入中國,融會中國儒學和玄學至唐朝最終完成佛教的中國化一樣,佛樂也經歷了佛教普臨東土的需要而中國化的情形,這也是佛教隨緣化物的表現。從漢語發音度而言,漢語發音的口型,音樂的長短,音韻的高低,以及文化素養、審美觀點,欣賞習慣的不同,其旋律也必然隨之改變。梁慧皎法師在其《高僧傳》言:“梵音重復,漢語單奇,用梵音詠漢語,則聲長而偈短;用漢曲詠梵文,則韻短而詞長”。基于這樣的語言矛盾,融會中國各種傳統音樂,探索新的梵唄聲韻以適應弘法需要,成為一項急待解決的問題和工作。隨著人們的不斷攝取中國傳統音樂來探索新梵唄,并使大量典型的中國傳統曲子融入梵曲,其結果也必然導致佛樂的中國化。相傳魏曹植賞游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雅哀婉,深動其心。曹植獨聽良久,大有體會,乃慕其音節,結合我國傳統音樂典籍《瑞應本起》,創作梵曲三千,流傳天下,使得梵曲在傳播實踐中獲得重要的重建和發展,對佛樂“改梵為秦”中國化情形也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后世因此尊曹植為中國梵唄的始創者。
佛樂的發展
佛樂在中國的發展,基本上是佛樂“中國化”的逐步完成和完善。自曹植創作極富中國特色的三千梵曲之后,東晉高僧慧遠大師又以“以歌詠法、廣明教義”為旨,創唱導制。亦即提倡以俗講方式宣講佛教經義,并注重俗講時唱頌的音樂性,因此大師吸收了大量當地音樂素材編制佛曲,用以俗講經義,此也為佛樂民間化取得了良好的開端。接蹱慧遠大唱導制進一步發展而來的講經形式,稱謂“變文”,其對佛樂的發展更是推波助瀾。“變文”主要是講經通俗化、故事化,融佛教精神于中國古代故事之中,形象生動地宣傳了佛教教義。由于“變文”以唱白形式相結合,唱詞為韻文體,且唱頌普遍采用民眾喜聞樂見的民間曲調,這對佛樂的民間化和普及都具有極大的推動作用。至唐代,隨著佛教傳播的深入人心和繁盛發展,佛樂吟唱也隨著佛事活動的隆盛而獲得了廣泛的發展空間,尤其是唐宮廷出于對佛教的信奉,不僅將佛樂引入皇室齋天、祈福、報謝、追悼及宗廟祭祀等傳統宗法活動中,并在禮娛宴樂中,也演奏佛曲,伴以歌舞助興。佛樂的地位得以極大地提高,佛曲從而成為唐代的主要音樂體裁;另一方面,佛教活動愈是大眾化、地方化,佛樂也就愈來愈要求民間化,用民間曲調和漢語聲韻來取代舊的“梵”聲已成為必然之勢。至宋代,佛樂完全采用民間曲調,并普遍為各寺院采用,這就是最終形成了中國佛樂的最基本的音韻調律,確立了自己的風格形成。時至今日,許多名山寶剎,仍是承襲自宋、元、明以來的佛樂曲調,只是由于地方方言之別,各地寺院在具體唱法上自然存在著不同差異。
大相國寺的創立及其佛樂發展狀況
大相國寺始創于北齊天寶六年(555年),其寺址原為戰國時期魏公子無忌之故宅,極富文化歷史意義。寺院初名建國寺,后毀于戰火。唐長安初年(701年),高僧慧云云游至開封,夜宿繁臺,看到城內汴河有紫氣沖天,天明徒步河岸,又見此地瀾漪中有天宮影,參差樓閣九重儀象,如彌勒佛之兜率宮院,慧云隨發愿建寺。后所督造的彌勒佛像,大放金光,照徹天地,震動人心。巧合的是,睿宗帝是夜也于夢中感通寶像奇瑞,且靈應肇發,大有感悟。而為紀念自己由相王龍飛稱帝,應其祥瑞,睿宗帝御筆賜名,對大相國寺以特別眷顧,使其極盡造化,風光莫比;另一方面,開封自古便為大梁故都,天下要沖,至唐代雖為河南道統轄下一地方單位,但自從隋代開通濟渠以來,更為“水陸都會”而名揚天下,商貿和文化活動均十分頻繁和發達,堪為地靈人杰。得益于古都開封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和壯闊的人文活動等上善因緣,大相國寺自創立之初便融入中國歷史文化的洪流之中了,唐代著名畫家吳道子,雕塑家楊惠之、王溫,文化巨匠李邕,以及當時京城第一琵琶大師善本長老的佛樂傳人虛真大師等,均為大相國寺的文化建設留下了光輝的史跡。可以說,大相國寺自建寺之始,在帝王政治權利的直接關照下,加上源源不斷的歷史文化名人關懷的諸多善緣,寺院不獨鑄就了其獨具秉賦的政治文化構架,更成就了其薈萃天下文化精英的文化胸懷,終以文化寺院而享譽天下,成為一方精神圣地。而基于寺院崇高的社會地位和文化傳統,伴隨佛教的弘傳而發展起來的佛樂,也自然與大相國寺的文化建設有著不解之緣。有關寺院和民間音樂的歷史典籍中,大相國寺自創建之始便有樂僧越仁大師、虛真大師在寺院演奏佛樂的記載。至唐天寶年間,大相國寺已出現完整的樂隊,并于高僧在法華經開講之前,敬獻佛樂以報謝佛恩來吸引聽眾。到唐大歷年間,寺院將向佛獻樂定為制度,開壇講經必由樂隊獻樂,以表莊嚴和虔敬。這一傳統的形成也使得寺院開始注意對佛樂曲目的整理和收藏,這無論對寺院佛樂的弘傳和建設,都有著重大意義。時至今日,單從佛樂曲目的傳承來說,由于大相國寺至今仍保存著大量較完整的古樂譜,研究中原佛樂和古代音樂的學者,都必須把大相國寺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這在客觀上,便使得寺院在傳統音樂方面秉賦一種廣泛的代表性,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源于寺院繼承民族優秀文化的優良傳統,大相國寺佛樂,已成為整個中原傳統音樂的典型代表大相國寺佛樂的成熟
唐代承南北朝隆盛的法運,佛教盛行全國,并由華土開始外傳東南亞諸國。大相國寺自經睿宗命名題額,在封建最高統治者大力維護下,迅即發展成為汴州最大的寺院。不僅如此,唐肅宗至德年間,經肅宗帝批準,將河南道統僧錄司設在大相國寺內,這使得寺院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這一變化,對推動大相國寺的佛教建設和文化建設,作用非凡。僅就佛樂而言,佛樂至唐代已發展為黃金時代,其最為顯著的特征是,唐代宮廷音樂中從七步樂到十部樂中,來自佛教國家或以佛樂模式建立起來的樂隊竟達六、七部,可見朝廷對佛樂的喜好和偏愛。而借助朝廷的支持,佛樂的發展當然也更臻鼎盛。
《洛陽伽藍記》描述當時寺院佛樂活動稱“梵樂發音,驚天動地”,可謂盛況空前。正處上升階段的大相國寺也不例外,此時不僅組建了專業的樂隊,且在吸收古樂曲和舞曲來充實佛樂方面,也有著長足的發展。見諸多種文獻記載,被譽為“華夏正音”的大相國寺大型佛樂變奏曲《駐云飛》,經由寺院專業樂僧的整理和創作,終于使這部古代樂曲演變成一部完整的佛樂作品。全曲共有六百一十九個小節,包括九個樂段,另有引子和尾聲的散板部分,作品甚為完整。尤值一提的是,該曲采用許多不同的佛教素材和各種變奏手法,并用統一的佛樂風格貫穿起來,如佛日中天、普臨天下,氣勢甚是博大、恢宏。從一定意義而言,象征佛光普照,降幅世人的大型佛樂《駐云飛》的圓滿問世,實為佛樂成熟的一個標志,其與當時唐代歌舞大曲相比也毫不遜色,或更有過之。此外,歌頌佛教天神摩訶迦羅的傳統樂曲《耍孩兒》,以及《普庵咒》、《水先枝》、《柳含煙》等一大批系列佛樂也在此時匯集或創作于大相國寺,并由此傳誦天下。僅唐崔令欽撰《教坊記》及明永樂年間《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目錄》等音樂典籍,所載唐代大相國寺佛樂就達三十余首(部)。而能為諸音樂史籍所關注,可見大相國寺佛樂的影響和地位了。
北宋時期大相國寺的佛樂
北宋定都開封,作為京都最大佛剎,大相國寺倍受北宋帝王的優禮和崇奉,被北宋王朝欽命為 “為國開堂”的“皇家寺院”,并設中央直屬管理機構“左街”于寺內,與“右街”開寶寺同理和管轄全國佛教事務。大相國寺由此一躍而成為天下首剎,寺院建設也達至空前的鼎盛,轄六十四禪、律院,占地達五百四十余畝。不獨高僧云集,也是朝廷巡幸、祈報、恭謝、祈禱等國禮祝禱的首選道場,以及招待安置外國使節和外國僧侶重要場所,堪為全國中外文化及佛法交流的中心。隨著大相國寺發展的盛勢,大相國寺的佛樂至北宋也達到最隆盛的階段,一方面,由于朝廷對寺院的崇奉,國家許多重大活動和典禮都放在寺院舉行,寺院為適應朝廷禮儀的需要,無論是樂隊還是所演奏的佛樂,都必須更專業更規范,演奏的技藝也必須更高超,入微和莊嚴。因此,大相國寺重視音樂,培養專職樂僧,嚴格訓練技巧和認真演奏樂曲的優良傳統自然形成;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參與以及在財力和人力和物力方面的支持,大相國寺自北宋初期即組織起龐大的專業樂隊,其狀況是空前的。此外,在朝廷的大力支持和安排下,大相國寺在寺內專門修建了演奏七弦琴的佛樂專業“劇院”--維摩院,以及在大殿前修建的專供一般游人和香客欣賞佛樂的演奏廣場--樂棚,這些其他寺院絕無僅有的專業設施,足以說明寺院佛樂發展的鼎盛及專業。更為重要的是,受命于朝廷且秉負“為國開堂”正大使命的大相國寺,每屆主持均由朝廷任命,而出于組織和參與朝廷在寺院舉行的各種禮儀活動,他們大多精通樂律,并在朝廷的要求下,赴任以后必將全部音樂資料做一次梳理工作,使之更加充實完善,并記錄存檔。故大相國寺歷史上不僅涌現大批造詣很高的專業樂僧,且千百年來,佛樂資料也一直得以能妥善地保存下來,實為寺院所建立的良好制度的原因。
北宋佛樂的基本特點
中國佛教自宋代起開始強化佛教化導世俗社會的世間功能,把出世求解脫之道與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統一起來,追求學佛與做人的統一,以及對社會的道德教化,并將愛國主義精神引進佛教,與祖國共命運。這種充滿新鮮空氣的狀況即佛教史上所說的佛教世間化。宋代佛樂也是如此,無論在道德上、習俗上,還是藝術上,都有創造和成就。此時期的佛樂,有別與唐以前的特點,佛樂繼續發展和完善。這種發展和完善,主要表現在技藝實踐上的深入,以及在社會世俗生活中的深入、社會風氣與社會心里的深入和人們情感生活的深入。僅就大相國寺的佛樂而言,自北宋起,由于寺院和朝廷以及民眾廣泛深入的接觸和合作,寺院佛樂大量吸收了民間音樂和宮廷音樂,形成了自身隨緣隨機且以提升道德,凈化人心,祥和社會為目標的自由風格,寺院不僅以“皇家佛剎”自律,致力與朝廷的各種禮儀活動,以莊嚴國土為己任,在寺內創建維摩院式供雅士欣賞“陽春白雪”的音樂廳,且設置樂棚常年舉辦“下里巴人”式普及性大眾音樂盛會,把寺院的佛樂推及到社會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這種宋以前不多見的佛樂活動的形式和盛況,在深入人心以及在最大程度上廣擴佛樂影響的同時,也成就了大相國寺佛樂雅俗共賞的基本特征和海納百川的雄輝氣勢與文化胸襟。此外,由于大相國寺在教內獨高的社會政治地位,做為一座秉負皇命擁有管理天下寺院職能的寶剎,其本身的佛樂,也自是一種標準和典范,不僅在最大程度上代表著帝王禮儀之樂,也是中原傳統音樂最典型的代表。
宋以后的大相國寺佛樂
自金兵攻陷東京,宋室南遷。大相國寺的佛樂活動大受影響。后南宋又在杭州建大相國寺,開封大相國寺不少高僧及樂僧又南渡臨安,曾經籍帝王之力創建的規模宏大的樂隊大為失色。據史料載,北宋大相國寺樂隊鼎盛時期人數達400人之眾,至元初樂隊人數已不足70人,可見其差別之大。不過,好在大相國寺向以皇家寺院著稱于世,在地方和佛教界一直有著非凡的影響,雖宋室南渡,大相國寺仍被中原一帶寺院奉為領袖寺院,故大相國寺樂隊雖人數大為遞減,但每遇寺院有重要的佛事活動,城內其他寺院及城外子孫小廟的樂僧,均會云集寺院,與大相國寺樂隊一道奏樂唱贊。元代詩人陳孚在其感荷“大相國寺天下雄”的詩作里,仍有“三千歌吹燈火上,五百纓縵煙云中”的感嘆,這說明大相國寺至元代,佛樂仍頗具氣勢,縱樂隊編制較北宋不可同日而語,不過佛樂仍為寺院標志性的事物,為人們所注目。而隨著元代雜劇的興起,著稱于世的大相國寺佛樂,也深入其中,尤其是中原地區,不僅大型的劇目吸收了不少佛樂,三、五成群的小型佛樂隊,更是活躍于民間,為鄉村父老操辦各種紅白之事,演奏人們耳熟能詳的大相國寺佛樂,影響甚為廣泛。
明朝開國后,朝廷仍詔命在大相國寺設置僧綱司,管轄開封府各州縣的寺院僧侶。并指令大相國寺重新整理佛樂資料,重組樂隊,服務于社稷。明朝在開封第二代周王朱有燉,酷愛戲曲,因崇慕大相國寺的佛樂盛名,故與大相國寺有著甚深的交誼,他曾組織聯合寺院樂僧,收錄當時流行于世的雜劇三十一種,名“中州弦索”,并指示寺院安住梨園班子,在大相國寺內設置舞臺,使四方藝人云集寺內,每日清唱不斷,佛樂繞梁的大相國寺由此也成為一所音樂雜劇的故鄉,直至明末。
崇禎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義軍與明守城官兵互決黃河,至使開封遭滅頂之災,大相國寺也造毀滅性破壞,寺僧四處逃亡,奔走他鄉,樂曲大多失傳,大相國寺佛樂由此一蹶不振,更談不上什么發展了。清初順治皇帝詔命重修大相國寺后,雖有樂僧不斷零星回寺,但卻無力組建成規模的樂隊了,只是應付佛事,做一些有償的演奏和向佛獻樂活動。直至清末民初,寺院承宋、明文化娛樂的傳統,籍寺院處于鬧市中心之便利,又成為市民娛樂中心,寺院佛樂才藉民間娛樂的興勢有了點起色。是時,寺院經年百戲雜陳,鼓書、相聲、墜子、皮影、說書、戲法等民間娛樂光彩爭華,相映生輝,雖然與北京的天橋,濟南的大觀園一道被專家學者譽為中國曲藝的三大發祥地,但所憾寺院馳譽天下的佛樂卻退而為次,未能占據主導地位,得到發揚光大。1927年軍閥馮玉祥主政河南,動用軍警,驅僧滅佛,沒收寺產以充軍餉,改寺院為市場,至使大相國寺的佛樂與佛教一樣,遭到毀滅性的打擊。1938年日軍侵占開封期間,重新恢復寺院的佛事活動,大相國寺也再度成立了佛樂演奏機構,并設置專職樂僧十余人,每逢佛、菩薩紀念日,還邀請外地樂僧到寺獻樂,雖規模較之太平盛世相去甚遠,但也還式笙管齊鳴,法音繚繞,大相國寺佛樂仍為中州之冠。
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歷史的原因,僧人再度離寺,大相國寺被改為公園,跟隨而來的連年政治運動,就連佛教都被視為封建迷信,更遑論佛樂了;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運動,寺內所保留的樂器和樂譜,全部被付之一炬,大相國寺佛樂活動完全終止,徹底云消煙散。
當今大相國寺的佛樂建設
1992年,在黨和國家宗教政策的關懷下,大相國寺重新做為佛教活動場所開放,千年古剎,迎來中興,不數年時間,大相國寺煥然一新,寶像莊嚴、道風盎然,各項佛教建設,都納入了正常的軌道。
1998年,在已故中國佛協會長趙樸初大德的舉薦下,心廣大和尚晉寺任主持。大和尚晉寺后,在趙樸初會長的囑托下,把繼承寺院優秀文化傳統,弘揚大相國寺高邁超拔的佛教文化,作為寺院建設的一項主要工作來抓,并分步驟對寺院傳統文化進行梳理。2002年,為使大相國寺歷史上極富盛名且已近失傳的佛樂再度重光,大和尚親任團長,成立了大相國寺佛樂團,開始致力于大相國寺傳統佛樂的挖掘整理,并先后聘請十余位國內著名的音樂教授,到寺指導和培訓樂僧。至2002年底,大相國寺佛樂團已培養專職樂僧20余人,寺院佛樂文獻的整理也取得不少成就,基本上能適應各種場合及各種規模的演奏。2003年,寺院佛樂團在大和尚的精心操持下,已大有進境,開始走出寺院,參加國內外各種重大佛事活動及社會慈善活動的演出,受到了社會各界廣泛的好評。大相國寺平和、悠揚、沉靜、清涼的佛樂,猶如璀璨明珠,光照大地。尤其是2004年應邀赴澳門參加澳門回歸祖國5周年的盛大演出,更是以整齊的陣容,恢宏的氣勢而折服無數觀眾,為近百家媒體所報道或轉載,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為天下注目。
今天,大相國寺佛樂團在心廣大和尚的運籌下,正在向更規范、更典型、更精深的方向深入發展,重振唐宋神韻,澤益天下友情,實為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大相國寺水到渠成的發展方向和目標。
大相國寺佛樂的構成
大相國寺佛樂與帝王政權和鬧市民眾長期水乳交融的甚深關系,頗具隨緣化導世俗社會的世間功能,演奏形式上也多有禪心對現實生活的觀察思維,是慈和的人生志向步向覺悟的音樂。因此大相國寺佛樂雖分為聲樂和器樂兩大類,但也兼有聲情并茂的歌舞,且相互之間密不可分,素有“歌聲繞梁,絲管嘹亮,諧妙入神”的贊譽。大相國寺的聲樂包括梵唄和勸世曲兩種:梵唄,《楞嚴經》解釋為“梵土之贊頌也”;“梵”是古印度語“梵摩”的簡稱,意為“清凈”、“寂靜”、“離欲”;“唄”乃“唄匿”音譯之略,意為“止斷止息”或“贊嘆”,指佛教徒以短偈形式贊唱佛、菩薩的頌歌。故從清凈心生發,修心頌佛,安然清唱佛經、偈贊且以歡喜心歌頌佛法,贊頌佛之功德的,均可稱為“梵唄”,如《戒定真香》等。勸世曲可看作佛樂中的通俗歌曲,歌詞多為高僧和文人所作,內容涉及民族英雄,歷史名人,歷史事件,民間故事以及二十四孝,三綱五常等傳統道德范疇,主要用于僧人作法會時,宣傳佛教,教誨世人揚善止惡。大相國寺佛樂中的勸世曲,多為當時文化名人如蘇東坡、王安石、黃庭堅、范仲淹乃至奸臣蔡京等人詠詩填詞,直至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大相國寺還保留并傳唱著這類詞曲。由此也可見,勸世曲能有如此強盛的生命力傳世,實為廣大民眾喜聞樂見的結果。
大相國寺的器樂在其佛樂中占據重要地位,歷史上也有著深遠的影響,遠遠超過了聲樂,這也是大相國寺有別于其他寺院佛樂的根本之處。因為一些大寺院雖有梵唄贊頌,但很少設有能擁有非常多專業器樂的組織。大相國寺卻自北宋開國,便以佛樂著稱于世,且在朝廷的欽命下,設有龐大的樂隊編制,常設樂僧達百余人,鼎盛時有400余人的樂隊組合,氣勢宏大,影響也深遠,更加上寺院不僅擁有大量的演奏曲目,還擁有無數專業和業余的“合唱隊員”,這是其他寺院所不能比擬的。尤為殊勝的是,大相國寺歷來注重樂僧的培養,寺院有專門從事音樂研究的高僧任教,源源不斷為寺院培養著音樂人才,幾乎類似一所職業的佛樂專科學校,至使寺院佛樂一直傳承不息,樂隊人才濟濟,這種其他寺院絕無僅有的情況,自然為世所注目,其演奏的佛樂,當然也冠絕天下,令人仰慕不已。終究,專業的樂隊和精湛的演技,其自身便蓄涵著無比的傳世偉力和影響力量。
大相國寺佛樂使用的樂器
大相國寺樂隊在演奏佛樂時,因基陣容的龐大,運用了大量唐、宋宮廷音樂和古代音樂中使用的、今已失傳或近于失傳的樂器。然而,由于寺院樂隊一直秉承古代遺制,樂隊中從不使用近代才出現的弓弦樂器,只運用了打擊樂器,吹管樂器(包含 樂器)和拔彈樂器,樂隊基本上是仿唐、宋古制而建立起來的。大相國寺主要運用的樂器有:
一、吹奏樂器:其中包括①橫吹,亦即橫笛;②文明笛,即古豎笛又稱君笛;③角笛,其形一端向上彎曲,頂端漸細而尖,另一端漸粗,呈微喇叭形,吹口在中間偏上處,現已失傳。④簫和排簫;簫為豎吹的單支編管,以其形象加為一排編管即為排簫;⑤籌,是為古今中原佛樂中廣泛應用的特有樂器,似簫非簫,似笛非笛,為竹制透底的吹管樂器,吹奏時樂僧面部與籌的管身約呈45度傾斜角,故俗稱“歪嘴籌”。⑤笙,大相國寺佛樂使用的為17管14簧的園笙。⑥螺,又稱法螺、海螺、貝、梵貝,為佛教傳統樂器,此外還有塤葉、篳篥、法號等。
二、拔彈樂器,其中包括①琵琶(曲項、四弦)②五弦,即五弦琵琶;③三弦,即三弦琵琶;④阮咸,即以西晉“竹林七賢”之一阮咸命名的琵琶,因該琵琶勁較長,俗稱“長脖子阮”⑤箜篌,亦即豎琴;此外樂器還有箏、古琴、瑟等拔彈樂器。
三、打擊樂器:大相國寺佛樂運用的打擊樂器種類很多,分擊革、擊金、擊石三部分,僅擊革中鼓類就達十余種鼓,手鼓、腰鼓、架鼓、羯鼓等應有盡有;擊金類不僅包括佛教用的銅鈸、饒、鎧、引磬、金鐸、云鑼等傳統樂器,還有吊鐘、編鐘等中國古老樂器;擊石類主要以和編鐘情況相似的編磬等石樂器為主。另外還有拍板(即檀板或稱紅牙板)、木魚等擊木樂器。
大相國寺的樂隊編制
大相國寺自創建以來,始終與國家和政府有著非同一般的關系,遠過于一般古剎。在唐代,以相王身份等級稱帝的睿宗帝,其所賜“大相國寺”之名,本身就包含著該寺與皇權不可分割的關系,雖然“寺”是宗教的,但“相國”卻是皇權的烙印。至宋代,大相國寺更是得到國家至高的禮遇,被敕封為“為國開堂”的“皇家寺院”,可謂極盡榮光。大相國寺的佛樂,也因寺院的關系與朝廷有著密切的聯系,其樂隊的編制,基本上與唐、宋宮廷的樂隊大同小異,寺院樂隊吹奏部分和隋唐宮廷音樂中清樂、燕樂、唐世俗樂、宋教坊音樂中使用的樂器基本相同,只是多了“籌”等佛樂專有樂器;拔彈樂器和隋唐宮樂、燕樂相近;打擊樂器部分,雖大相國寺佛樂所使用的樂器較多,尤其是木魚、引磬、鐺、鉿等佛教專有法器是宮廷音樂所沒有的,但偏鐘、編磬、振金鐸等,卻和歷代雅樂中用于祭祀的樂器相同,編制也一樣。宋以后,中原漢文化遭少數民族文化侵略,由于習俗和文化的不同,宮廷樂器和大相國寺佛樂使用的樂器相同的越來越少,出現了較大的差異。不過,大相國寺始終堅持自己佛樂隊編制的正宗性,堅信自己代表著華夏正音,且樂隊編制本身即有金石鏗鏘的打擊樂,又有音色清脆悠揚的吹管樂和拔彈樂,是一種大吸收和大融合的燦爛文化,早以融通了古印度以及西域和中國古代的各種樂器,達到了已令世人仰慕的高度,故千百年來,樂隊編制的傳統,極少有什么變化,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
大相國寺佛樂的速度
佛教的宗本是慈悲,佛教的心髓乃智慧。所謂“破迷開悟”,無外乎“慈悲智慧”。佛樂本是佛法與古樂的結合,其終極目標,當然以佛為究竟,是覺悟,是無生涅槃。因此,演奏和聆聽佛樂,最根本的收獲,當是以佛樂去作修心之事、是樂事、沉靜、反省、濾知的自覺過程,亦即覺悟。故而,嚴肅、清凈、安祥、誠實,是為佛樂最顯著的特點。大相國寺佛樂在吸收和圓融宮廷音樂、民間音樂及古代音樂的基礎上,非常講究佛樂演奏的速度,這當然也是修持和弘揚佛法為根本的要求。在這樣的要求下,大相國寺佛樂,在應對演奏的需求上,有著兩個顯著的特色;一是隨緣化物,應病與藥,在一般民間放焰口,祝禱紅白之事上,所奏佛樂,大多來自民歌、戲曲、民間器曲等,并加以變奏和哄托,有著熱場和起興的作用,以便吸引聽眾,達到佛教普度眾生的理想,樂曲的演奏速度,故較為歡快,以適應廣大群眾的欣賞習慣;二是專用于獻佛和國家的重大祭祀,這類佛樂,乃心境之光,充滿了莊嚴、開闊及觀法入境的宗教意義,追求的是曲行人心,直提自心于道,不見凡事,但見圣容的效果,其演奏速度較為深沉緩慢,且不因世俗的欣賞習慣而改變,著重突出對莊嚴、感動、信仰、遠囑以及廣大和沉靜的感悟。這一特征,不獨和古代宮廷音樂的大氣相吻合,也是大相國寺佛樂傳承不息的精華所在。唐、宋以降,大相國寺仍得以為中原傳統音樂的代表,且擁有深遠的 影響力,這種氣韻安祥、從容自若的演奏風格,實為其關鍵所在。
責任編輯:C006文章來源:大河網 2012-05-02
下一條:千年傳承 開封盤鼓聲震中天上一條:中國國寶:針灸穴位銅人詮釋中醫文化
相關信息
沒有記錄!
著名人物
沒有記錄!
精彩展示
沒有記錄!
評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