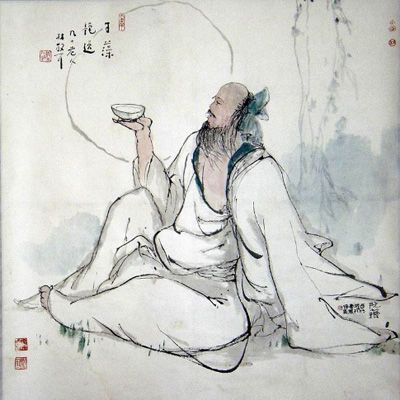-
沒有記錄!
- 1、宋太祖千里送京娘非虛構 對美女動心為
- 2、張從正酒酣露絕技
- 3、趙匡胤悼韓通:你我都沒錯
- 4、趙匡胤的吝嗇與奢侈
- 5、包拯:清心為治本 直道是身謀
- 6、掙扎于亂世中的悲情蔡文姬
- 7、董宣用計囚國舅
- 8、看阮籍眼中的封建禮教
包拯:清心為治本 直道是身謀
2013/4/1 8:49:59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南宋思想家朱熹與學生談論交際之道時,講了包拯的一個故事,說包拯年輕時,曾與一李姓同學就讀于家鄉廬州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市)某僧舍,每次從家里往返僧舍,必須經過一富翁家。包拯與李生品學兼優,前途無量,都是集優股,富翁很想親近他們。某日,當他們路過時,富翁邀請他們進屋做客,包拯和李生委婉拒絕了。過了一段時間,富翁又特備酒宴,熱情邀請他們去家里吃飯。李生礙于情面,打算接受邀請,包拯卻厲聲說:“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包拯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不注意小節,與富翁吃吃喝喝,稱兄道弟,那么將來萬一學有所成后回鄉做官,這些人情債難道不會影響公正嗎?人家在工程招標時要求關照一下,在官司纏身時要求放他一馬,怎么辦呢?于是,他又一次謝絕了富翁的盛情相邀。事也湊巧,多年以后,包拯果真被朝廷安排回鄉,出任廬州知州,因為以前沒欠人情債,故斷案執法,皆能公正無私,留下千古美名。
包拯為人做官,一貫嚴格自律,既不傍大款,更不攀權貴。康定元年(1040年),42歲的包拯出任端州(今廣東省肇慶市)知州。端州產硯,中國四大名硯中端硯尤以石質優良、雕刻精美居首,被朝廷欽定為貢品。那些附庸風雅的權貴,均以能得到端硯為榮。因此,在端州任職的官員,似乎找到了一條升官的捷徑,紛紛打著納貢的幌子,以多出數十倍的數目征收,假公濟私,拿著公家的東西去結交打點。然而,包拯到端州任職后,首先想到的是減輕農民負擔,有權不用,自斷這條升官捷徑,悉數減去多余的征斂,只征收進貢的數目。領導也好,故交也好,他一概不理。他還在端州府的墻壁上寫下《書端州郡齋壁》一詩:“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他認為做官當除貪欲、謀正道,以做清官為榮、以做貪官為恥就是他的人生觀和榮辱觀。于是,包拯任職3年,“歲滿不持一硯歸”。
包拯鐵面無私,不但在士大夫間名聲大,而且在民間名聲好,因他曾任天章閣待制,百姓親切地稱他為“包待制”。嘉祐元年(1056年),包拯出任開封知府,負責京城訴訟和治安。當時,打官司有一個規矩,百姓不得直接到衙門遞交狀子,要由小吏轉呈。為了使知府大人早些受理,許多人不得不上下打點疏通關節,一個官司打下來,往往贏了官司輸了銅板,得不償失。包拯坐堂開封府,卻一改陋習,大開正門,使百姓能夠直接上前陳述曲直訴說冤情,既減少了百姓的打點費用,又準確地把握了案情,更縮短了審理周期,一舉數得。因此,京城迅速流傳這樣一首民謠:“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意思是打官司無錢疏通關節也沒關系,有包大人呢!
包拯不會種花,只會栽刺。他與張堯佐是一對冤家。張堯佐是外戚,其侄女張貴妃很受宋仁宗寵幸,因此官運亨通。開始,張堯佐被任命為三司使,包拯向宋仁宗說,像張堯佐這樣的人,連做小官都不合格,遑論三司使這種朝廷大臣,并表示反對;幾年后,在張貴妃的軟磨硬泡下,宋仁宗提出任張堯佐為節度使,再后來又提出任張堯佐為宣徽使。包拯認為這樣的提拔速度太快,不符合干部升遷制度,以“不可驟升”為理由,前后7次上書彈劾張堯佐,甚至在朝堂之上當面頂撞宋仁宗,硬是在身單力薄的情況下,讓張堯佐的升遷受阻。
包拯最重官員操守,最恨以權謀私。嘉祐三年(1058年),他出任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當時,三司使張方平利用手中的權力,廉價套購某商人的住宅,從中漁利。包拯認為,三司使是朝廷最高財政官員,非廉潔之士不能勝任,張方平巧取豪奪,不適合擔任這么重要的職務。因此,包拯上書彈劾張方平,致使張方平隨即被罷免。
包拯就是這樣,做官行事,只論是非,不論利害,只論榮辱,不論得失。他高風亮節,不虛情假意,不隨聲附和。他的心里只有朝廷綱紀和百姓冷暖,不想因交往而影響公正,那些門生故吏和親朋好友,誰也別想通過他撈到任何好處,所以,“故人、親黨皆絕之”,大家紛紛離他而去。在人情關系的力量遠遠勝過綱紀國法的官場,包拯形影相吊,門可羅雀,顯得那么孤立。然而,孤獨一生的他,卻一直是那些貪官污吏眼中的煞星,《宋史·包拯傳》說:“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是啊,這樣一個鐵面無私而又六親不認的人,叫人如何不害怕呢?【原標題:包拯:清心為治本 直道是身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