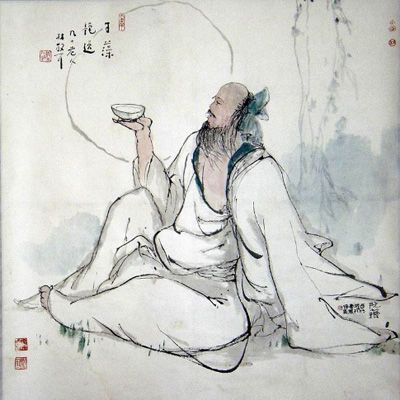精彩推薦
熱點關(guān)注
專題推薦
-
沒有記錄!
熱點排行
- 1、史海探秘:大楚皇帝張邦昌埋在江西樂安
- 2、被出賣的黃樵松將軍
- 3、張從正酒酣露絕技
- 4、一紙“勸進文”逼死了阮籍
- 5、“硬脖子”縣令董宣斗公主的故事
- 6、范雎的遇與不遇
- 7、種世衡的妙計
- 8、“另類老師”邊韶
范雎的遇與不遇
2014/12/4 11:00:09 點擊數(shù): 【字體:大 中 小】
“伯樂相馬”與“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這些說道,人們耳熟能詳,都是說生活中不缺少人才,但缺少發(fā)現(xiàn)和賞識人才的“伯樂”。
戰(zhàn)國時代,策士游說之風(fēng)很盛,其中有一些人則由于“伯樂不常有”所致,他們大多屬于“馬投伯樂”那伙的。
范雎(或作范且)本是魏國人,在中大夫須賈(音古)門下當(dāng)差,沒干成什么大事情,反遭受一場冤枉,幾乎丟了性命。那是有一次魏國派中大夫須賈訪問齊國,范雎是隨員。他們到了齊國,齊國的國君齊襄王遲遲不接見須賈,卻仰慕范雎的才華,先給范雎送去一些金錢和禮品。范雎雖有自知之明沒有收受,卻仍然引起了須賈的疑心,以為他給齊國泄漏了什么機密。
回國后,須賈把這件未經(jīng)證實的事報告了國相魏齊。魏齊偏聽偏信,同樣不經(jīng)任何調(diào)查分析,就叫來一伙打手把范雎狠狠打了一頓,所謂“折肋摧齒”。眾打手見范雎差不多已死,就找來一領(lǐng)破席卷了扔掉。但范雎并沒有死,他緩過來后,改名張祿,輾轉(zhuǎn)逃到了秦國。
當(dāng)時秦昭王已在位36年,但他并不是勢力中心。國中政治上勢力最大的有四個人:穰侯、華陽君,都是昭王母親宣太后的兄弟;涇陽君、高陵君,都是宣太后寵愛的兒子,即昭王的同母手足。穰侯是宰相,把持國政,其余三人輪流掌管軍權(quán)。黨親連體,互為羽翼。他們仰仗宣太后這個后臺,實際權(quán)力很大,封邑廣闊,家財富足,國王不及。
范雎根據(jù)這些不正常的現(xiàn)象,到秦國后先給昭王遞上了一封書信,請求面談。昭王沒有擺架子,立馬派車子接范雎進宮。范雎來到宮中,故意東走走西看看,內(nèi)侍們吆喝道:“王來了!”范雎故意大聲說:“秦國只有穰侯和太后,哪有什么王?”昭王聽到了這句話,心中如被一根針刺了一下,當(dāng)即特別隆重地接待了范雎。周圍人很少見這種隆重場面,驚訝不已。
昭王吩咐左右退下,然后恭恭敬敬地對范雎說:“先生有什么見教?”范雎只是“嗯!嗯!”并不答話。昭王連問三次,范雎也三次以“嗯!嗯!”作答。昭王感覺到事關(guān)緊要,便跪下央求道:“先生終究不肯賜教嗎?”
范雎這才開始講了一番大道理,并且強調(diào):“我現(xiàn)時寄居秦國,同您的關(guān)系還很生疏,而我要說的,卻是關(guān)于君臣之間和骨肉至親之間的事。今天說了,明天就可能有殺身之禍。死固然沒有什么可怕,人總是有死的一天,只要是我說的這些話,對秦國有利,即使因此被殺,又有何懼?我真正顧慮的是,天下有才能的人們,見到我為秦國盡忠,反而被殺,他們就可能從此誰也莫肯向秦了。”
范雎的這次談話,深深打動了昭王,昭王雖早有察覺,卻沒有認(rèn)識到大權(quán)旁落的嚴(yán)重性,可謂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范雎的話取得了昭王的認(rèn)同與信任。昭王拜范雎為相,收回了穰侯的相印,讓他回老家陶邑去了;還讓宣太后告老,不許她再過問朝政;華陽君、高陵君、涇陽君也都移居到關(guān)外。范雎多年為相,一直到老。
這個故事在《史記》《戰(zhàn)國策》中都有記載。同是一個范雎,齊國和秦國都敬重他,景仰他;他雖是魏國人,魏國不但不重用他,反因齊國國君看重他,則偏聽小人打小報告而加以陷害。古今中外,人們大多感嘆人才難得,實際上被埋沒的人才,什么時候都比比皆是。有的是沒碰上機遇,有的則是沒遇上真伯樂。
我見過一種“伯樂”。我稱他們是“跑馬場上的伯樂”。平日里他們的視野中沒有千里馬,待某一日哪匹馬在跑馬場上奪了頭彩,他們則跑上前去錦上添花,似乎大有發(fā)現(xiàn)地宣布“這是一匹千里馬呀!”。真正的伯樂是在千里馬沒有奪冠之前,已看出其具備了千里馬的素質(zhì),并加以調(diào)教,精心喂養(yǎng),給予雪中送炭。不過現(xiàn)在有一個好處,如果你真是個人才而被埋沒了,一般情況下是允許“跳槽”的。也就是說,可以“伯樂相馬”,也可以“馬投伯樂”。作者:高深
責(zé)任編輯:C009文章來源:《中國紀(jì)檢監(jiān)察報》(2014-06-24)
相關(guān)信息
沒有記錄!
精彩展示
沒有記錄!
評論區(qū)
友情鏈接
商都網(wǎng)
中國網(wǎng)河南頻道
印象河南網(wǎng)
新華網(wǎng)河南頻道
河南豫劇網(wǎng)
河南省書畫網(wǎng)
中國越調(diào)網(wǎng)
中國古曲網(wǎng)
博雅特產(chǎn)網(wǎng)
福客網(wǎng)
中國戲劇網(wǎng)
中國土特產(chǎn)網(wǎng)
河南自駕旅游網(wǎng)
中華姓氏網(wǎng)
中國旅游網(wǎng)
中國傳統(tǒng)文化藝術(shù)網(wǎng)
族譜錄
文化遺產(chǎn)網(wǎng)
梨園網(wǎng)
河洛大鼓網(wǎng)
剪紙皮影網(wǎng)
中國國家藝術(shù)網(wǎng)
慶陽民俗文化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