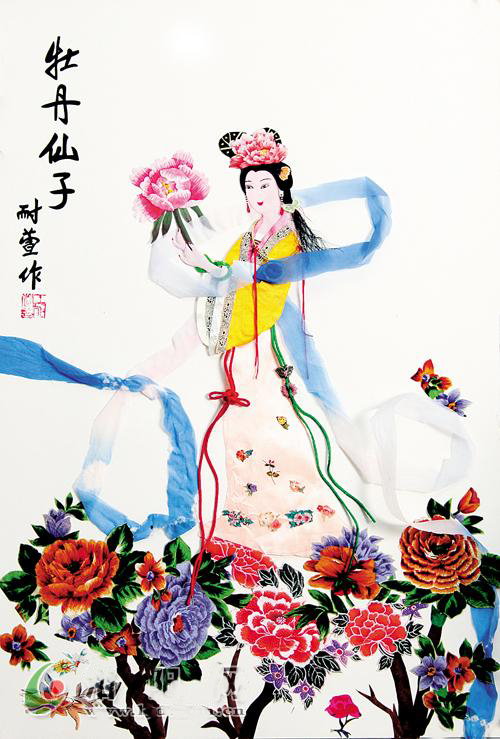精彩推薦
熱點關注
專題推薦
-
沒有記錄!
熱點排行
雙城記:泥之重生河之絕唱
2012/8/17 9:08:47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中國四大名硯中,澄泥硯是唯一以人工澄煉之泥燒制而成的陶硯,也是唯一不以產地命名的名硯,這就為后世的紛爭埋下了伏筆。”三門峽市美協主席、澄泥硯收藏家李俊林說。
2006年9月10日,國家郵政總局舉行了“文房四寶”郵票首發式,據業內人士稱,被選中的“國家名片”“硯”票,取材于珍藏在肇慶歷史博物館的兩方明清端硯。
此消息一出,驚動了所有相關地域。端硯自是名正言順的“首發式”舉辦地,澄泥硯也趁勢出擊,一場混戰后,山西新絳縣、河南新安縣都搭上了順風車,經國家郵政總局批準搞了“首發式”。三門峽澄泥硯,曾是“唐代中國澄泥硯的NO.1”,到現在有被“邊緣化”的尷尬,這個消息刺激了張建成。在他的全力操作下,三門峽為彰顯自己的原產地身份,自行搞了一個首發式。
張建成,39歲,三門峽人。1995年,28歲的張建成還在三門峽小車馬坑博物館過著“一張報紙一杯茶”的悠閑日子,在當年5月27日的《人民日報》上,他看到一篇文章,記者郅振璞到三門峽尋找澄泥硯,市長抱歉地說:“愧對古人,我們還未挖掘、用好虢地河泥呢。”張建成第一次因澄泥硯而受刺激,“憤”而開始研制澄泥硯。
11年過去了,他從一名文物局的干部變成了一個精明的商人,創建了自己的研究所,挖掘傳統,銳意創新,隨著三門峽創建“中國優秀旅游城市”的步伐,他也把澄泥硯變成了三門峽的“文化名片”。
11年之后,張建成看到的是,在全國,澄泥硯以泥硯的身份被眾多石硯包圍,在拼爭傳統魅力。在黃河流域,山西和河南拼搶區域影響。在河南境內,則有鄭州、新安、三門峽三地在攤薄市場大餅。河南境內多地或明或暗的紛爭,無形中削弱了河南澄泥硯的整體影響力,以致在全國并不占絕對優勢地位。
為了澄泥硯,記者走訪了三門峽、洛陽、鄭州三地的澄泥硯藝人,看到了他們各自艱辛的努力,也看到了他們的困惑。
對于坊間盛行的“澄泥硯歷史上曾有長期斷代”的說法,李俊林一直持否定說。他自言收集的三百多方古澄泥硯歷代皆有,他說:“唐宋金元澄泥硯一直有大量實物出現,僅三門峽考古研究所就藏有二百多方。再加上私人收藏,足以佐證,澄泥硯在三門峽這塊土地上,沒有失傳,傳承有序。”李俊林這種想法,影響了張建成,堅定了他一定要把三門峽的澄泥硯傳承下去的決心。
通過翻閱資料,張建成在1936年《陜縣志》中發現了關于澄泥硯做法的記載,馬上如法炮制,但“發現不行,看起來講得很清楚,中間好多細節未交代。”張建成很苦惱。
在李俊林的陪同下,張建成開始了漫漫求師路。第一站直奔陜縣人馬寨村,找到了王玉瑞的第五代后人王國州。老先生當時年近七十,耳聾眼花,多年不制硯,得知有人要做硯,十分高興,便傾囊相授。在他的指點下,張建成制出了“色黑而雜銀沙星點”的人馬寨澄泥硯,倒模成型,極具民間風格。
這種硯,粗、耐磨、下墨、實用,是一種實用硯,但距離史書上記載的“堅實如鐵,叩致金聲,刀之不入”、“撫如石,呵生津……”等可作觀賞品的文人硯還有距離,怎么辦?張建成只能再四處求師。
遠赴山西新絳(古絳州),近奔洛陽新安,新安縣的澄泥硯藝人李中獻給了他幫助,并派一名師傅幫其建窯。提及此事,張建成一直感激于心。
要制澄泥硯,先找泥。“泥場是制硯藝人核心的機密,誰也不會告訴你。你得自個找。”張建成說。
為找泥場,張建成沒少吃苦頭。一個冬雪剛過的傍晚,他到盧氏找泥場,山路呈S狀,陡且滑,他開的破吉普車控制不住往溝里栽去,幸虧汽車前橋撞在溝邊的一塊大石頭上,車剎住了。一身冷汗的張建成鉆出車,才發現溝邊孤零零只有那一塊石頭,他立馬沖那塊救命的石頭磕了個頭。這回差點把小命搭進去,還是沒找到泥場。
“我在哪兒找到的泥場誰都想不到,靈寶和陜縣的交界處,五原村一帶,千溝萬壑之間,找到了泥場。據說唐朝虢州澄泥硯,就是在這兒取土。”張建成說。
這個泥場當然是商業機密,張建成不會帶記者去看,像是安慰,張建成帶我去了黃河邊上他的另一處泥場。出陜州故城向西,來到黃河灘里,他指著河心一叢蘆葦說:“每年六七月份黃河落水后,有一層泥,二三厘米厚,長達半年的蓄水期把泥浸泡得泥性改變,做硯臺不會裂。就取這層泥用。”
泥找到了,窯建起了,燒窯就是燒錢,前五窯全是廢品,數萬元錢沒了。燒窯師傅也急了,認為窯址離鐵路太近,震動太大,要求重新建窯。新窯建好,第一窯開窯的前一天晚上,張建成睡不著,出身音樂世家的他,便拿出久違的二胡,拉了起來。
第二天,開窯,成了,60%的成功率,“120方澄泥硯在三門峽這塊古老土地上重生。”當地媒體用欣喜的語氣感嘆。
鱔魚黃、蟹殼青、豆沙綠、玫瑰紫、魚肚白、蝦頭紅,這些歷史記載中講得神乎其神的顏色,張建成試圖一一復活。這些顏色都是通過窯變才能產生的。窯變的產生往往以全窯報廢為代價,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
“以報廢80%的代價,換來了第一方豆沙綠犀牛望月硯臺,后來又以報廢90%的代價,換來了弦紋瓷窯變。”張建成說。
年少時學過美術雕刻的張建成,對硯雕有獨特的看法,他要求工人不要滿足于多與像,要在意與味上下工夫。這應是制硯者的新追求。
如此嚴格要求,令他的多件作品獲獎。“龍鳳龜”獲2004年中國文房四寶博覽會金獎。同年,他的多件澄泥硯作品在中國旅游商品博覽會上獲金獎。2005年,他被河南省文聯評為“十大民間(工藝)美術家”。
河南境內澄泥硯原產地在三門峽,2003年,中國工藝美術家協會授予的“中國澄泥硯之鄉”卻是洛陽新安縣。2006年,河南省首批“民間文化杰出傳承人”新安占據兩位——游敏和李中獻,兩人均為河南省民間工藝美術大師。新安縣的地位得以凸顯,得益于新安縣制硯的產業化程度。“2004年,新安縣生產澄泥硯的廠家有數十家,從業者300多人,品種有數百種。”河南省民間工藝美術大師游敏說。
游敏告訴記者,“歷史上新安縣曾先后隸屬過古虢州和古陜州,1947年后才隸屬洛陽。”游敏和李中獻自述,傳承都是源自三門峽的陜縣人馬寨村。而三門峽張建成復生澄泥硯,又得益于李中獻甚多。到了現在,因行政區劃分屬兩地,兩地關系相當微妙。
58歲的李中獻說:“曾祖父李廷選曾隨陜縣人馬寨村最有名的制硯藝人王玉瑞學藝十年,后返鄉將這一技藝帶到新安。”50歲的游敏自述“祖上游宗豪是清末秀才,游學陜州,拜當地制硯名家王玉川學制硯”,后回新安制硯。
游敏和李中獻的成長還得益于新安的歷史背景。新安有宋代陶瓷遺址幾十處,是有千年歷史的陶瓷之鄉。李中獻從小就跟著父兄學會做缸、盆、碗。游敏學生時代在瓷廠做工,主要也是學做瓷盆、瓷罐。
兩人能夠成為澄泥硯的杰出傳承人,更得益于黃河,“黃河挾泥裹沙穿越秦晉大地,躍出龍門,自三門峽經豫西峽谷至新安,岸低水闊,水流緩慢,留下了一個個淤泥灘。黃河至此已流經數省,沿途納入眾多支流,所沉之泥,含有豐富的鐵、銅、鉀、鎂、鉛、鋁等礦物質,成為制作澄泥硯的上佳材質。”游敏在文章中說。
新安縣城東500米處有漢函谷關,記者和游敏一起踏訪此處。曾經的漢函谷關,“北至黃河,南至宜陽,長達100公里”。記者眼中所見,不過是衰草寒煙中的一座殘破城門洞,高不過10余米。游敏認為:“當年制作磚瓦材料的工匠們,在新安縣城西北部黃河中下游交接地帶采泥燒制磚瓦時,也制作了一些澄泥硯,至今散落于新安民間。”
這是極有可能的。因為“唐宋之前大家都有用秦漢舊磚瓦制硯的習慣,就是因為找不到那么多秦磚漢瓦,唐朝人才模仿秦磚漢瓦的制造方法制造了澄泥硯。”三門峽市美協主席李俊林的看法,在新安再度得到佐證。
作為新安現代澄泥硯的領軍人物,李中獻和游敏兩人個性與作品迥然不同。
李中獻是新安現代澄泥硯的拓荒者。他不擅言談,不長于理論。他已經干了十六年,踏踏實實,但有時步履不免艱難。
1995年,《人民日報》記者郅振璞在三門峽尋澄泥硯未果,趕到新安時發現,李中獻帶領十幾個人在黃河邊摔了五年泥巴,已摔出數十個品種上千個硯臺。
在郅振璞采訪李中獻的前一年,即1994年,是李中獻事業的一個高峰。“1994年9月,國務院總理李鵬及夫人來洛為小浪底工程開工剪彩,澄泥硯被作為禮品贈送給李鵬和夫人,受到稱贊。”《洛陽日報》如是報道。一個月后,他的澄泥硯在“1994中國名硯博覽會”上獲獎。
為了事業,李中獻把畢業于復旦大學的兒子李湛拉了過來。李湛說:“我起初并不愿意,有一天晚上,天很熱,我爸在雕刻,衣服后背全濕了,灰揚得到處都是。”李湛被父親的執著打動,便辭去公職,到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學習了兩年雕塑,學成歸來后全力投入到研究中,2000年春,造型美觀的立體硯臺出爐了。
2000年春,李中獻試圖復活宋代“呂道人”硯。呂道人是宋代山西澤州制陶硯的名家,作品“堅潤宜墨,金鐵劃之,了無痕跡”,是澄泥硯中的極品,但傳世甚少。李中獻一次次試燒,2005年4月,“呂道人”硯問世。不盡完美,但不失為一次大膽的嘗試。
游敏是個很有想法的人,像盤谷硯的制硯大師張書碧一樣,他試圖用硯承載許多文化概念。只是游敏意欲承載的,是“河洛文化”這個大命題。他的漢辟邪硯、漢簡硯、石鼓文硯、河圖洛書硯、中華寶璽硯等,都是別人很少涉及的題材,他想用獨特的造型藝術向人們展示一部立體的人類文明史。他受天津美術出版社之約,撰寫的《漫話澄泥硯》一書目前也已定稿。
2003年10月,游敏在新安縣創辦了澄泥硯藝術館,展示了從黃河禹門口到花園口近三百公里河岸線上采集到的泥材和一些古今精品硯。他的代表作品“回歸硯——家”也陳列于其中,這是他在1997年為迎接香港回歸而制作的。整個硯臺取黃河澄泥為材,重150公斤。被央視大型專題片《香港滄桑》評述為“慶回歸珍品”。
在他的藝術館內,記者看到了他和女兒游曉輝(河南省最年輕的民間工藝美術大師之一)合作的多件作品,2004年,父女制作的澄泥硯“東方之子”、“商周古韻”榮獲第五屆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珍品博覽會銀獎和優秀獎。
游敏制硯,思維現代,但“工藝流程忠實古法”,他反復強調,“原材料及工藝流程不能改變,改變了就不成為澄泥硯了,傳統工藝的尊嚴就沒了。”
唐宋金元澄泥硯一直有大量實物出現,僅三門峽考古研究所就藏有二百多方,這表明澄泥硯傳承有序。【原標題:雙城記:泥之重生河之絕唱】
責任編輯:C009文章來源:大河報 2006-12-8
下一條:澄泥硯的歷史造型研究上一條:黃河澄泥硯 泥與火的傳奇工藝
相關信息
沒有記錄!
著名人物
沒有記錄!
精彩展示
沒有記錄!
評論區